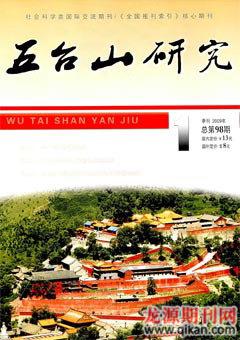佛學當代價值意蘊初探
郭繼民
摘要:現代佛學是從古印度傳入華夏后,經與儒家、道家近千年摩蕩而終成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之有機組成部分。然而,由于諸種原因,近百年來,佛學一直處于邊緣地位,隱而不顯。當下人類面臨諸多全球性問題,重返經典無疑給人類有益警示,尤其在解決人生問題、倫理道德問題、文化溝通乃至提攜科學研究等方面均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佛學;當代;價值
中圖分類號:B94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6176(2009)01-0035-05
佛教雖誕生于古印度,然佛學卻大興于東土。自佛學傳人華夏與儒、道摩蕩千余年,已與儒、道三分天下,構成華夏文明內核之一,或隱或顯地影響著華人的心理結構。近、現代佛學雖經“五四”之“革命”、“文革”之“驅除”,然深入國人骨髓之文化基因焉能割斷?那種慎密、玄思之智慧,仁慈、悲閔之情懷又焉能舍棄之?
綜觀當下所謂全球化之時代,幾乎各國皆以經濟利益馬首是瞻,視“技術主義”為救命稻草,于科技、經濟、軍事等諸多領域展開激烈競爭,不但導致能源、生態、氣候、環境等全球性的“生存危機”,亦導致了信仰、道德、文化之精神危機。人類向何處去,人類應如何自我救贖?無疑成為人們在21世紀的必答題。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次諾貝爾獎頒獎會議上,與會國際知名學者提出“人們要解決當下的問題就必須回到二千多年前的孔子時代尋找智慧”。此言甚切!不過,我以為非但要向了孔子汲取智慧,亦須向老莊、佛陀那里吸取智慧。
客觀地講,就外在現象而言,對于儒、道之學術,尤其儒學已引起國人足夠注意:如既有納入“國家工程”的儒藏之編纂,亦有波及全球的“孔子研究院”之建立,更有方興未艾、轟轟烈烈的“講經”、“讀經”之活動。相比之下,佛學則不免落寞許多。此既有人們受各種妄言干擾之因(如人們對之所持的不加審慎的所謂“迷信、封建”之偏見),亦有佛學自身理論玄奧之故。若世人能真正走進佛學,體悟其思想之深邃、邏輯之嚴謹、理識之圓融、智慧之超拔,則不免讓人頓覺茅塞大開,頗有醍醐灌頂之功效。事實上,佛學玄妙、精深處即在于其視野廣闊與思維“超越”。若強比之于世間所謂“真學術”,如科學、哲學,其深刻可見一斑。竊以為,科學乃針對實體現象之規律,謂之一維空間(表層/實用);哲學乃追問現象背后之本體,是超現象的,謂之二維空間(實層/意義);而佛學則研究、體認“實質”后的真如,是超越哲學的,或日“后哲學”的,強名之為三維空間(深層/終極)。其實,對于佛教學術之定位,現代高僧太虛法師、著名佛學學者歐陽竟無、王恩洋、周叔迦、張化聲等均對之有精辟之論,究其要旨,大概略同,即認為佛學乃超越哲學、科學、宗教之上的教育。張化聲先生曾明確指出“佛法者非科學而科學,非宗教而宗教,非哲學而哲學,其精義乃在法相唯識”。筆者無意探討佛法與宗教、科學、哲學之關系,亦不參與佛教是否為宗教之辯。筆者所探討之要旨乃在作為開啟人智、學術層面之佛學在當下之功效,或日當下佛學之價值意蘊。
竊以為,作為學術層面之佛學,其內蘊豐厚,義旨精微,視野恢弘,對改變當下世界之現狀尤有裨益。余姑且將佛學之理“照”之于世,以期對社會人生、哲學、倫理、科學等諸領域有所提攜。
佛學之于人生就佛學與人生問題,上世紀三十年代,太虛法師在廈門“人生佛教之目的”之演講,大致歸結為“人間改善、后世勝進、生死解脫、法界圓明”四則,其論自然鞭辟入里。今筆者則從當下現實出發,去闡發佛學對人生之關照。
佛學倡導心靈的生活,它以超越物欲及世俗束縛而獲得心靈自由為宗旨,更以修持戒、定、慧脫離六道輪回而達到永恒涅槃為鵠的。自然,脫離生死輪回的涅槃狀態乃佛之境地,似乎非世人所能達到。但佛學所謂“諸法無我,諸行無常,涅槃寂靜”之法印所彰顯的“去執”理念頗有益于當下。
首先,“去執”有益于心靈之解放與心理問題之解決。誠如盧梭所謂的“人生之追求在于自由,然無時無刻不在枷鎖之中”那樣,人生的最大追求莫過于自由。然而,當下的人卻被種種“執”緊緊束縛,尤其是“物欲”之貪,非但束縛人之心靈,更引起能源危機、生態危機、環境危機,進而導致人類生存危機。古希臘先哲推崇的“節制之生活”,儒家倡導的“中庸之生活”,道家所向往的“自然之生活”,其“中道義”均可視作佛家之“去執”。“執著心”起,貪、嗔、癡亦起,所謂“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天機既失,人生何趣之有?且夫物欲纏身,人隨物轉,為物所控,為之殫精竭慮,精神焦慮,欲罷不能,豈非失去自性,何談自由?亦如莊子所言:“終身役役而不見其功,熒然疲役而不知其歸,可不哀乎?”因此,竊以為在“利益主宰”一切的當下,在消費、浪費、揮霍成為“關鍵詞”的當下,在競爭日益加大、生存壓力日益增大、心理問題尤其突出、自殺率居高不下的今天,用“去執”之理念來治愈人類之“焦慮”,倡導一種節制、回歸心靈的生活,對個體身心健康、社會和諧穩定均大有裨益。
其次,“去執”對老人之終極關懷有所幫助。人之于世,不過百年,畏死之心,人皆有之。尤其在中國即將進入“老齡化”社會的當下,終極關懷問題日漸緊迫。自然,若世人皆能以老莊之豁達、唯物科學之理性對待生死固然甚善,但并非每個人皆能了悟生死,更多的乃是畏死、恐慌。事實上,多數老人乃于恐懼、孤獨中離去,尤其在老人院,此種問題更加突出。竊以為在宗教信仰不甚普遍的中國,我們既可通過佛學有關理念(如“去執”)之推廣來開示世人,使其胸懷寬廣、博大,用“月到天心、風來水面”之自然和恬淡之心對待“生死之大”;亦可通過“人間佛教”之推行而安撫之。事實上,在民間,凈土宗對百姓之終極關懷一直起著重要的安撫作用。
佛學之于哲學、文化之交流佛學于文化交流之功用可謂大矣!文化交流之準則乃為求同存異,增進溝通,故爾要求諸文化中須有“公約數”或至少須有相似點——最低限度亦要“形似”——溝通、對話方可進行,否則自說自話,交流流于形式。同樣,若諸文化完全一致,亦無交流之必要,此種況味莫若白石老人論畫所語一“似與不似之間”。佛學本始于古印度,之所以能在華夏扎根,亦在于其于儒、道之“似與不似之間”,彼此具有互補性,故而能和諧交融,成為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若缺乏交流、貫通之環節,佛學亦或能傳承至今。當然,筆者并不排斥完全“不同質”的文化也可能經過碰撞、摩蕩乃至交流的可能性。
當下,鑒于地球村、“經濟全球一體化”之客觀現實,文化、學術之交流亦頻繁有加。竊以為弘揚佛學之精髓,不但有益于佛學之傳承,亦有益于諸文化之精進。就“同質”文化而言,當下應加強漢傳佛學與藏傳佛學,以及日本及其東南亞各國之交流,取長補短,彼此提高。通過學術交流,進一步圓融律、密、禪、凈、教等各
學派,推動佛學文化的傳承、弘揚和發展,以求為人類提供智慧之資。
就佛學與西方文化而言,尤有交流之必要。似乎表層而言,佛學與西學風馬牛不相及。然而,事實上,佛學或隱或暗地影響著近代西方思潮,西人叔本華、尼采、柏格森乃至海德格爾莫不受其影響。無疑,此種“形似”至少為佛學與現代西方哲學文化之交流奠定了基礎。恰如北大教授張祥龍所言:“在今天眾多的西方哲學流派中,也許只有少量的能與中國古代思想進行有孕育力的對話。肇端于二十世紀初的現象學,而非任何傳統的西方概念哲學,是這樣一個待選者。”予深有同感。不過,予將之鎖定了較為“準確”的目標,竊以為更須在佛學之唯識論與西方現象學之間架起溝通之橋梁。現、當代西方哲學,多受胡塞爾現象學之影響,薩特、舍勒、海德格爾等哲學大家莫不受惠于現象學,現象學業已成為西方學術界之“顯學”。其始祖胡塞爾終生作現象學導論,以本質直觀、現象學還原及意識構造為核心內容,以求為一切科學尋找絕對支撐。然究其根底,仍不圓滿,若以唯識論視之,似乎并沒有超越前六識,若其在生年能接觸唯識之末那識、阿賴耶識等理論,其“現象學”理論之構造也許更為精當。當代有識之士如張祥龍、倪梁康及瑞士著名現象學者Iso Keem(耿寧)諸先生已著手展開佛學與現象學溝通之研究,然而上述諸君皆以西學為宗,兼及佛學,似有所隔。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太虛法師于廈門講法相唯識學,其不但“才通三藏,學融古今”,更熟稔西學,將西方哲學、科學與唯識論融為一體,為佛學學術之精進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今人若有精通唯識之君能以佛學貫通“現象學”乃至西方后現代哲學,則無論對推進人類學術、矯正西學之偏執還是弘揚佛學文化之精義、溝通中西哲學文化均有無上之功德。
佛學之于道德倫理雖然佛學之宗旨乃是“成佛”,但成佛之根基仍在“做人”,故爾“道德倫理”乃其“份內事”。如凈土宗之《觀無量壽經》云:“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如此三事,名為三世諸佛敬業因果。”所謂“佛從人起”,只有先修持德行,返歸良知,然后在此基礎上不斷精進,才有達到“佛”之可能。
就佛學倫理之當代意蘊而言,竊以為可從普世倫理、動物倫理、環境倫理而挖掘之。首先,就普世倫理而言,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佛學之宗旨乃著眼于“動物人”之解脫,此解脫乃是針對整個人類而言,這勢必使之帶有“人間佛學”的性質。因此,通往“解脫”途中的諸多戒律多為“普遍人性”之規范,自然使其帶有普世倫理之特質。上世紀末,西方倫理學界熱衷于將“摩西十戒”納入普世倫理之體系,事實上,佛法戒律亦具有普世性,且更為詳盡、周當:既有對人性基本約束的“八戒”,亦有涉及衣食住行、坐臥起止的細節——“小戒律”。尤其重要的,佛法之倫理要求不但有豐富的內容,更有一種有效的約束機制,或日修德之保障。
佛學要旨首先在于做人,雖然禪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頓悟”說,似有忽略德性修持之偏向,但是總體而言,佛學尤注重“因果報應”、“六道輪回”之威懾與“依德漸次修行”之道。此種“因果報應”及其“威懾”(如世人若不能積德行善,就有可能墜入地獄)不斷拷問、警醒,進而喚起人之良知,并通過“持戒”將外在威懾內化為德性,從而避免誤入歧途。可見,“因果報應”、“六道輪回”對規范人性起著至關重要的“監督”作用。而當下,崇尚利益、技術理性之人類,道德標準日漸模糊,行為肆意妄為;外無“因果”之威懾,內無良知之反省,以至于導致人性之惡泛濫,雖有法律之干預,然終不能在心靈根本處斷絕惡念。故而導致法律條文愈來愈繁,然犯罪率卻居高不下,斯為痛矣!
若佛學能走進民間,以凈宗之“慈、孝、敬、信”、華嚴之“包容必均”之理念化解人間爭執、沖突,實行太虛法師所謂的“人間佛教”,則不僅有利于道德人心,亦能幫助政府解決諸多社會問題。今人凈空法師以安徽湯池小鎮為“試驗區”,以“弟子規”教化當地村民,用力三月有余,而營造出一個人心和諧的首善社區,可謂成績斐然。其做法值得我們深思!
復次,佛教倫理亦有助于動物倫理與生態環境倫理之發展。佛學大乘倫理思想乃是“慈悲為懷、普度眾生”。《金剛經·大乘正宗分》云:“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余涅槃而滅度之。”此論標明佛學所持動物與人乃平等關系之理念,當下西人倫理學家辛格、約納斯等所謂的動物權利亦不過如此。且佛法又將人與動物皆納入“六道輪回”之中,作惡之人可淪為動物,而“昕經得法”之畜生亦有輪回為人之可能:此規避了西人口頭宣傳之虛妄,為世人“身體力行”之實踐打下良好根基。天臺宗智覬大師進一步把“六道輪回”擴充為“十界互具”,意謂動物畜生不但有人性,而且也有佛性,只要修成正果,不但可成人,亦能成佛,可謂為動物之生存爭取了廣闊空間,亦為當下人們重新審視人與動物之關系提供了一種新的視野。其次,就生態環境倫理而論,可謂“眾生有情”的進一步邏輯推演,即把眾生由“有情界”擴大至“無情界”,首倡之舉,當推湛然大師。湛然在《金剛鋅》中對“故知經以正因結難,一切世間何所不攝,豈隔煩惱及二乘乎?虛空之言何所不該?安棄墻壁瓦石等邪?”其義在于表明“無情有性”,既然“無情有性”,一草一木、一塵一石、一瓦一礫皆有佛性,那么世人應以平等心對待一切眾生,包括植物、土地等等。近年西方人雖有土地倫理、生態倫理、環境倫理之宣言,但仍然處于“人類中心主義”立場,并沒有從根子上人手,若將其與佛學之“眾生有情”之理互攝、參照,殊幾對當下人類走出環境、生態、生存之危機有所貢獻。
佛學之于科學研究提及科學與宗教之關系,常人似有荒誕不經之感:科學與宗教水火不相容,豈能共生?然而,事實卻遠非如此。相反,愈是大科學家,其對宗教愈充滿敬畏之感,愈看重二者聯系與互補性。恰如192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康普頓所言:“科學與宗教不存在沖突,科學愈來愈成為宗教的盟友。我們對大自然理解的越深,我們對大自然之神也認識的愈清。”愛因斯坦亦有“沒有宗教的科學是瘸子,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瞎子”之論。事實上,確實如此,大物理學家開普勒、牛頓、愛因斯坦、普朗克,大數學家萊布尼茲、康托爾等皆有著深厚的宗教情結。無怪乎楊振寧先生有“哲學發展到一定程度變成科學,而科學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到了宗教”之感嘆!
就佛學與科學之關系而言,亦大抵如此。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尤智表居士在《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中就佛學與科學之關系從外在“形似”到深層“神似”聯系均進行了詳盡、中肯之論述,至今讀來,亦發人深省。尤其對佛學時空觀與相對論之比較、“因緣和合”與“質能之聯系”之貫通、“色、空”之轉換與“物質不滅定律”之關聯均有真知灼見,頗啟人思維。
就當下佛學予科學之對話、溝通,余不自量立,嘗試歸納為以下諸點,以求教于方家。竊以為,佛學與科學之提攜,大致有五:一則佛學可為科學提供更為廣闊、立體的多重思維空間。科學愈取得突破性進展,首先要“跳出廬山”,將自身置于更為開闊的空間內,才有可能“識得廬山真面目”。佛學中所蘊涵的豐富想象、超常思維及多維觀察視野均有“超越”之質,極有益于科學之“思想解放”。二則佛學“圓融”之理有助于糾正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之偏執。自然科學方法傾向于機械、孤立之術,然宇宙萬物乃因緣和合、互為條件、一體無隔之狀。假若不能將具體學科置于整體聯結之網絡下,科學研究猶如盲人摸象,很難取得重大突破。當下各種學科之界限已不復明顯。呈現出一種混沌狀態,交叉學科異軍突起,似乎印證“萬法歸一”之古老哲理。三則佛學之因明學所蘊涵的“邏輯思維”尤其有益于科學探索。雖然就表面而言,科學注重事實、實證,然而科學欲要超越自我,亦需“思想實驗”,愛因斯坦相對論之提出乃建立于獨特想象與抽象思維基礎之上,而“因明學”即為訓練人之抽象邏輯之妙術。遺憾的是,當下,非但自然科學家對之知之不多,即使從事哲學人文學科之士亦大多對之陌生。若有志之士能將因明之學所彰顯出的思維方法予以研究,則會使其更加科學。四則佛學唯識論有益于心理科學之發展。心理學研究大抵圍繞感覺、直覺、思維而展開,其總體研究仍然在六識之內,若能將末那識、阿賴耶識之理論運用于心理學,心理學中的諸種難題亦可化解。五則佛學之信仰及其“體證精神”對當下從事自然科學研究者亦有所啟發。佛學講信仰,更講“實證”、“體證”,皈依佛門的諸多“僧寶”用終生來證其“信念”,這種對信仰的堅持和實證精神與科學家的追求真實乃一脈相同。不同的是,自然科學從共性角度求證世界之真,而佛僧則從個體身份體證世界之真。就當下而言,從事自然科學工作者不僅信念不足,且缺乏甚至失卻嚴謹的實證精神,近年發生在科學研究中的種種丑聞、鬧劇即為明證。竊以為,若其能從佛學精神領悟一二,亦當有益于科學之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