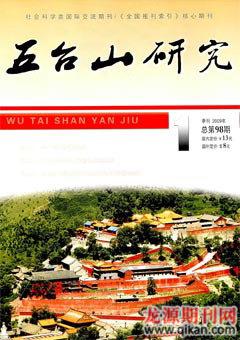云想衣裳花想容
康立群
摘要:通過考察研究,深化了對五臺山文化的認識,提出“崇尚佛教,首尊文殊”系清朝的一項基本國策的觀點,并論述了“包裝”的意義。提出五臺山的規劃開發應走主題公園的路子,要在文化軟包裝上下功夫。
關鍵詞:國策;主題公園;軟包裝
中圖分類號:G11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6176(2009)01-0046-05
文化是景區的靈魂。景區的魅力取決于文化的展示。文化的展示有賴于載體的包裝。
五臺山的主體文化是佛教文化,核心是文殊信仰。悠久的歷史,闊大的地域,還造就了與之相關聯的皇家文化、民俗文化、節慶文化、山水文化等系列亞文化。千年的修煉,高貴的靈魂,歷代的尊崇,宏麗的包裝,奠定了舉世聞名的黃金品牌、圣地形象。五臺山猶如一座積淀深厚、品位高雅而又取之不盡的文化寶藏。在旅游市場激烈競爭、景區強烈需要文化支撐的今天,變換角度,拓寬視野,以創新思維去進行探索、研究,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筆者現將最近考察學習所得匯整如下:
一、“崇尚佛教,首尊文殊”,是清朝的一項基本國策。
佛教,作為一種文化,一種宗教,一種哲學,在塑造中華民族的靈魂和性格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于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社會風俗的滲透和浸潤更是不可估量,一個民族的復興必然伴隨著文化的復興。當我們沖破“左”的束縛,用現代理性的目光審視包括佛教的傳統文化時,一種新的意境出現在眼前,發現經典離我們并不遙遠。五臺山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崔正森先生,前不久在《略論五臺山文化及其核心》一文中,對文殊菩薩的思想精華——般若,作了既深刻又通俗易懂的闡發,是一次有益嘗試。同時,一批角度新穎、貼近現實的論著在《五臺山研究》相繼發表。相信用不了多久,佛經也會走上“百家講壇”。
最近,筆者對北京北海公園內永安寺作了一次實地考察,對“文殊信仰”有了更深體悟。始建于清順治八年(1651)的永安寺位于皇家內苑北海中的瓊華島上,山裹寺,寺包山,山寺一體,景致殊勝,系規格最高的皇家喇嘛寺院。主殿法輪殿供奉釋迦牟尼,兩側為八大菩薩,文殊位列首席。島東側半月形平臺上的智珠殿專供大智文殊。白塔腳下位置最高的殿堂名善因殿,覆有上圓下方雙層歇山式屋頂。此種特殊形制,在故宮太和殿丹墀之上,兩側各有一桌面大小的微縮形建筑,它象征天地宇宙、江山社稷。殿內正中供一尊文殊忿怒化身——大威德金剛,被尊奉為大清帝國的最高保護神。立于殿前放眼下望,但見碧波蕩漾太液池,玉帶飛虹金海橋,筆者不由聯想到乾隆皇帝六上五臺山時所作詩中的兩句:“大士如如據蓮座,金容永永鎮華垓。”公園北岸寺廟群實際是永安寺的延伸,主殿為五智之一的大圓鏡智寶殿,供有文殊,著名的九龍壁即其影壁。岸邊建有敞式五亭,綠蔭遮蔽,清風穿越,智者樂水,心曠神怡,故號五智亭(即人們俗稱的五龍亭)。如此看來,若稱永安寺為文殊寺毫不為過。藏式大白塔高高聳立(為老北京最高點),象征著佛教至高無上的地位。它代表的不僅是一種宗教信仰,更是一種治國理念。
北海公園東側即景山公園。明朝時為一大土丘,因堆放宮中所用煤炭,故俗稱煤山。至清初順治年間,將此大土丘一分為五,形成今日五峰連綿的格局,取名“景山”。乾隆年間,于其上建五亭,內供佛像(今已不存)。法號“癡道人”順治皇帝大行之后,遵其遺囑,即于此火化梓宮并做法事,以骨灰人葬孝陵。此后,景山成為清代帝后停靈之所,又建壽皇殿,供奉皇室祖先之影像。史料載,世祖生前喜參禪悟道,尤傾心五臺山,甚至萌生棄帝位出家之念頭,曾委僧人前往預作準備。民間則傳說出家是實,今五臺山清涼寺、鎮海寺、上善財洞等處仍留有遺跡。筆者認為,順治皇帝一生雖未能親去五臺,但其虔誠仰慕之情至死不變。為了了此情、圓此夢,其將宮墻后大土丘仿五臺之狀分為五峰,并囑于此火化,也算是魂歸五臺吧。古漢語中,“景”、“影”同義,取名景山,寓意昭然。爾后五丘之下成為停靈、供像處所,對于崇佛的清皇室來說,五峰所寄托的含義是不言而喻的。
清廷熱衷于為文殊菩薩修廟建寺之例尚多,如乾隆皇帝仿五臺山殊像寺內菩薩瑞相,在北京香山建寶相寺,后又在承德避暑山莊附近仿寶相寺之制建殊像寺,將寺前之水命名獅子河,左側山谷命名獅子溝。乾隆帝創立的滿族喇嘛寺院中,最大的一座是建于香山的寶諦寺,其形制系仿五臺山菩薩頂,供文殊真容。
藏傳佛教亦稱黃教,為蒙藏等民族所共同信仰。文殊菩薩為大乘空宗奠基者、密宗祖師之一,系奉如來法旨將大法東移神州的象征性代表人物,且傳說黃教創始人宗喀巴及清代皇帝均為其化身,故特別受信徒尊崇。清廷以崇信黃教為維系民族團結的“柔遠之道”,誠如康熙皇帝所言,“我朝施恩于喀爾喀,使之防備于朔方,較長城為尤堅固也”。乾隆帝則講得更清楚,“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指達賴、班禪),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
清朝是唯一不修長城的朝代,佛教文化尤其是文殊信仰,對這個疆域遼闊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鞏固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作用至今仍在延續。清朝前幾位皇帝多次登臨五臺山,正是體現上述興黃教即安眾蒙古的政策。
其“崇尚佛教,首尊文殊”被定為一項基本國策,還有著更深更廣的用意。歷代統治者奉行的儒家學說中,嚴格的“華夷之辨”使滿清統治者被視為“非我族類”,康雍乾三朝綿延百年的“文字獄”就是真實寫照。因此,需要抬高另一種學說與之抗衡,既淡化儒學的“獨尊”地位,又能破解其狹隘局限之病,爭取廣大漢族士子的認同,使其統治地位正統化、合法化。在這長期艱巨的“正心”過程中,佛教倡導的眾生平等觀念,特別是文殊菩薩所代表的整套般若學說,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康熙皇帝在《御制南臺普濟寺碑》中講到,“佛氏之教,息心凈業,以獨善其身。而文殊所愿,在饒益眾生。布施以廣仁義,持戒以守信,忍辱以(扌為)謙,精進以施敬,禪定以守靜,智慧以通理”。然而儒學的主流地位畢竟不可動搖,故自號“圓明居士”的雍正皇帝在《御選語錄》卷12《上諭附錄》中指出,“但于日月星之本同一光處,喻三教之異用同體可也”。三教同源既無異教之說,滿漢同根又何來異族之見?“使天下后世,真實究竟性理之人,屏去畛域,廣大識見。朕實有厚望焉”。雍正帝可謂用心良苦矣。乾隆皇帝承繼父祖遺志曾說:“朕以圣王之法治天下,而于法王之法蚤承先訓,深契凈因,故推演至義,為大眾津筏。”他在游五臺的許多詩中也表達了此類思想。如:“清涼名獨占,分別不生心”、“梵宗儒理本無二”等等。嘉慶皇帝在詠東臺詩中也點明“佛法王道,原無異同”。在17、18世紀國內國際空前大變革、大動蕩的復雜形勢下,滿清以一個少數民族對中國實行了260多年統治,且創下封建時代“康乾盛世”之輝煌。這是一筆龐大的
遺產,有太多的地方值得后人思索。
二、非常的文化需要非常的包裝
一天,李白正陪唐明皇在興慶宮內沉香亭飲酒,只見楊玉環分花拂柳,從小徑款款而來。大詩人的視覺受到強烈沖擊,揮筆寫下流傳千古的《清平調》(三首),頭一句就是:“云想衣裳花想容”,道出了縱使天生麗質也需美景美服烘托、包裝的道理。
佛教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勸人向善、自我約束、關愛生態、凈化心靈的作用,尤其文殊信仰中崇尚理智、追求創新的精神,在指導、調節人類思維層面和營造文明祥和的人際關系方面,有著重要而獨到的作用。正因如此,佛教文化歷來是旅游資源中吸引客源的“大戶”,各地景區不惜花大力、投巨資進行打造包裝。浙江寧波市為弘揚佛教文化,規劃以天童禪寺為中心,整治美化周圍環境,建設“東南佛國”。無錫太湖早已是著名旅游勝地,前幾年又開發了靈山景區,建成一座88米高的東方大佛,并有整套的配置設施和多種相關活動項目。如設計新穎的動態雕塑、九龍灌浴、五智門,別出心裁的洗心降魔處、握佛手、抱佛腳等十大景觀。最奇的例子是福建三明市金湖風景區。該景區原本是一處自然山水,通過對河流兩岸山峰、巨石的細致考察和精心包裝,再現了天然逼真的眾多佛教人物造像,如彌勒、如來、觀音、羅漢等等,被稱為“水上天然佛世界”。另外,還有的通過大型專項活動來造勢,如“重走唐僧西行路”中外文化交流活動、扶風法門寺所供佛舍利巡展,承德普寧寺每年兩次的無遮大法會等等。
五臺山的佛教文化資源是千年修成的“正果”,全山化現,得天獨厚,舉世無雙。今日五臺山,從全山格局、寺廟分布、環境營造,到殿堂設置、塑像壁畫、匾聯碑刻,再到遺跡傳說、音樂舞蹈、法事活動等,都是歷代僧眾打造的文化載體,以此再現人間“文殊凈土”,這其實就是傳統形式的包裝。其中尤以“五方文殊”的構想獨具匠心,最富特色。始自隋文帝,“下詔五頂,各置寺一所,設文殊像”,分別為“聰明”、“智慧”、“獅子”、“無垢”、“孺童”,表示五佛五智。清乾隆年間,為方便朝臺,又仿各臺頂文殊造像集中供奉于黛螺頂。其他還有帶箭文殊、甘露文殊、老文殊、金剛文殊等造像。先人在開發建設中,充分發揮了想象力、創造力,并始終以圍繞佛教文化、突出文殊形象為主旨。毫無疑問,這一點也應成為今天規劃、開發五臺山的指導思想。
在本刊編輯部的熱心鼓勵指導下,筆者近年發表了幾篇關于五臺山旅游和景區規劃方面的文章,每篇題目之下都冠以副標題“論五臺山需要包裝”。如此強調“包裝”,實是有感于在現代化大潮中,旅游景區尤其是以傳統文化為主體的景區,更是面臨著空前的挑戰和激烈競爭。我國成規模的真正意義上的旅游業是從改革開放后才出現的,僅有30年歷史。在這之前,各地的旅游資源大多處于原生的自然狀態。比如寺廟自古以來只是僧尼打坐參禪之地,不具備現代旅游的功能,在初期的觀賞型階段尚可應付,若想適應市場變化,跟上時代節拍,與時俱進,就必須推出創新型的包裝。
何為“包裝”呢?簡單來講,對人和事物原始形態的任何附加成分均可稱為包裝。因此,可以說沒有包裝就不會有一個不斷變幻的五彩繽紛的世界。包裝是否成功,取決于對人和事物的深刻理解,還要符合所處時代的審美時尚。在知識經濟時代,包裝已成為一門學科,更注重對客體文化內涵的挖掘和藝術化、個性化的表現,力圖在更深層次上把握人和事物的本質,并尋找與時代精神的契合點。這種“附加”已與客體相融,成為其有機組成部分。每一次包裝都是一次認識的飛躍,都是對人和事物本來面目的一次接近,都是對其價值的一次重估。
五臺山寺院的規模、格局是一代又一代人根據自己所處時代的理念,歷經漫長歲月打造而成的。從現代旅游的角度看,寺廟雖多,但彼此之間不具有內在關聯的有機鏈接。所以,多年來,旅行社在線路的深度設計、開發方面功效不彰,推出的線路基本上是老一套,即固定的幾大寺廟,有的加上幾段不著邊際的所謂傳說,再到某個“靈驗”之處匆匆燒一把香,行程就算結束了。參觀方式的單一和寺廟布局的雷同,使游人容易視覺麻木、感覺單調。總之,佛教景觀多年一貫的老面孔,制約著佛教旅游業的持續發展。近幾年,不斷有寺廟重修或增建、擴建,但仍沿襲以往模式,上述問題未獲解決。我們往往滿足于五臺山頗高的知名度,但從一定意義上講,它更多是一個地名品牌、宗教品牌。如何發揮地名優勢和圣地優勢,向旅游品牌轉化,就需要在資源提煉、整合、包裝上做文章。
如何以時代精神再塑景區形象,主題公園的設計構思可供我們借鑒。修建主題公園,是近些年來旅游開發的一大趨勢。如北京世界公園、西安黃土民俗村、昆明民族風情園、長春世界雕塑園、杭州宋城、圓明園遺址公園、河北邯鄲成語故事苑、吳橋雜技大世界、上海崇明生態島主題公園、山西臨汾堯廟等等。主題公園通常由六大要素構成:
1、人文景觀是核心,是公園的主題。可遷建仿建或重新設計。
2、山水園林。
3、定時舉辦民俗、節慶活動,演出專門量身訂做的文藝節目,如杭州宋城的大型歌舞《宋城千古情》、武漢東湖楚天閣的楚樂演奏。
4、開展游人可廣泛參與的趣味互動項目。
5、標志性的圖案或建筑。
6、完備的服務設施。
由于主題公園能在有限空間內合理配置旅游資源,并可在傳統之中揉入現代元素,做到全景式的典型展示,符合當今快節奏、重體驗的旅游潮流,又能縮短路途耗時、節省費用,故受到游人特別是年輕人和女性游客的青睞。主題公園是一種新型文化包裝。筆者設計的“般若苑”就是游一園知全山的主題公園,它除了上述優越性外,還有著保護景區資源和環境的作用。般若苑的核心是設計富有時代精神的“五方文殊”造像,與此配合,還須設計一款五臺山形象標志,使游人對景區文化特質一目了然。筆者在《六論五臺山需要包裝》一文中對景區形象標志有專門論述,且設計了初稿,可參閱。建議景區或旅游部門向社會征求設計方案,進行篩選。可以說,如果能讓每一位游人在離開景區時,腦海中都有一張生動鮮活的畫面和一款過目不忘的標志圖案,就是一大成功。
“借景”是擴展主題公園空間,烘托主題文化的重要手段。自古以來,在信眾眼中,全山一草一木、一土一石,皆文殊化現。《佛祖歷代通載》卷7說,五臺山“頭出星辰,尾搖日月,方圓五百里,皆屬圣基,乃文殊化身也”。故唐時日本圓仁大師率弟子朝拜五臺山,遠遠望見“清涼峰巒文殊圣域”,便“伏地遙禮,不覺雨淚”。宋代日僧成尋不顧隆冬風雪,跋涉近一個月,“始見東臺頂,感淚先落”。從這個意義上說,五臺山“借景”的資源俯仰皆是,多不勝數。例如1996年崔正森和李安保發現普化寺背靠的貢布山,形狀頗似一佛仰臥,取名“仰天大佛”,召來不少游客觀賞。這是一個好創意,然此名稱
各地多有且無特色,筆者在這里正式向景區建議,將此景更名為“文殊觀天”,形狀既符,也可與“性空幻有”的般若思想產生聯想,更體現了“全山化現”的傳統理念。發現,也是一種創造,是文化勞動成果,對它的命名則屬于包裝,建議有關部門對此類重要的發現勒石留名并予以物質獎勵,并可向游人廣泛征集。
佛教文化的包裝屬于“軟包裝”,歷來是景區設計開發中最大的難點,包裝出來的文化產品須達到三項標準:1、具有宗教淵源;2、內容文明健康;3、形式生動活潑。試以“剪發池”的構思為例作一說明。
在《潑墨鳳林谷工筆般若苑》一文中,筆者勾畫出五臺山主題公園的全貌,“剪發池”屬人文景觀的一部分,也是筆者的一項創意。它的宗教來源出自“貧婆乞食”典故,影響久遠,為人樂道,其喻義發人深省。早期,有的僧尼信眾不惜自殘身體,表達對佛教對文殊的虔誠信仰,在五臺山就有過“燃指朝臺”的駭人之舉。隨著社會的發展,這類舉動不再為人們認同、接受。受上述典故影響,“剪發供佛”出現并流傳開來。這一儀式將身體的一部分——頭發剪下來作供奉,既表達了對文殊菩薩的虔誠信仰和紀念,又避免了對身體的摧殘,是人類文明進步和佛教與時俱進的體現,故至今仍在流行。五臺山正是這一儀式的發源地,他是一份珍貴的旅游資源。對“剪發池”的修造和游客剪發的儀式要巧妙設計,賦予剪發“六根清凈,立斷煩惱”的象征含義。游客通過參與這種活動,既能感到這種形式的新穎,又能獲得心靈上的啟迪,是一項十分有意義的活動。
30年來,我國旅游業發展迅速,但是開發、設計有景區當地特色的旅游紀念品,卻始終是最薄弱的環節。這里關鍵是對“旅游紀念品”這一概念的內涵認識不到位。“旅游紀念品”是什么?它是景區文化的濃縮和延伸,是其藝術性的再現。景區文化的包裝越有特色,紀念品的設計就越能獲得靈感和發揮空間。說到底,旅游紀念品的實質是對景區文化的一種包裝或者是對包裝的再包裝。它是無聲的推介與展示,是吸引客源、增加回頭客的重要途徑。目前,各地景區文化“軟包裝”的不足,已成為制約旅游紀念品開發的瓶頸。
現在,五臺山正迎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景區負責人梁有升先生在“宏圖更起清涼界無限風光在五臺”一文中,描繪了五臺山的美好前景。由政府統一組織的如此大規模、高檔次的開發建設,是前所未有的盛舉,將對景區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我們衷心期待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五臺山的開發取得圓滿成功。多年來,五臺山研究會團結了一批社會各領域的專家學者,致力于五臺山研究,辛勤耕耘,碩果累累,為景區的規劃開發夯下堅實的理論基礎。這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如何通過有效的機制,將他們累積多年的豐富學識包裝成文化產品,轉化為現實成果,是關乎景區下一步開發成功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也是目前尚待加強的一個重要環節。望各級領導明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