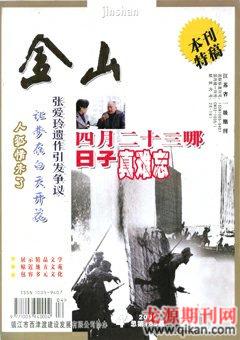《紅樓夢》的語言魅力
鄭 文
讀《紅樓夢》其文,常感氣勢貫通,流暢自然,往往片言只語,而境界全出。不妨摘幾段看看:“士隱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我們試想一下這后面八個字,是不是一幅“炎夏永晝”圖?“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弦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我們試想一下這“飛彩凝輝”四個字,是不是比常用的“皎潔”更美,更靈動?“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鍋火逸,便燒著窗紙。此方人家多用竹籬木壁者多,大抵也因劫數,于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這“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八個字,是不是牽引著我們的視線看到了一條街,且在這“火焰山一般”的特寫鏡頭中,又仿佛聽到“劈劈啪啪”的爆炸聲,感到熱烘烘的氣息?
文字如此簡潔,表達效果卻極佳,充分顯示出曹雪芹語言功力的爐火純青。其中有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他充分發揮了漢語中四字結構的巨大表現力。如果大家對上引文字中四字結構的印象還不夠深,那就請再看一段:“適聞二位談那人世間榮耀繁華,心切慕之。弟子質雖粗蠢,性卻稍通;況見二師仙形道體,定非凡品,必有補天濟世之材,利物濟人之德。如蒙發一點慈心,攜帶弟子得入紅塵,在那富貴場中、溫柔鄉里受享幾年,自當永佩洪恩,萬劫不忘也。”
《紅樓夢》的語言,尤其是作者的敘述語言,是文言與白話的和諧融合。在這樣一種話語系統中,兩個字、三個字構造詞組的能力顯然有限;而五個字以上,又往往不能凝結成相對固定的詞組,在句子中不能作為獨立成分來運用;只有四個字,構造詞組的能力既強,又能作為固定詞組在句子中充當某一種語法成分。舉例說,“擔風袖月”是兩個動賓詞組的組合,“書香之族”是定語加中心詞,“支庶不盛”是一個主謂結構,“愛女如珍”是動賓結構加補語,“聰明清秀”是四個詞的聯合,“名山大剎”是兩個偏正詞組,“既聾且昏”是遞進式詞組,“齒落舌鈍”是兩個主謂結構并列……諸如此類,變化繁多;而它們在句子當中的具體運用,其變化也可謂層出不窮。總之,四字結構往往是漢語中長度最適合、運用最靈活的固定詞組,而這也是漢語中的成語絕大多數都是四個字的根本原因。曹雪芹顯然深諳其中之奧秘,所以他不但能熟練地運用成語,而且能巧妙地運用四字結構,這就使他的敘述語言更加簡潔,流暢,而且生動。
語言的“生動”,不僅要求作者具有修辭煉字的深厚功底,而且要求他能使文字與內容、人物、環境、氣氛等諸多因素互相交融,互相印證,形成和諧統一的整體,才能產生很強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且看《紅樓夢》中一段著名的描寫:“眾人先是發怔,后來一聽,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來。史湘云撐不住,一口飯都噴了出來。林黛玉笑岔了氣,伏著桌子喊‘喲。寶玉早滾到賈母懷里,賈母笑的摟著寶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著鳳姐兒,只說不出話來。薛姨也撐不住,口里的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飯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座位,拉著她奶母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的無一個不彎腰曲背,也有躲出去蹲著笑去的,也有忍著笑上來替他姊妹換衣裳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撐著,還只管讓劉姥姥。”這段絕妙的文字,不但形象地描繪了各人不同的笑態,而且生動地體現出各人不同的身份和性情。作者先總寫眾人從“發怔”到爆發的“哈哈大笑”,再一一分別刻畫:史湘云的笑透著豪爽;林黛玉的笑顯出柔弱;賈寶玉邊笑邊撒嬌;賈母邊笑邊寵孫子;王夫人似乎要批評鳳姐玩笑過當,手指著她,卻笑得說不出話來;薛姨媽盡管是客,“也撐不住”了,但她噴的是茶,因為前面有交代她是吃過飯來的;性格放達的探春把飯碗合到了“溫柔可親”的迎春身上;“形容尚小”的惜春拉著奶母叫“揉一揉腸子”。最后再概述其他人:“也有躲出去蹲著笑去的”,“也有忍著笑上來替他姊妹換衣裳的”,這些是下人,只略寫一筆。而與這一切相對照的,是依然“撐著”的鳳姐和鴛鴦,因為她倆是“逗哏”,故有本領堅持不笑。馮其庸先生評論這段文字道:“作者寫各人的笑態,可以說淋漓盡致,各極其妙,即集古今笑事于一處,恐亦無此恢宏場面。”意味深長的是,在這極盡歡樂的場面描寫中,曹雪芹卻有意“漏”掉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那就是薛寶釵。這仿佛是畫中的留白,樂曲中突然的靜音,引發我們作有趣的猜想:這位以冷靜穩重著稱的“道德楷模”是笑還是不笑?是微笑還是大笑?是矜持還是失態?如果要寫她的笑,究竟該怎么寫呢?可以說,曹雪芹在這里又留下了一個神秘的“哥德巴赫猜想”。
其實,像這樣鋪張細致地描寫,曹雪芹其實也是偶爾為之。他更多地是在簡約中隱含豐富的內涵,需要我們結合人物的言行去仔細體會,主動積極地參與作者的審美實踐。比如,曹雪芹每寫那一僧一道出場,總是伴隨著他們的笑聲,不是“說說笑笑,來至峰下”,就是“揮霍談笑而至”,這樣的描寫我們很容易一讀而過,但仔細一想,其中大有深意存焉!這神仙之笑,首先是因為他們的逍遙自在,不像我們蕓蕓眾生有許多的煩惱;而在《紅樓夢》中,也是為了反襯后面的許多痛苦和悲涼。同時,在這神仙的笑聲中,我們也能體味出一種濃重的滄桑感,令人產生“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的慨嘆。再者,在這神仙的笑聲中,又充滿了對塵世無情的嘲諷,即所謂“笑天下可笑之人”的意思。這樣一想,我們就會對這些瀟灑談笑的神仙產生一種敬畏之感,并感受到一種哲學的意蘊了。
同樣的道理,在“葫蘆僧亂判葫蘆案”那一段文字中,我們也不可忽略那“門子”的笑。他是當年葫蘆廟內的一個小沙彌,卻侃侃而談地向賈雨村“講授”官場之道,并“指導”他如何判案,其間竟一連“笑”了六次,其中還包括兩次令人極不舒服的“冷笑”。嗚呼!無怪乎此人事后要被雨村兄“遠遠的充發才罷”——誰叫你在頂頭上司面前顯出如此精于官場“潛規則”,如此老于世故,且又如此好為人師的呢?活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