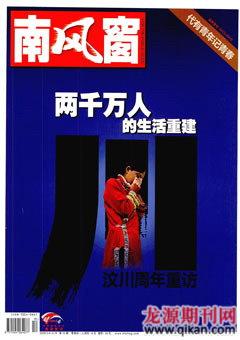《郵政法》修訂留下重大死角
趙 杰
郵政企業及其管理部門受驚于快遞業務蓬勃發展和滲透到信件寄遞業務咄咄逼人的態勢,專心于用修訂《郵政法》來規定、限制快遞企業的活動空間,這正是《郵政法》修訂的重大缺陷。
2009年4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法》(以下簡稱新《郵政法》)經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以146票贊成、4票反對,4票棄權平靜地通過。但是,新《郵政法》在郵政專營權的界定和國家對郵政市場以及快遞市場的管制框架方面,仍遺留下諸多懸而未決的難題。市場各方表面的平靜反應背后,對新《郵政法》實施的擔憂卻與日俱增。
雖然在關鍵條款“郵政專營權”問題上,新《郵政法》采取回避態度,僅作原則性表述:“國務院規定范圍內的信件寄遞業務,由郵政企業專營”。外界流傳的“信件郵政專營范圍降低為150克以下”的條目在新《郵政法》中并未出現,民營快遞公司的存廢前景仍存在變數,但是新《郵政法》重點突出郵政普遍服務價值取向、暫時擱置“郵政專營權”的內容爭議,仍讓人們看到《郵政法》修訂的開放姿態和快遞業的發展曙光。
快遞公司的“原罪”
快遞業務的發展,在中國郵政管制的框架中,天生就是個“沒娘的孩子”。雖然在中國老《郵政法》中,從來就沒有快遞業務、快遞企業的管制框架和管理用語,但是快遞業務卻日益壯大。
據新華社報道,快遞目前已經成為我國發展最快的業務之一,近幾年來保持了年均20%以上的增長速度。目前在郵政管理部門登記備案的快遞企業有5500多家,從業人員約30萬人,年產值在400億元以上。國內快遞企業雖然存在發展不平衡,企業規模較小,市場秩序不規范,服務質量參差不齊等現狀,但若不理清快遞業的管制框架,非郵政快遞企業的“原罪”必然會嚴重制約其發展。
從2003年修改《郵政法》被列入十屆人大立法計劃開始,圍繞著郵政專營權的內容規定及其運行機制,各方進行了錙銖必較似的博弈:2003年的《郵政法(修訂草案)》第五稿強化了郵政的專營范圍,規定“500克以下的私人快遞業務由郵政專營”,經過2004年第六稿、2006年年初第七稿“國家郵政局專營的快遞業務重量由500克下降到350克”,直到2006年8月第八稿“信件郵政專營范圍降低為150克以下”,以及最近流行的“重量加資費”標準來確定郵政專營范圍(即規定單件重量以及資費均在一定標準以下的寄遞業務由郵政企業專營)。
頒布于1986年的《郵政法》,需要修訂的內容和環節很多。民營快遞公司成為該法修訂的重要訴求主體,皆因快遞業務在老《郵政法》和郵政部門規制之外誕生的“原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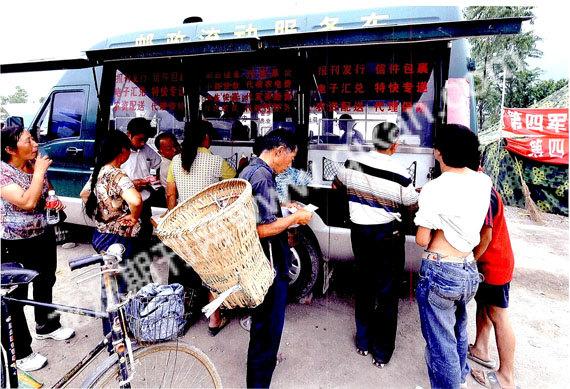
最先,郵政專營權是靠郵政企業的獨立運行來保障的,中國郵政部門在速遞市場中的占有率幾乎為100%(直到1987年以前仍保持在95%以上);1986年的《郵政法》在明示郵政企業專營信件的寄遞業務時,已為非郵政部門經營商業文件快遞業務留下了“后門”:它規定“信件和其他具有信件性質的物品的寄遞業務由郵政企業專營,但是國務院另有規定的除外”。但是,老《郵政法》并沒有對快件業務及其經營者進行界定,也沒有否定非郵政企業可以經營與郵政企業寄遞業務相似的快件業務。
1992年開始,交通、鐵路、民航等部門都獲得了對速遞業的審批權,批準了一些國有速遞企業。于是,民營企業通過掛靠在這些部委審批的速遞公司,繞開了郵政專營權的管制,得以生存發展。
1995年6月29日,國務院批準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貨物運輸代理業管理規定》指出,經批準成立的國際貨物運輸代理企業可以從事國際快遞業務,但私人信函除外。這為外資速遞公司由經營快遞業務中的貨運業務,滲透到經營信件速遞業務,打開方便之門。郵政的專營權受到民營企業蠶食的同時,又面臨外資快遞企業的挑戰。
郵政管理部門也面臨“原罪”
伴隨著郵政專營權的喪失和傳統郵政規制的被突圍,面對20世紀60年代興起于美國并在世界范圍內蓬勃發展的新興快遞產業的步步進逼,郵政管理部門和國有郵政企業也陷入另一種“原罪”:不重新界定清楚郵政普遍服務與快遞競爭性業務,傳統郵政企業徒具合法存在理由卻日益失去市場空間。
于是,以2002年國家郵政局發出《關于貫徹信息產業部等部門有關進出境信件寄遞委托管理文件的通知》(簡稱國家郵政局64號文)為標志,在老《郵政法》沒有界定快遞業務屬性和范圍條件下,快遞業務的管制權爭奪進入公眾視野,并被拖入新《郵政法》的修訂歷程中。
其實,1994年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達成的《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已經區分了郵政服務(Postal services)和信使服務(Courierservices)是不同的業務類型,與此對應,我國各行業管理部門對郵政業務與快遞業務屬于兩種不同的服務類型,并無爭議和分歧。
郵政專營權引發出管理部門的管制“原罪”在于:非郵政部門經營的快遞業務(包括航空快件、鐵路包裹等),究竟必須經過郵政部門的授權才合法呢,還是可以由各自的行業管理部門批準即可?換句話說,郵政專營權的實施是否就蘊涵著自動賦予郵政管理部門對郵政郵件業務(郵政部門遞送)和非郵政快遞業務(非郵政部門遞送的快件)的管制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貨物運輸代理業管理規定》指出:“國際快遞業是國際貨運代理業務的一部分”,經原外經貿部批準經營國際快遞業務并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記注冊的企業,均享有合法經營權。而且外經貿部是國務院授權管理國際貨運代理業務(包括快遞業務)的主管部門;又因為1998年1月,民用航空總局根據航空法,頒布了《中國民用航空快遞業管理規定》,航空快遞業務成為民用航空總局行業管理對象。上述兩個行業規定,并沒有挑戰郵政專營權,卻自行規定了快遞業中的兩個重點領域——作為國際貨運代理的國際快遞、航空快遞的管理范圍。
與郵政專營權的被肢解相伴隨的是郵政體制改革:1998年獲利最豐的電信被從郵政系統剝離,1999年,國家宣布逐年取消郵政補貼,2005年8月,國務院通過《郵政體制改革方案》,郵政體制改革大幕由此拉開,原屬郵政的郵政儲蓄業務也與郵政“分家”,于是捍衛郵政專營權一方面成為郵政企業的生死劫,另一方面也是郵政管理部門鞏固管制地位的一張牌。
冷靜來看,郵政服務與信使服務、郵政業務與快遞業務、郵政專營業務和競爭性業務可以統歸郵政管理部門管理,但按照“專業專營、同業同策”的管制原則,郵政管理部門必須劃清郵政服務(郵件的普遍服務業務)與信使服務(非郵件的競爭性業務)的管制界限。這是新《郵政法》賦予郵政管理部門全行業全業務管理權的必要條件。目前,新《郵政法》雖有第十八條“郵政企業的
郵政普遍服務業務與競爭性業務應當分業經營”的郵政企業內部業務區分,但這遠不如上述國家郵政管理局管制業務大類的區分重要。這是郵政管理部門實現全行業全業務管理的一個總綱。
《郵政法》修訂的重大缺陷
《郵政法》的修改,本應該厘定重大的郵政業發展理念和討論制定相應保障規則。郵政企業及其管理部門受驚于快遞業務蓬勃發展和滲透到信件寄遞業務的咄咄逼人態勢,缺乏探索保障郵政普遍服務的新的運行體制和財政保障機制的新思維,卻專心于用修訂《郵政法》來規定、限制快遞企業的活動空間,這正是《郵政法》修訂的重大缺陷。
從現有條目來看,新《郵政法》的管理半徑是很大的,既包括對郵政普遍服務的管制權(狹義的郵政行業管理),還包含了對非郵政部門提供業務的管制權(廣義的郵政行業管理,即“郵政服務+快遞業務”)。但是新《郵政法》全文和附則都缺乏對郵政市場的描述,這成為一個修訂死角。
郵政市場是何物?1986年的老《郵政法》因為誕生在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前,沒有也不可能規定。國內民營快遞企業和外商投資快遞企業在國內發展如火如荼情勢下,新《郵政法》顯然想依據此法,實現郵政市場的全行業管理。但是,新《郵政法》總則第一條“為了保障郵政普遍服務,加強對郵政市場的監督管理”,第四條“國務院郵政管理部門負責全國的郵政普遍服務和郵政市場的監督管理工作”,這兩條都是將郵政普遍服務與郵政市場并列在一起,卻讓人摸不著頭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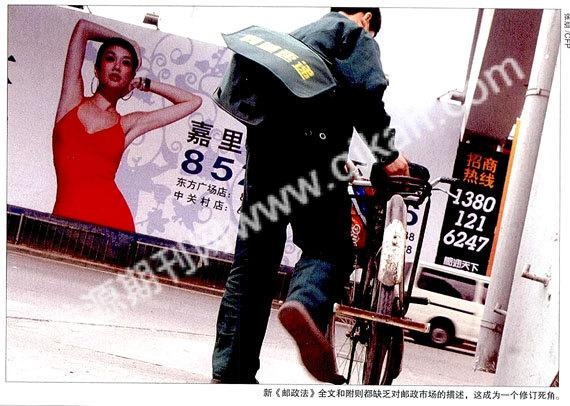
聯想到郵政普遍服務由郵政專營權規定,通過郵政企業運行提供,郵政市場就應該是非郵政企業經營的快遞等競爭性業務市場(至多再加上郵政企業經營的競爭性業務),它對應于廣義的郵政行業管理。
而聯系新《郵政法》對郵政企業、郵政普遍服務、提供郵政普遍服務的郵政設施、郵政營業場所或者郵件處理場所、郵政服務、郵政資費等術語的使用,郵政市場似乎僅僅特指郵政企業所提供服務的交易市場(即狹義的郵政專營市場),而非郵政企業提供的快遞業務被排除在郵政市場外,只不過需“依照本法規定取得快遞業務經營許可”并因此納入郵政管理部門管理。這個意義上的郵政市場,又對應于狹義的郵政行業管理。
筆者認為,新《郵政法》應在網絡經濟、信息社會、服務業發展背景下,順應快捷的、門到門的、個性化的快遞業務方興未艾趨勢,在不影響和限制新興的快遞業發展前提下,探索和解決好郵政普遍服務的運行方式和補償機制問題。至于郵政管理部門監管郵政企業和郵政市場的問題,則需要立法和管理的新思維,即明確界定郵政市場究竟是郵政企業專營的自然壟斷性市場,還是一個包括郵政企業壟斷專營市場和非郵政企業經營的快件市場在內的混合市場。
總之,新《郵政法》雖然已經通過,但是郵政管理部門若無視快遞物流作為電子商務發展的物質保障手段,具有服務業發展的巨大市場空間,仍以部門立法的思維來管制快遞業,定會遭遇諸多實施難題。只有用更加開放的態度,解決好郵政業、物流業共同成長中的“管制煩惱”,理順中國服務業發展中的政府責任和政府管制思路,新《郵政法》及其配套規定才能順利實施,社會上各類快遞企業和快遞消費者才能獲得和享有新《郵政法》對中國郵政事業、快遞物流業發展的積極影響。
我們冀望未來將制訂的《國務院關于郵政企業專營業務范圍的規定》(2009年1月7日,國務院曾下發2009年立法工作計劃,明確規定將出臺《國務院關于郵政企業專營業務范圍的規定》)將郵政企業普遍服務職能的履行及其財政保障機制的建立,作為“規定”的重點。同時,管理部門能順應快遞業、物流業、電子商務、生產性服務業相互融合相互滲透發展的趨勢,制訂《快遞業務經營許可管理辦法》、《快遞市場準入管理辦法》等法規、規章,不再糾纏于郵政專營權的信件的“重量”細節,在“穩住郵政普遍服務一點”基礎上,放開“快遞市場一片”。
只有這樣,才能打消郵政企業和郵政管理部門借提供郵政普遍服務之責,逼迫蓬勃發展的快遞市場企業就范的部門立法嫌疑。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