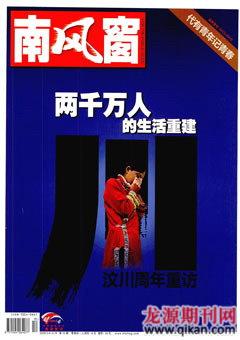黑白南京外的人性色彩
陶 杰
《南京!南京!》公映了,得力于中國電影不分等級的制度,據(jù)說為了照顧少年兒童觀眾,剪掉了20分鐘的血腥暴力鏡頭。
這樣一剪,就增加了電影的“客觀中立性”——日軍殘殺中國平民的“歷史鐵證”消失了,相反,日軍攻占南京之后的太鼓祭祀,一不血腥,二不暴力,充滿了“文化深度”,居然還一刀不必刪剪,加強(qiáng)了日軍的威武形象。尤其是幾個(gè)仰拍角度,把站在平臺上擊鼓的日本武士,在陽光之下,顯出十足的陽剛味,真是一支“威武之師”。《南京!南京!》最后這幾個(gè)日軍擊鼓的體育項(xiàng)目,不只教人誤以為是日本大導(dǎo)演市川昆的《1964年東京奧運(yùn)會》的日本運(yùn)動員出場陣容的風(fēng)格,叫人一揉眼睛,還差點(diǎn)以為是1936年柏林奧運(yùn)會納粹德國的萊妮·里芬施塔爾歌頌日耳曼民族的大手筆。
《南京!南京!》是一部別開生面的好戲,要點(diǎn)就在這里。觀眾一心以為,會看到的是日軍在南京屠城一個(gè)月的足本,引證“死難者30萬”的官方數(shù)字。可是導(dǎo)演著墨在“慰安婦”的主體戲,而且還時(shí)時(shí)強(qiáng)調(diào),日軍殺人有“政策”,要把軍人和平民“嚴(yán)格分開”。編導(dǎo)忠于史實(shí),讓觀眾看到,原來慰安婦也有日本女人,其中的一個(gè),名叫小百合,還害得多情種子,日軍主人公角川苦苦相思了一回,浪漫之情,尤為動人。
實(shí)際上,《南京!南京!》的主人公,不是高圓圓演的姜老師,不是劉燁演的英勇就義的國軍,更不是范偉飾演的胖翻譯唐天祥,而是面目清秀的日軍角川。影片的第一個(gè)鏡頭,就是角川在行伍途上,坐在路邊,抬頭凝望著青灰的天空。導(dǎo)演搶先向觀眾提出了角川的“視點(diǎn)”,片中許多情節(jié),包括最后槍殺姜老師,皆以日本人角川的視點(diǎn)出之。電影角色的視點(diǎn),眾所周知,也是一種話語權(quán)。中國的戰(zhàn)爭電影,從《平原游擊隊(duì)》開始,話語權(quán)都牢牢掌握在李向陽之類的我方英雄手上,然而這一次不一樣了,日本的觀點(diǎn),也充分“包容”了一下,不但照顧了中日關(guān)系,還確保影片能突破框條,解放思想,成為中國抗戰(zhàn)電影系列一座新世代的里程碑。
除了角川,另一個(gè)日本軍官伊田,雖然殺人如麻,也有“人情味”的一面:他進(jìn)了城,逗著中國的小孩玩,給他們糖吃,帶他們一起上街,這個(gè)場面,叫人想起姜文的《鬼子來了》。伊田的名言,是“活著比死更難受”這句話,為中國人的老話“好死不如歹活”提供了某種哲理上的“互補(bǔ)性”,也許受了這句話的感召,唐天祥明明有機(jī)會逃生的,由于日軍“只能活一個(gè)”的規(guī)矩,他與一個(gè)不知名的老鄉(xiāng)毅然交換了身份,自己赴死了。殉難之前,伊田給他點(diǎn)煙,勉勵(lì)他“一路走好”,然后,唐天祥笑著說:“你知道嗎?我老婆又懷孕了!”這句含蓄又辛酸的話,比從前看抗日英烈的標(biāo)準(zhǔn)臺詞“殺吧,中國人民是殺不盡的”之類。有了藝術(shù)上的提高。看了《南京!南京!》,我們才會為中國電影在藝術(shù)之路上的邁步而可喜,又為這一邁步,畢竟耽誤了許多年而惋惜。
由于影片的多個(gè)片段,有這種可疑而可堪玩味的“思想灰色地帶”,不知道《中國不高興》的知識憤青一族,對于一些貌似“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fēng)”的場面,作何詮釋,有何感想?《南京!南京!》的最大看點(diǎn),正是其整體的“客觀持平”,而且因中國電影缺乏分級制,是官方的剪刀協(xié)助達(dá)到了“持平”。相比之下,李安的《色戒》,女主角王佳芝,何嘗不是像角川一樣,在殘酷的戰(zhàn)爭之前,因?yàn)樾詯鬯艘话眩鴮Ω髯缘拿褡迨姑挟a(chǎn)生了動搖,為什么王佳芝的形象,與傳統(tǒng)抗戰(zhàn)電影《野火春風(fēng)斗古城》里的金環(huán)不同,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反而角川這個(gè)日軍角色,相當(dāng)正面,與老演員方化扮演的“日本鬼子松井”之流,大相徑庭,就沒有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這個(gè)問題,不免讓人略有納悶之感。
無論如何,《南京!南京!》是一出好戲,好在不太“中國”,好在整個(gè)調(diào)子上,跟60年代的李向陽們,在形式上分道揚(yáng)鑣,藝術(shù)創(chuàng)作就是這回事,在黑白之間,灰色更引人入勝;在陰暗和光明之間,還有許多艷麗的色彩,《南京!南京!》描寫的人性色彩很豐富,雖然是黑白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