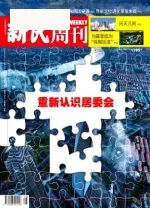是什么縱容著抄襲和造假?
鄧聿文
最近被揭露出來的論文抄襲事件越來越多,而且很多抄襲者已經不是一般的學生、老師或學者,而是擔任一定領導職務的高校領導。例如,遼寧大學副校長陸杰榮、廣州體育學院院長許永剛、廣州中醫藥大學校長徐志偉等都涉嫌抄襲,而本月15日,西南交大向社會通報了對該校副校長黃慶抄襲事件的處理結果:取消黃慶管理學博士學位,撤銷其研究生導師資格。
樁抄襲案的認定需要花些工夫,然由此亦可見當它涉及到領導人時處理起來是何等困難。所幸黃慶畢竟得到了處理,西南交大這所百年老校沒有因為一個副校長的抄襲而對其“護短”,維護了自己的學術尊嚴。然而,更多的是對領導的抄襲行為不了了之,或處理起來輕描淡寫,例如,昆明中醫學院學術委員會對其院長顯而易見的抄襲行為居然“創造”了一個“過度引用”的詞匯為其辯解,院長的“面子”是得到了維護,但學術委員會的“學術”形象也在這一聲“過度引用”中轟然倒塌,并成為世人的笑柄。
論文抄襲不過是當今愈演愈烈的學術腐敗之一種。在目下的大學、研究機構等過去被視為凈土的學術界,正如一些論者所言,從學者抄襲到教授行賄、從招生作假到文憑注水、從教師走穴到導師雇工、從虛構履歷到偽造成果、從掠奪項目到竊取獎項,種種學術不端和腐敗屢見不鮮。學術的意義在于求真,誠實被認為是治學的最基本的態度。學者也因此而受到公眾的敬仰,甚至被視為社會的良心。假如誠實這一基本的治學品德在學術腐敗中大面積喪失,那么,其對社會產生的危害甚至比官員腐敗還要大。因為高校和學者們還擔負著教書育人的重任,而學生的素質直接關系到一個民族的未來。
現在的問題是,面對著普遍化的學術腐敗和學術不端行為,我們似乎拿不出有效的辦法來對付,以致很多學術中人和普通民眾對抄襲等都不以為恥。
抄襲當然是個人的品德問題,但到抄襲成為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時,就必須追問其背后的制度因素了。
一個時期社會的思想、價值和觀念,是依附于該社會而存在的。社會環境的變化必然會導致它們發生相應變化。中國的改革和社會轉型被認為是千年未有之變局,其對人們思想和觀念的沖擊肯定前所未有,在一個一切皆變的社會中,原本一些是非分明的價值和觀念也會變得模糊,從而給人們思想和道德造成極度混亂。
學者們并非生活在真空中,大學也非真的象牙之塔,社會的發展和變化必然會影響到他們。所以,追本溯源時,我們一定要把種種學術腐敗放到社會變革的環境中來觀照。一個無序和失范的社會其產生的種種問題肯定比一個有序和規范的社會要多得多。當下的社會變革和思想混亂,為學術不端和學術腐敗提供了豐厚的“土壤”。
如果說社會變化為學術腐敗提供了一大的歷史背景,那么,盛行于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學術評價體系則直接催生了學者們的抄襲行為。目前的學術評價體系重量不重質,而且與一個人的利益和榮譽掛起鉤來,如果沒有一定數量的論文,你就很可能不能畢業,也不能晉級和晉升,以及獲取科研經費等。量化的學術評價體系本來就容易制造學術垃圾,當一個人的前途和利益只能被文章的數量和刊物的級別所左右時,客觀上會對人們產生一種“負激勵”,即只要事后的懲罰成本不大,人們就有動力采取包括抄襲、造假等手段和方式,尋求論文的發表。
問題恰恰是,懲罰機制發揮不了作用。雖然教育、科研主管部門和高校、研究機構出臺了不少懲罰學術腐敗的規定和條例,但這些懲處條例看起來有聲有勢,給人的感覺卻是高高舉起,輕輕落下,欠缺實際的東西。這從前述有抄襲嫌疑的校長們得不到及時處理可見一斑。另外,有關知識產權和著作權的法律對論文抄襲、學術造假等行為的懲罰也較輕,通常只有經濟賠償、公開道歉,威懾力不夠。特別是對于一些被侵權人來說,真要通過司法途徑來維權,成本很高。懲戒的“寬松”無疑會縱容人們去抄襲或造假。
上述幾個方面并不是單個發生作用的,而是互相強化,互為支撐。但貫穿于中,將它們串聯起來的,則是權力。無論是學術資源的分配、學術評價體系,還是社會風氣和個人品行等,都與某種權力的嚴重濫用有關。
由此來看,要整治學術腐敗和學術不端行為,釜底抽薪的辦法是改革現行的官本位的學術體制和教育體制。不過,這是一個長期的問題,而且也非教育界和學術界的力量所能動搖的,必須有政治層面的變革來配合。這是一個方向,我們可以朝這一方向努力,但當下的反腐重點,則在于學術評價體系的改革,發揮輿論和社會的監督力量,以及修改知識產權法和著作權法,加強法律的制裁;同時,借鑒國外的一些做法,建立起學術界的自律機制,發揮團體懲戒作用。
但愿西南交大對黃慶抄襲行為的處理能夠打開一片天地。(作者系中央黨校學者,知名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