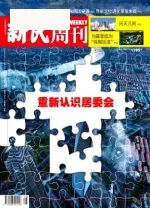嚴培明:為蒙娜麗莎“送葬”
楊建勇
在這一堆畫布前,舞動長刷,肆意揮灑,在塑造蒙娜麗莎的同時解構著蒙娜麗莎。在他筆下的蒙娜麗莎眼里含著淚水,表達了“死亡”的主題。
2009年對嚴培明來說相當重要,他同時在中國、法國、美國的頂級藝術館舉辦大型畫展。上個月,北京798尤倫斯基金會藝術中心為他舉辦了個人畫展,這個畫展將歷時四個月。
《童年的風景》是嚴培明藝術作品中第一個帶有裝置形式的作品。藝術家直接在大展廳的墻壁上作畫,34面旗幟繪制了全球背景下的兒童肖像,用旗桿倒掛,固定在離地面1米的地方,34臺功率強大的鼓風機所產生的音量和風力,讓整個作品在2500平方米的空間內瘋狂延伸,從銀色的墻到銀色的“國際風景”,整個空間被賦予了象征意義,即在一種和平的狀態下如何看待生命的意義。旗幟透明的特性凸顯出生命特別是兒童生命的脆弱,也將他們生存的普遍問題重新拉回到觀者的視線中。
走在排列整齊的兩排旗幟間穿越展廳時,會聽到強大的風聲,風聲下孩子們的臉在顫栗,并且高聲吶喊。當你到達巨幅的“國際風景”前,風景變得很抽象。抽象背景后面34幅迎風招展的旗幟,讓人有一種在船上的感覺。“想象是一艘軍艦,所有的旗幟迎風而動,而我們就是在這船上進行著生命的旅程。”嚴培明這樣解釋他的作品。
一般而言,旗幟不升到頂通常意味著死亡,譬如降半旗致哀,而現在連旗桿也倒了,是否代表著一種對死亡的顛覆。“我不怕死,只是害怕不能活”,藝術家用這種方式來應對關于“死”的思考。作品讓觀者體驗如同在人的面孔和城市景觀中穿行。他用震撼的方式將死亡、貧窮、饑餓、不平、戰爭等問題以人物肖像的形式作出主觀闡釋。在這里,聲音成為作品重要的組成部分,無限延伸與擴展了作品的內涵和感官沖擊力度。
UCCA館長杰羅姆·桑斯表示,“嚴培明以當代標志性人物為對象創作肖像畫。他的作品在國際當代藝術界占有一席之地。”
在北京這個畫展前,嚴培明已經在巴黎掀起了一波狂瀾,那是由蒙娜麗莎引發的。地球人都知道,自達·芬奇以后,蒙娜麗莎發生了很多故事,六百多年來她就像還活著一般。從20世紀開始很多藝術大師在這幅世界名作身上表達著自己的觀點和思想。馬塞爾·杜尚在蒙娜麗莎的臉上加了山羊胡子,攝影師哈爾斯曼將蒙娜麗莎的臉置換成達利那怪異的面容——鼓瞪雙目,翹到眉毛的達利式胡子,青筋突起的手中塞滿了錢幣等等,所有這些都在講述著一個故事。
現在,嚴培明在盧浮宮的這個畫展,標題就定為《蒙娜麗莎的葬禮》。在距盧浮宮鎮館之寶達·芬奇《蒙娜麗莎》原作30米的地方,嚴培明要為這個藝術史上最偉大的美人舉行一場葬禮。我最先看到了草稿,看到了在一片銀灰色中顯現的蒙娜麗莎,后來為期三個月的《蒙娜麗莎的葬禮》在盧浮宮德農廳揭幕,我又看到了3米高五幅一組的大幅畫作,看到了獨特的嚴氏繪畫語言——依然否定色彩,回避色彩。嚴培明用了很長時間,在這一堆畫布前,舞動長刷,肆意揮灑,在塑造蒙娜麗莎的同時解構著蒙娜麗莎。在他筆下的蒙娜麗莎眼里含著淚水,表達了“死亡”的主題。
嚴培明說:“蒙娜麗莎在藝術史上一直是一個謎,在過去的20世紀,很多藝術家就蒙娜麗莎嘗試過新的挑戰,如今21世紀,我想再增加一個新的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