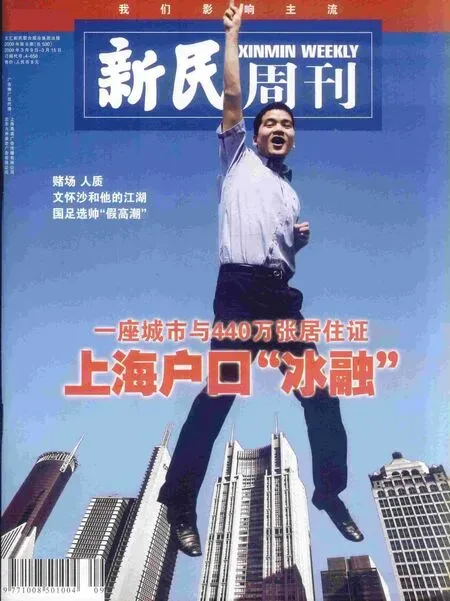突破基尼系數的盲區
張仲禮 王泠一 陳莉莉

我國社會當前的關鍵問題并不是去直接關注基尼系數的大小,而是應該高度重視解決農民工問題。特別是要允許和加快人口流動的同時,逐步解決城市的“農民工”問題。
當前,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危機因素還沒有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各國政府都在尋求良策以謀求宏觀經濟的穩定性。與此同時,各國尤其是抵御這場危機的主流國家的經濟學家們,也開始了嶄新的戰略思考和理論反思。這種思考和反思主要集中在兩個領域——國民生產與收入分配。其亮點分別是:在關于“國民生產”的研究領域,開始在批判GDP崇拜;而在關于“收入分配”的研究領域,已經突破了基尼系數的盲區。上海社會科學院年輕的經濟學人權衡研究員,在他的著作《收入流動與自由發展》中,對后者有著深刻的闡發。
權衡來自于西北腹地蘭州,對于東西部之間的發展差距感性認識豐富。因而,在上海獲得博士學位之后,他開始致力于一項長期的科研項目——貧富差距與分配公平的系統研究。為此,權衡還去了印度——這個據說和中國有很多類比性的國度進行貧富差距的實證調研。在那里,他發現用單純的西方經濟學概念如基尼系數來進行中印兩國社會生活中的貧富差距比較,已經很難得心應手了,必須進行一些必要的符合發展中國家實際的修正或補充。
一般的讀者都了解,運用基尼系數這一相對傳統的分析工具,也能夠大致判斷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均衡水平;那么,經濟學家為什么又要對它進行深刻的揚棄呢?經常參與國際高級學術討論的權衡在他的新著中開宗明義:目前,發達國家對于收入分配的考察,已經開始從原來關注靜態意義上的基尼系數轉向研究對收入流動性的動態分析;而較強的收入流動性,特別是當向上的收入流動大于向下的收入流動時,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沖突就會大大降低和減少。這一嶄新的理論視角及其系統思維,是改革開放30年后繼續前進的中國社會所迫切需要的。而2009年2月,訪問英國——這一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故鄉的中國總理溫家寶也這樣斷言: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要威脅社會穩定。這一斷言,也贏得了英國朝野的廣泛尊敬。
顯然,這不是一個偶然的巧合,而是東西方宏觀經濟治理思想的有效交融。這也使我們發現原先的基尼系數概念,在現實的工具運用上已經出現了明顯的盲區。那么,盲區主要表現在哪里呢?權衡認為,基尼系數概念誕生80多年來,雖然是國際機構曾經普遍采用的一種度量收入差距的分析工具,但是這一工具的運用前提很明確——市場經濟發展極為充分、信用制度和相關體系健全、統計指標和工具比較完善,等等。也就是說,基尼系數概念的適用條件決定了它自身的局限性。尤其是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基尼系數作為一個衡量收入差距的“總量概念”,無法真實地反映收入差距的“結構差異”,而且忽略了大國發展的空間和區域的不平衡、階段性差異以及各地錯綜復雜的異質性因素。因此,這樣的基尼系數比較以及直接套用“0.4的國際警戒線”結論,并以此作為政策設計的依據,不僅存在著一定的盲目性,而且無助于社會貧富差距問題的有效解決。
因此,基尼系數在現實中國的適用過程中,必須充分考慮到大規模人口流動因素對城鄉收入差別、地區收入差距擴大所產生的抑制效應甚至是緩解作用。如果簡單地使用數字計算結果表示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和地區收入差距,忽略人口流動因素對收入分配的積極效應,必然是不符合我國當前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的現實情況。所以,權衡特別強調:我國社會當前的關鍵問題并不是去直接關注基尼系數的大小,而是應該高度重視解決農民工問題。特別是要允許和加快人口流動的同時,逐步解決城市的“農民工”問題,使得他們能夠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逐漸獲得市民待遇,特別是解決他們在城市的住房、子女教育、基本醫療和社會保障等,確保他們能夠順暢地自由流動,在流動中獲得穩定的收入,進而緩解城鄉收入差距和地區收入差距。
當然,這里涉及到為城市“農民工”提供完備的公共服務大課題,其較為完全的解決還有待于我國社會生產力的充分發展。畢竟,中國是個地域遼闊的國家,各地經濟差別和財政投入力度的明顯不同,直接產生了社會政策在民生領域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并不值得肯定,但卻是我們可能在2020年之前都必須面對的現實。如關于義務教育階段的責任問題,筆者也在上海曾經進行過專項調研,從中可以到破解流動中的民生難題的艱難。
我們生活的上海,雖然號稱是海納百川的城市;但一個“納”字,卻也有很多文章可做。以前我們對于“納”字,往往理解為吸收——即積聚資金、技術和勞動力;現在,我們站在世博時代的認知水平上,“納”字則更加突出給予新上海人以身份認同以及他們極其看重的子女在滬接受公平教育的問題。子女受教育的權利,在新上海人眼里甚至被看得比參加人大投票等政治權利更重。但是,如果沒有雄厚并且長期良性循環的財力作基礎,“納”字是不會被大寫的。有位基礎教育界的管理人士這樣告訴筆者:“農民工”子弟的西部或中部家鄉,國家已經將9年義務制教育經費撥付到縣級教育部門;東南沿海城市的公立學校吸收“農民工”子弟入學,勢必要動用本地的公共財力。因此,最公平的做法是實行基礎教育券制度,由“農民工”子弟輸出地的教育部門發放,東南沿海城市的公立學校接收,經費不足部分也就是東西差距由輸入地的教育部門進行補貼。不少同業人員贊同他的觀點,但筆者以為這樣“絕對公平”的制度安排,在目前流動性廣而且會出現回流的中國社會是很難實施的。更為現實的思路是,東南沿海城市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不加索取地盡可能改善“農民工”子弟的教育環境。
可喜的是,相當多的地方政府也已經在現有條件和中央政府的積極引導下進行破冰式的試驗。如在上海,“農民工”的概念已經逐漸被新上海人的稱謂所替代、其子女已經能夠進入上海公立學校接受基礎教育、針對性的社會保障體系也在初步建設之中。而最近,世界經濟增長的衰退跡象對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帶來了負面影響。面臨新的挑戰,我國中央政府和各地地方政府都及時地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新政策、新舉措,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只是,在這些一攬子促進發展的政策和舉措中,被聚焦的往往是經濟刺激方案,而對于社會發展尤其是基礎教育的投入及其可能帶來的新機遇,則關注較少。
事實上,2008年第四季度中央新增的千億資金中就有44億明確作為教育投入。這部分新增教育投入,總計惠及學校將超過2000所、學生100多萬,直接加大了“十一五”后期基礎教育和諧公平發展的力度,同時對中西部地區的中長期發展意義重大。
和中央的舉措相呼應,上海積極推出了以“兩個確保”為目標的8項措施。其中,促進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和保障新上海人子女教育權利的舉措,被認為是加強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的重要組成。上海的這些新舉措,也令人鼓舞地把“公平”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值得指出的是,公平是一個涉及社會、經濟、文化、道德等多個范疇的概念。它著重強調機會公平和規則公平,而對基礎教育的積極投入與均衡教育差別的努力,又是機會公平和規則公平的一面鏡子。同時,教育領域公平發展的社會也將對經濟增長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而就上海的相關新舉措而言,我們就可以判斷出未來發展的新質量。今天的教育公平力度將積極折射出明天的經濟發展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