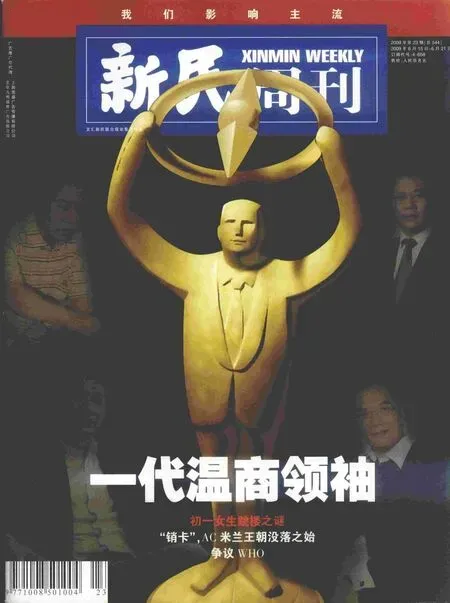看小白的看
黃昱寧
我不知道這樣讀是否正中小白的心意:被他引導著,看他要你看的東西,并被這些東西迷住或激怒。
比起一般的隨筆集,《好色的哈姆萊特》可以算是少見的體裁統一、思路連貫。但小白及其作品并沒有因此就更容易概括,簡直是一概括就死。性文化考?色情史?視覺藝術論?還是更為曖昧的“準風月談”?這些都是可以預見的,必將出現在書訊、書評中的詞匯,洋溢著某種既鋪張華麗又言不及義的喜劇意味。也好,其實這正是最適合讀小白的語境——唯有充分浸淫在這樣的喜劇現場里,你才更能讀懂下面這般一本正經的、用學術腔耍寶的句子:
“顯然此時的秋千已從儀式發展成為一種單純的娛樂。在古代以裙袍為主的服裝式樣下,這項娛樂之向著色情演化,幾乎具有必然性。從賈寶玉的酒令‘秋千架上春衫薄到洛可可畫家弗拉戈納爾的秋千畫,都突出了秋千為觀看女性身體提供的便利。那衣衫輕盈的少女在秋千上翻飛,瑪麗蓮·夢露被地鐵出風口吹翻裙裾,只能算是色情的一閃即逝的幻燈片,秋千能夠不斷變化新的角度,像一架色情的萬花筒,令架下的男性目光應接不暇。秋千上的看,是機會主義的看。唯其機會主義,所以更讓人肉緊,更覺得刺激。秋千上的被看,是冒險主義的被看,吊索大幅搖曳,暴露遮掩之間,平衡搖擺于微妙的支點上。”(《吊起身子提起腿》)
各種“主義”的大帽子,在小白筆下,屢屢給精確地扣到被“主義”不屑、讓“主義”尷尬的細節——小房子,黃段子,秋千架上,鏡像深處,絲襪頂端,裙擺下沿。以我對白兄的了解,他對于尋找“準確詞語”(motjuste,法語,我加上這個括號是為了現場演示一下小白的行文習慣,他的括號里永遠塞滿了各種煞有介事的深奧原文)的興趣,絲毫不亞于對所謂“史實”的考據——如果“史實”本身沒有被小白獨特的寫作方式消解的話。為了能靠近目標,他對于形容詞和名詞的推敲,用陳村的話是“虐戀”,用他自己的話是“濫用”,而在我看來,無論性質如何,也不管他究竟是如何辦到的,這樣做常常呈現出乎意料的荒誕效果:他越是力求精確,意義就越發飄忽不定,這幾乎給他看似狂歡的文本帶來一種女性化的冷淡效果。
當我們的目光被古希臘瓶子上的“濕褶”牽引得神思迷離時,當塔瑪拉手執畫刷讓鄧南遮欲罷不能時,當乘著時光穿梭機的倫敦現代人坐進16世紀的環球劇場、被場子里的臭味和咸濕笑話顛覆了對莎士比亞的認知時,當情人的屁股成為權力與承諾的交易所時,我們被這些新鮮的、原本完全不搭調的意象組合“雷”得眼花繚亂,以至于無暇顧及:小白本人的視角在哪里?如果仍以“秋千”一說類比,則他的目光既非“自下而上”,也非“自上而下”,甚至不是專注的,入迷的,而是聚焦在這些物象之外的某一個(也許是純粹語言學意義的)點上。這一點也超出了讀者的視野,因而,有時候,我們讀小白,是會有一絲慍怒的。
這種慍怒很難表達,很容易被簡化成針對這些作品的敏感題材或者作者的曖昧立場。可以想見,對于本書的討論,最常見的切入點是:第一,作者如何處理涉性題材,如何在意識形態的夾縫間體現其“合法性”,進而,這個問題會演變成“這是不是性研究”乃至“性研究于人類生活有何重大意義”。第二,作者的“研究”材料取自一般人絕少涉獵的領域,那些在希臘羅馬中世紀的碎片中穿梭自如的方式近乎炫技——據我所知,網上的言論,對小白的“崇拜”抑或“反感”,基本上自此而來。
我不知道這樣讀是否正中小白的心意:被他引導著,看他要你看的東西,并被這些東西迷住或激怒。如果我們換一種讀法,揣摩他究竟是如何將這些材料打碎后捏攏在一起的;考究他如何以近乎羅蘭·巴特或者蘇珊·桑塔格的方式,既精準地判斷、定義,又在不動聲色間“曲解”乃至“調戲”原意;拆穿他在嚴肅與玩笑的兩極間如何自定下一整套游戲規則……這樣讀,我不知道會更有趣還是更無趣。這就好比,電影演至高潮,欲仙欲死之際,忽然生出疑心,想舉頭張一張攝影師到底蹲在哪里取景——你自然是望不到的。
游戲感始終充盈在小白的寫作中,盡管他在材料的前期準備階段從不“游戲”,其認真態度幾乎到了不惜工本的地步,他可以為查清莎士比亞時代劇場地板的材質,去翻閱三本大部頭,而查找的結果只是文章中一個不起眼的形容詞——這舉動卻又近乎作者借以從中自娛的游戲。從這個意義上講,連題材之敏感之禁忌都是服務于他的“游戲規則”的。正因為處理這個題材需要步步小心,沒有現成的規則和先例可以參照,表達的難度遠遠超過那些安全的、沒有冒犯感的東西,所以,高手下筆,才更能享受在鋼絲上跳舞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