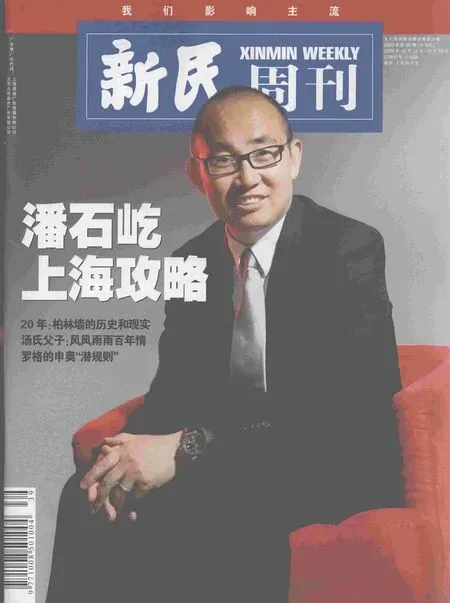帶有體溫的魯迅,略顯蒼老
沈嘉祿
斯人獨憔悴,荷戟獨彷徨的魯迅讓人想到很多,甚至當下。
國慶期間,中國美術館舉辦的一個藝術展為北京增添了絢麗奪目的光彩,這就是作為“向祖國匯報——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系列文藝活動”重要組成部分的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chuàng)作工程作品展。
這個工程由中宣部、文化部、財政部主持,任務下達到各省市自治區(qū),藝術家們躬逢其盛,開始嘩嘩地洗筆鋪紙。上海有9位藝術家被選中,他們是張培成、韓碩、施大畏、徐芒耀、姜建忠、殷雄、陳妍、唐世儲,俞曉夫當然逃不了。既然是回顧性質的,俞曉夫就選擇了魯迅。
還在俞曉夫讀中學時,那位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民族巨人就給了他不少精神滋養(yǎng)。但是很奇怪,成為一個油畫家后,喜歡歷史題材的他,在筆下經常出現的名人有畢加索、托爾斯泰、司馬遷,魯迅倒并沒怎么正式地畫過。俞曉夫說:我一直在思索,生活中的魯迅是什么樣子的。難道他老人家就整天皺著眉頭抽著煙嗎?“文革”時,陳逸飛、湯小銘等都畫過魯迅,都是橫眉冷對的經典模樣,甚至再早,在建國前已經有人畫過他了,木刻形象充滿了戰(zhàn)斗性。但我認為,在今天的語境下,魯迅再也不能符號化和扁平化了,他應該帶有正常人的體溫和彈性。因為一直在思索,就用了一些時間。
這次“回家作業(yè)”讓俞曉夫思索了很久,跑到山陰路,跑到紹興,甚至跑到北京,那幾處留下魯迅足跡的地方,他都沒放過,細細地體味,尋找歷史的印記。底稿打了五六幅,最終選擇了魯迅一生中的三個片斷。一是從日本留學回到故鄉(xiāng),也就是重見閏土或重游百草園的時期。二是在上海。魯迅在上海十年。是生命中最后的時光,也是最輝煌的歲月。三是魯迅與宋慶齡、蕭伯納、蔡元培、林語堂在一起的歷史鏡頭再現。
三聯畫的形式,巨大的尺幅,也給了畫家很大的想象空間。中間一幅的背景就是灰調子的十里洋場,魯迅走在中間,身旁是抱著嬰兒的許廣平,還有他的學生,甚至日本友人。他們走到哪里去,不知道。反正,天空中醞釀著風暴,魯迅的面容因為疲累而顯得蒼老憔悴。“我想,那個時候的魯迅應該是這樣的,他很疲勞,需要休息。但是他一直走著,走在中國歷史的深處。”俞曉夫在記者面前展開他的大幅新作。
在這之前,俞曉夫多次熱身過,他在瓷瓶上畫過魯迅。許廣平煎了藥給先生喝,但先生怕藥的苦味。俞曉夫寫在畫面旁的一段文字有些調侃、有點揣度,但充滿了生活氣息。這個圖案的瓷瓶他畫了不少,都送了朋友。后來他正式畫過魯迅,那是5年前,他為第十屆全國美展創(chuàng)作的,畫面上出現了魯迅的形象,但不是單純?yōu)樗茉斓闹鹘恰T俸髞硭介_筆了,心口生疼地截取了魯迅在生命最后時刻的影像,畫面處理比較灰暗,只有先生捏著一支煙的手是異常清晰的,煙蒂是紅的亮的,魯迅的面容和許廣平的形象都虛化了。這個瞬間讓每個看過畫的人都驚嘆不已,一下子被推到昏暗的歷史通道中。斯人獨憔悴,荷戟獨彷徨的魯迅讓人想到很多,甚至當下。
而這一次,俞曉夫更加慎重地選擇了三個瞬間,尤其是十里洋場的形象,希望觀眾能看到身后的東西,匆匆而過的身影,在風雨如晦的日子里,是那樣的蒼茫啊。寫實主義風格與精準的技法,在這時體現了一種感動人的力量與還原歷史真實的優(yōu)先權。
他曾經想選擇一個魯迅與弟弟一起坐黃包車去看病的片段,甚至,還有一幅是畫家本人與魯迅一起在酒館里喝酒暢談的場景。這些構思對國家工程來說也許不合適,但俞曉夫將來肯定會試一試的。“這次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chuàng)作工程作品,我是花了極大的精力來創(chuàng)作的,為藝術,更為歷史。現在的年輕人,在市場化和時尚的沖擊下,在西方語境的影響下,奉行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對歷史的興趣越來越淡薄,對我們民族的偉大人物也是如此,這是很悲哀的,也是讓人擔憂的。那么用一種他們愿意接受也容易接受的圖像來解說,也許能吸引年輕一代的注意和思考。比如魯迅,中學課里有,但是簡單的說教、機械的分析可能會引起他們的反感和排斥,所以我希望魯迅能成為他們生活中的具體人物,一個看上去可親可愛,也會說說笑話、調侃一下別人,坦然享受一下物質生活的爺爺,那么,這位爺爺內心的煩惱和憤懣,他們就愿意傾聽。”他說。
俞曉夫是認真的,所以他不喜歡夸張炫耀的達利,但也不反對當代藝術的張狂與沖動,“只要是認真地表達真誠的思想結晶和過程,我都尊重他。”他說。
文學評論家吳亮說過:“俞曉夫的油畫總是帶有回顧的性質,一開始他的回顧是人文的,他追溯令他感興趣的近代歷史片段,在想象中與那些大師共處一個夢中空間。當他的叩問式訪問漸漸成為他個人的歷史之后,作品中的文學意味就減弱了。”
文學性減弱了,不是壞事情,作品的思想內涵增強了,這才是關鍵。比如眼前的這幅三聯畫,很強大的三個瞬間,迷茫、蒼老、憔悴,卻真實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