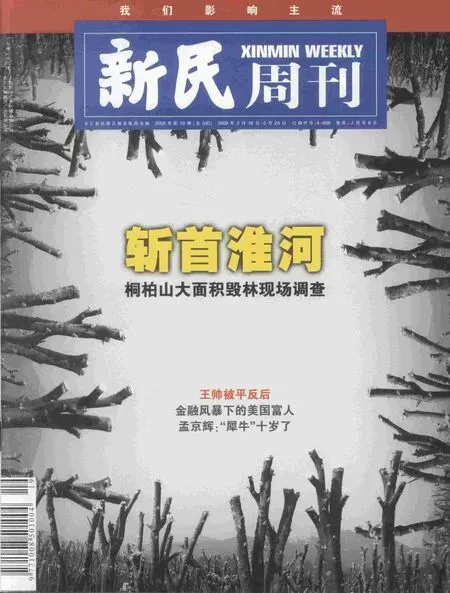警惕“后門”口的暴力
汪 偉

編程高手常常有意在自己寫的軟件中留一個“后門”,通過這個“后門”,他就能進入軟件用戶的計算機,控制他們在計算機上進行的一切活動。行政和法律系統中的“后門”為暴力開了綠燈。
最近國內最火的一本書本來只是“內部發行”——不過可不是它的內容有多么敏感和火爆,這只是北京城管使用的一本內部培訓材料。不知道出于什么考慮,三年前有人委托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公開出版了這本罕見的著作,據我所見,《城管執法操作實務》的封面設計十分鄙陋, 上面還印著城管執法的標志LOGO,更增加了這種鄙陋感,至于書中的內容,稱得上相當暴力血腥。
血腥的教材內容和現實相映照。最近一個關于城管的壞消息是深圳一名城管在他長期巡邏的地點,被一名小販刺傷。萬幸的是傷不致死。經過這件事,深圳的城管部門立刻引進了新的防刺背心。這自然不是深圳的發明。在深圳之前,已經有多個地方的城管投入巨資,購買了包括鋼鐵頭盔、防刺背心、防割手套和閃光背心在內的各種裝備。
中國不少地方城管隊伍的思路,正堅定而決絕地朝著一個危險的方向前進。各地城管傷害攤販、拆遷戶和普通市民的消息,不絕于報紙與網絡,深圳這樣的報復傷害事件也不是第一次發生。對此,一些地方的城管,應對之策不是自我檢討,而是加強武裝,公開倡言暴力。
以流動人口為主的低收入階層的生存需求與一條整齊劃一的街道發生沖突的時候,一些城市的管理者如何選擇?他們熱愛秩序和干凈的城市,一旦理想和現實發生沖突,就本能地撥出一筆筆稅款,試圖將城管武裝起來,以保證他們的戰斗力,甚至不惜以社會對抗和群體事件為代價。
“后門”
對熟悉中國行政體制的人來說,城管這個部門的存在是古怪的,它的設立沒有經過全國人大的立法程序,所以沒有明確的法律地位,也沒有合法的編制和經費預算;它所負載的每一種行政權限,都已經授予衛生、環保、工商、園林、規劃、交管等部門。當初為了解決這些部門的扯皮行為,國務院要求地方政府集中行政處罰權,由此組織的城管部門本來是有中國特色的臨時辦事機構,但現在已經變成常設機構,不僅按人口總數的一定比例配備編制,經費納入財政預算,而且一直在游說全國人大,謀求自己的法律地位。
在法律之外運行的、以暴力為特征的組織,不管其目的是追求利益還是追逐權力,在通行的法律用語中被稱作有組織犯罪,也即通常所謂的黑社會。城管的執法行為在法律之外運行,暴力傾向越來越明顯,如果全國人大堅持不授予這個機構行政執法的權限,人們產生種種聯想也是很自然的。
在軟件行業,這種情況通常被稱作“后門”。編程高手常常有意在自己寫的軟件中留一個 “后門”,通過這個“后門”,他就能非法進入軟件用戶的計算機,控制他們在計算機上進行的一切活動。城管幾乎成了中國法律和行政系統中的“后門”,和軟件業不同的是,這個“后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街道的眾目睽睽之下運行著,除此之外,一次次的暴力活動還經常占據報紙和網絡的版面——因此,幾乎沒有哪個政府機構的口碑像城管這樣糟糕。
但在城管濫用暴力這個問題上,至今我們看到的多是態度曖昧,令人懷疑是一種心照不宣的沉默。北京警察學院教授高鋒作為《城管執法操作實務》的關鍵的撰稿人之一,寫下了“臉上不見血、身上不見傷、周圍不見人”這樣迅雷不及掩耳的排比句,足以和東莞城管局長要求建立特警水準的城管應急分隊相媲美。但顯然沒有人會為此事負責。高鋒教授供職的北京警察學院是一家專門培養警察的專業院校,出版社所屬的國家行政學院,主要目標是培養中高級公務員,但它們都不用對這本書中的內容負責,作為當事人北京城管局,也只是聲明說“部分隊員對當前部分媒體及網絡對該書斷章取義,針對個別詞句和提法進行炒作的做法表示遺憾”,除此,他們甚至拒絕發表更多的評論。
對如此深廣的民怨視而不見,堅持要留下這個治理系統的“后門”,或許只有一種解釋能夠行得通,那就是盡管城管的存在有諸多“副作用”,但是有利于社會治理。
但從長遠來看,這種意味深長的制度安排很有可能是得不償失的。撥款驅動此類“曖昧”的組織維持街面整潔,效率也許相當可觀,但默許暴力的思路最終會導致暴力泛濫,甚至政府的合法性也可能因此而動搖,對高高在上的中央政府——盡管是它要求地方政府集中行政執法權限的——來說,這種危機就會轉化成治理的危機。一旦城市街道成為暴力相對的戰場,社會治理其實已經失控。
暴力泛濫
濫用和依賴暴力已經成為一種觸目的現象,不獨城市管理領域如此。2009年以來,已有15名羈押在看守所內的在押人員“非正常死亡”,其中有人經確認是被同監打死的。由于警力不足,看守所依賴犯人來管理犯人,給“牢頭獄霸”提供了土壤,造成看守所內暴力泛濫。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因此聯合印發了《全國看守所監管執法專項檢查活動方案》,要求從4月20日起,開展一項5個月的專項行動,以打擊“牢頭獄霸”。最高檢察院一位負責人說,在這些看守所內發生的非正常死亡事故中,公安機關監管不力,而檢察機關也沒有盡到法律要求的監管責任。
如此嚴重的“非正常死亡”,并沒有導致對看守所體制的更多的質疑;主管部門的行動是富有中國特色的,中國人非常熟悉這種為了改善特定目標而發起的“運動”,它們有益于改善在看守所內泛濫的暴力行為,但由于缺乏長效的機制,類似的排查活動很難被看作是治本之策。奇怪的是,沒有多少人質疑排查運動一旦結束,看守所內的情形會怎么樣。
當然,最高檢察院和公安部也沒有公布2009年之前發生在看守所內的“非正常死亡”案例,因此羈押場所的暴力活動到底有多嚴重,實際上并不為人所知。
鑒于大量在押人員是犯罪嫌疑人,上海律師斯偉江認為,如果《律師法》第33條規定能夠得到落實,律師可以自由會見當事人,就可以大大降低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內受到不法侵害的幾率。
《律師法》第33條規定,律師憑“三證”(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
在中國的法律體系中,“疑似后門”比比皆是,關于律師會見權的規定是一個著名的例子。
《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應當經偵查機關批準”,“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這與《律師法》第33條規定沖突。
律師不能自由地會見當事人并且不受監聽,一直是中國法律界的老大難問題,由于《律師法》是新法和下位法,《刑事訴訟法》是舊法和上位法,到底是“下位法服從上位法”還是“舊法服從新法”,律師和警察存在嚴重爭執。
“涉及國家機密”常常被用作阻止律師會見當事人的托詞。實際上,有些為了阻止律師會見當事人的做法,完全蠻橫到無視法律的規定。許多地方的警方至今仍然要求律師在“三證”之外,必須出具辦案機關簽發的會見許可。也就是說,律師能否會見當事人,取決于警察或者檢察官的意愿。
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權接受律師的專業法律服務,這也是防止公安和檢察機關濫用權力的制度安排,但這項制度安排至今不能落實,導致看守所內的暴力得不到遏制——和城管一樣,暴力泛濫的根源是權力的濫用。現在的當務之急是盯住行政和法律體系中那些“后門”,不讓它們繼續為暴力開綠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