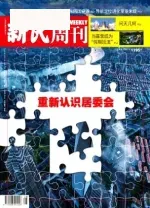司法改革何去何從
王 琳
有媒體近日統(tǒng)計(jì)發(fā)現(xiàn),全國(guó)30名現(xiàn)任高級(jí)法院院長(zhǎng)中,14人以前主要在黨政系統(tǒng)任職,不少院長(zhǎng)之前從未系統(tǒng)學(xué)過法律,從未在司法機(jī)關(guān)工作過。盡管這項(xiàng)統(tǒng)計(jì)還不包括中國(guó)其他級(jí)別的法院院長(zhǎng),但僅高院院長(zhǎng)就有一半黨政系統(tǒng)出身的現(xiàn)實(shí)仍在公眾中引起廣泛關(guān)注。有網(wǎng)絡(luò)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網(wǎng)民贊成司法型院長(zhǎng)與黨政型院長(zhǎng)的比例懸殊到接近12∶1。這樣的輿情讓人并不意外。
近十余年來,基于司法獨(dú)立理念的廣為傳播,無論是法律界還是社會(huì)公眾,對(duì)于法官的專業(yè)化、職業(yè)化和精英化都有了更多的認(rèn)同。“司法官三化”的改革指向在統(tǒng)一司法考試的推行之后,也有了長(zhǎng)足的進(jìn)展。應(yīng)當(dāng)承認(rèn),法官的專業(yè)素質(zhì)正在穩(wěn)定提高之中,這也是司法的必由之路。
但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zhǎng)黃松有等一批學(xué)術(shù)型法官的落馬,讓“法官黨政化”的回潮又提供了一個(gè)噴涌的出口。在加強(qiáng)法官職業(yè)道德的幌子之下,不少地方黨政型法院院長(zhǎng)的比例又有上升的趨勢(shì)。
應(yīng)當(dāng)承認(rèn),司法型法官擁有較高的專業(yè)素養(yǎng),并不代表他就擁有了良好的職業(yè)道德。法官的專業(yè)化和法官的職業(yè)化雖有交叉但并不重合。專業(yè)化強(qiáng)調(diào)審判的專業(yè)素養(yǎng),職業(yè)化強(qiáng)調(diào)獨(dú)立的職業(yè)特質(zhì),這其中,就包括了法官的職業(yè)道德。可以說,法官的專業(yè)化是法官的專業(yè)基礎(chǔ),法官的品行良好是法官的道德基礎(chǔ),二者不可偏廢。專業(yè)素養(yǎng)和道德素養(yǎng)并不是一組矛盾的概念,而是可以有機(jī)共存的。如果過去在推動(dòng)法官專業(yè)化的過程中,忽略了對(duì)法官良好道德素養(yǎng)的要求,那么,在專業(yè)化的基礎(chǔ)上加大法官的職業(yè)道德建設(shè),努力實(shí)現(xiàn)兩者的融合,就應(yīng)成為司法改革的方向。
奇怪的是,在近年來的司法改革方向之爭(zhēng)中,卻出現(xiàn)了一些否定司法專業(yè)化、職業(yè)化的聲音。他們把專業(yè)化與職業(yè)化對(duì)立起來,把專業(yè)素養(yǎng)與道德素質(zhì)對(duì)立起來,因此,被認(rèn)為擁有更多道德素質(zhì)的黨政型院長(zhǎng)重獲青睞。但問題恰恰是,司法型院長(zhǎng)并不一定就擁有良好的道德素質(zhì),黨政型院長(zhǎng)也不一定就品行良好,且能潔身自愛于腐敗之外。沒有任何數(shù)據(jù)和實(shí)例可以支撐后面這一論斷。相反,黨政型院長(zhǎng)鬧出的司法丑聞和司法笑話也比比皆是。
從中國(guó)的司法生態(tài)看黨政型院長(zhǎng)的存在,實(shí)不在“道德素質(zhì)好”,而在于司法機(jī)關(guān)本身又有了加速行政化的傾向。法院院長(zhǎng)的日常工作并不是審判等法律專業(yè)事務(wù),而是諸如抓政治、帶隊(duì)伍、促發(fā)展、保大局、協(xié)調(diào)關(guān)系、加強(qiáng)溝通等等黨政事務(wù)。本來也應(yīng)該是“法官”的法院院長(zhǎng)事實(shí)上成為“大官”。如果我們有興趣翻翻一位法院院長(zhǎng)的工作日志,也許就明白了黨政型院長(zhǎng)之所以存在且日益受重視的現(xiàn)實(shí)理由。
在法治國(guó)家,法院院長(zhǎng)的名稱實(shí)為“首席大法官”,亦即在所有平起平坐的法官之中擔(dān)任“日常召集人”的那位法官。無論是召集會(huì)議,還是主持審判,“首席大法官”的權(quán)力都是限于程序性的,而非實(shí)質(zhì)性的。這樣的理想圖景與中國(guó)現(xiàn)實(shí)的司法生態(tài)相隔甚遠(yuǎn)。也以高級(jí)法院院長(zhǎng)為例,這是一位副省級(jí)官員。雖然此院長(zhǎng)名義上也是該院的“首席大法官”,但實(shí)則是一名不折不扣的黨政領(lǐng)導(dǎo)。法院院長(zhǎng)在現(xiàn)實(shí)中就是一個(gè)基本不主審案件,而日常做著上傳下達(dá),溝通協(xié)調(diào),政治宣傳,組織生活,考察調(diào)研,乃至本院的基礎(chǔ)建設(shè),法官的工資福利,以及扶貧、計(jì)生、各種創(chuàng)建、各類評(píng)比等等等等非司法事務(wù)的官員。要說起“專業(yè)對(duì)口”來,黨政型院長(zhǎng)倒真的要比司法型院長(zhǎng)更為合適。
看來,院長(zhǎng)的“專業(yè)化”和“職業(yè)化”與法官的“專業(yè)化”和“職業(yè)化”完全是兩回事。在《法官法》中,法院的院長(zhǎng)、副院長(zhǎng)初任法官資格,并未被要求通過司法考試,而只是規(guī)定應(yīng)當(dāng)從法官或者其他具備法官條件的人員中擇優(yōu)提出人選。司法職業(yè)之外的黨政領(lǐng)導(dǎo)或許難以勝任從事審判的法官之職,卻可以勝任主要從事管理工作的法院院長(zhǎng)一職。這道人為的法律“口子”,看來還是立法者在對(duì)中國(guó)司法生態(tài)有著深入了解,并試圖因應(yīng)現(xiàn)實(shí)需要的產(chǎn)物。
司法改革之所以被定位在“改革”兩字,是因?yàn)橹袊?guó)已有一個(gè)責(zé)任、權(quán)力與資源配置并不十分融洽的司法體制。改革的對(duì)象不是某一個(gè)具體的制度,而是整個(gè)司法系統(tǒng)——自十六大報(bào)告起,在黨的文件里,“司法改革”也被統(tǒng)一替換為“司法體制改革”。司法領(lǐng)域中的改革已經(jīng)到了非深入體制而不能推進(jìn)的時(shí)候。就像這場(chǎng)“××型院長(zhǎng)”之爭(zhēng)——黨政型院長(zhǎng)只是表象,法院體制的行政化才是本質(zhì)。一味爭(zhēng)論是司法型院長(zhǎng)好,還是黨政型院長(zhǎng)好實(shí)則并無意義,也解決不了問題。唯有推進(jìn)法院體制改革,這一爭(zhēng)議自然消停。想想看,將來的某一天,法院院長(zhǎng)不是“大官”了,也沒有副省正廳的行政職級(jí)而只有法官或首席法官的尊榮,還會(huì)有那么多黨政官員對(duì)“法院院長(zhǎng)”趨之若鶩嗎?想想看,將來的某一天,法院院長(zhǎng)的權(quán)力僅限于“召集”、院長(zhǎng)的主要職能就是審判,那些沒有法律學(xué)科背景和司法實(shí)踐基礎(chǔ)的地方黨政官員還會(huì)對(duì)這樣的“法院院長(zhǎng)”職位感興趣嗎?(作者系海南大學(xué)法學(xué)院副教授,知名時(shí)事評(píng)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