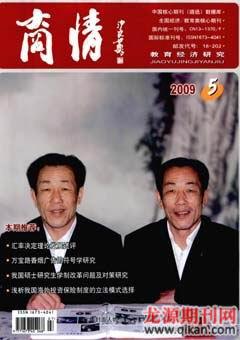試論冷戰后中亞戰略格局的多極平衡態勢
萬 鑫 康勝臣
【摘 要】以戴維?辛格、肯尼思?華爾茲等為代表的“層次分析”視角是國際關系研究中一種常用的分析方法。冷戰后中亞地區戰略格局的走向恰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訴諸于理論的典型案例。冷戰后中亞地區戰略格局雖日趨錯綜復雜化,但國際體系特征、國家間相互借重與制衡式的博弈、領導人自身的外交理念均推動其朝多級穩定的態勢演化。而且從現狀觀之,這種形成中的多級穩定態勢在客觀上也有利于地區穩定和亞歐大陸的整合。
【關鍵詞】中亞 格局 層次分析
中亞地區——這一在無數地緣政治家筆下頻頻出現的“風水寶地”,其戰略地位與重要性自然毋庸置疑。蘇東劇變、冷戰終結之后,中亞地區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紛紛改寫自己的歷史,走上獨立自主的發展之路。但就冷戰后至今中亞地區整合的進程來看,有關國家在能源利益、地緣政治等方面的競爭遠未結束,地區局勢也呈日益復雜化之勢。未來的中亞地區格局會趨
于怎樣的態勢?本文欲借助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層次分析”,并輔助以冷戰后中亞地區發展的重要歷史片斷,力求對該問題給予闡明。
一、戴維?辛格與肯尼思?華爾茲的“層次分析”視角
層次分析法是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一種十分常用且重要的方法。首次將層次分析方法作為國際關系學方法論加以討論的是美國政治學家戴維?辛格。辛格承認了將兩類分析層次即“國際體系層次”和“民族國家層次”結合起來的難度,但卻期望經驗主義的國際關系研究在未來變得更加系統化。
結構現實主義流派代表人物肯尼思?華爾茲在其早期著作——1959年出版的《人,國家和戰爭》中又明確指出了個人因素對引發戰爭的影響,可謂對辛格以往兩個分析層次的再一有力補充。這在1960年辛格對華爾茲新書的評價中就可見一斑,其評價道:“對于華爾茲來說,所謂的分析層次有三類,即:個人,國家與國家體系”。由此可見,盡管戴維?辛格與肯尼思?華爾茲的層次分析方法還存在著某些缺陷,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影響國際沖突的其他因素如國際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但它畢竟為我們理解全球政治提供了一個相對簡明完善的分析框架。而冷戰后中亞地區錯綜復雜且尚不明朗的格局態勢也恰恰成為了我們檢驗層次分析方法的一個絕佳個案。
二、以“層次分析”為分析工具看中亞戰略格局的現狀與走向
1.體系層次
中亞戰略格局相對平衡的多級態勢是世界戰略格局“一超多強”態勢的具體表現,也是競爭中求合作、相互借重與制衡的時代特征與國家間關系的具體反映。當前中、美、俄和歐盟、日本等大國在中亞進行的博弈不同于19世紀大國在中亞的競爭。一方面,19世紀,英國和俄羅斯在中亞的大國博弈是在中亞沒有形成自己民族國家的情況下進行的,中亞人民在大國競爭中是被動的,而現在中亞在大國的競爭與合作中采用靈活外交政策發揮著自己的作用。另一方面,19世紀的大國競爭是排他性的,在中亞形成了壟斷性力量,而現在是各大國在中亞共存的多極體系,這不僅是中亞希望構建多極體系,而且也是各大國所希望的。
2.國家層次
構成中亞戰略格局現存狀態和未來變化的主要力量“單元”處于此消彼長、相互借重制衡的競爭與合作態勢。
(1)美國:中亞地區“奮起直追”的“后來者”
美國在中亞地區決不甘心永遠扮演一個“后來者”的形象。冷戰終結、蘇聯解體前后,美國就已憑借自身強大實力趁機向中亞地區滲透。這種直接或間接的“攻勢”在“9?11”事件以后達到了空前的規模,美國妄圖將中亞和中東的戰略資源區連成一片,以更好地為其全球“大棋局”服務。然而事與愿違,2003年11月起在歐亞大陸興起的“顏色革命”浪潮似乎抵消著“9?11”后美國在中亞所取得的優勢。2005年7月,上海合作組織阿斯塔納首腦會議就發表聲明,強烈要求美國制定從中亞撤出軍事基地的具體時間表,烏、吉等與美保持傳統合作關系的中亞國家也紛紛通過提高要價、明確要求撤出等方式對美國基地施加壓力。美國這一“后來者”在中亞地區“奮起直追”所取得優勢可謂“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2)俄羅斯:中亞地區“韜光養晦”的“看守者”
俄羅斯盡管承繼了前蘇聯強大的核武庫和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政治地位,但經濟領域的捉襟見肘從根本上制約了其在中亞地區影響的發揮。但畢竟俄羅斯擁有與中亞地區天然毗鄰的地緣優勢,“地理環境是俄羅斯中亞地緣政治戰略制定的客觀物質基礎”。隨著近年來綜合國力的日趨恢復,俄羅斯——這一在中亞地區“韜光養晦”的“看守者”正頻頻以能源合作為切入點、以上海合作組織為戰略平臺積極“收復失地”,其地區影響力正逐步回升的態勢。“顏色革命”一定程度上更使中亞這顆“砝碼”在俄美之間的天平中重新向俄傾斜,然而中亞格局短期內不會發生有利于其的本質性逆轉。
(3)中國:中亞地區多級穩定態勢的有利“推動者”
中國早在80年代后期就開始認識到國家利益與周邊穩定的密切關系,進而提出了睦鄰、富鄰和安鄰的周邊外交政策。中亞無疑是這一大周邊戰略體系的重要構成環節。具體表現在:中亞可以成為中國相對穩定的能源來源,是中國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外交平臺。 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之前,中國始終沒有急于出臺一項全面、長期的中亞戰略,究其原因,“不是中國對中亞在地緣政治和能源方面的戰略意義視而不見,而是由于當時中亞地區的形勢尚未明朗。”“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尤其是9?11恐怖主義襲擊爆發后,中國以該組織為戰略平臺加強與各成員國的非傳統安全合作,并對中亞的獨立、穩定、安全和發展尤為關注,中亞各國希望與中國進行全方位、多領域、高成效的合作。事實證明,中國一貫是中亞多級穩定態勢的有利“推動者”。
(4)日本、歐盟、印度:中亞地區“各具特色”的“競爭者”
總體觀之,以上三方在中亞的地位和影響雖然遠不能與美、俄、中三大國相提并論,但其對中亞的政策卻可謂具有鮮明的特色:日本在中亞的利益所系主要集中于經濟和能源,而且已經出臺了整體的中亞戰略;歐盟在中亞尚未形成像日本那樣明確的戰略,就眼下來看主要是安全及能源方面的考慮居多;印度雖然是踏入中亞地區的一個“遲到者”,但其通過與中亞國家建立雙邊合作關系、加入“上海合作組織”等方式迅速提升了自身地位。可以說其轉變也是出于多方面的縝密考慮,如:在中亞取得戰略立足點以形成對巴基斯坦的地緣優勢、對逃亡中亞并危及印度安全的穆斯林宗教極端勢力進行打擊和遏制、在中亞豐富能源天然儲備中“分一杯羹”。
3.決策者層次
毋庸置疑,冷戰后意識形態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盡管沒有完全消除,但卻已基本退出了主流角色舞臺,在中亞地區利益攸關的各方領導人或是采取了靈活務實的對外施政方針。普京執政下的俄羅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既有不顧西方“阻撓”、對境內車臣恐怖主義勢力進行無條件“清剿”的強硬風范,亦有面對咄咄逼人的北約東擴時通過參與“和平伙伴關系計劃”化被動為主動的靈活手腕。總體上看,其基本放棄直接意識形態對抗、以謀求經濟利益至上的“韜光養晦”式的外交方針是有利于中亞地緣政治與地區格局朝多級穩定態勢發展的;而對于中亞一些小國、弱國的領導人來說,如何在大國博弈的“博弈”中求得生存與發展就顯得尤為重要,實質上也最有助于這些國家多方“漁利”、謀求外交利益的最大化。
三、結束語
美國著名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在分析歐亞大陸戰略格局時曾評價道:“歐亞大陸的巴爾干在地緣政治上也是重要的,因為它將控制一個必將出現的旨在更直接地聯結歐亞大陸東西最富裕最勤勞的兩段的運輸網”。以戴維?辛格和肯尼思?華爾茲的層次分析法為分析工具,冷戰后中亞地區戰略格局日趨錯綜復雜化,但國際體系特征、國家相互借重與制衡式的博弈、領導人自身的外交理念均推動其朝多級穩定的態勢演化。而且從現狀觀之,這種形成中的多級穩定態勢在客觀上也有利于地區穩定,更有助于中亞地區發揮如布熱津斯基所言之“聯結”亞歐大陸的作用,加快亞歐大陸的整合與發展。
參考文獻:
[1][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美]肯尼思?沃爾茲著,信強譯,蘇長和校.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潘志平.中亞的地緣政治文化.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4]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上海合作組織:新安全觀與新機制.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
作者簡介:萬鑫,廣東技術師范學院經濟與貿易學院研究生,助教。 康勝臣,河南省湯陰縣一中歷史教師。
(作者單位:廣東技術師范學院;河南湯陰縣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