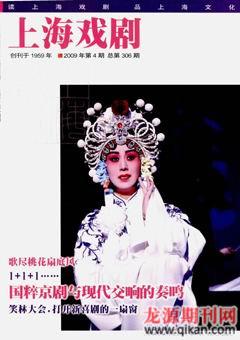古今契合 無戲不趨新
李惠康
Lvruiyings Yue opera performing art
談呂瑞英的越劇流派藝術

戲劇是為了觀眾而存在的。演員創造角色,功在臺上,成在臺下,一切均須以觀眾的理解和認同為前提。唯其如此,演員的表演才能誘導觀眾的鑒賞反應,溝通舞臺上下的情感交流,由此產生社會藝術審美效果。
《九斤姑娘》是越劇發展初期的一出老戲,是用男班的[呤嚇調]演唱的。嚴格地說,由山歌體演變而來的[呤嚇調]尚未完全形成戲曲體,不僅在刻劃人物、表現情感上有較大的局限性,且對現代觀眾已經形成的越劇審美定勢有著很大的距離。上世紀50年代初,呂瑞英在主演此劇時,為解決這些問題,喚起現代觀眾對越劇藝術的審美感情,巧妙地融入了當時觀眾所熟悉的[四工調]和[尺調]的音樂唱腔元素,成功地塑造了一個既不失原有本色、又富有現代情味的九斤姑娘形象,贏得了觀眾的喜愛和贊賞。那時的呂瑞英尚在少女時代,就已經開始致力于藝隨世變、“望今制奇”(劉勰《文心雕龍》)的嘗試并取得成功,使《九斤姑娘》成為呂派藝術的一個發端。
越劇是以抒情為主的藝術,而“情以獨至為真”(陳子龍《佩月堂詩稿序》),即演員只有對角色產生獨到的感悟之情后,才能上升到藝術的至真之情。呂瑞英的杰作《打金枝》歷經半個多世紀的考驗,久演不衰。這出戲是50年代由山西晉劇傳統劇目移植而來的。呂瑞英不僅賦予該劇濃濃的越劇情味,且把君蕊公主的形象提到了“情以獨至為真”的境界,通過傳神寫照的演唱給予觀眾親切的觀感和耐人尋味的情趣,演出了一個皇家女兒特有的靈性之美,顯得格外清純亮麗,化可笑為可愛,直至可愛至極。
藝術流派的境界是“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魏書?祖瑩傳》)。呂瑞英在《西廂記》中對于紅娘的塑造,不僅與《打金枝》中的君蕊公主一樣達到了“情以獨至為真”的藝術境界,還由此產生了諸如“夜坐時停了針繡”等膾炙人口、傳唱廣遠的唱腔,在各劇種的“紅娘戲”中生動而有力地顯示出自出機杼,自成一家的藝術之光。她所照亮的,何止是越劇一個劇種所達到的輝煌?
流派藝術的產生,均有著繼往開來、獨樹一幟的發展過程。呂派藝術之所以與眾不同,不僅是因其別出心裁的唱腔突破了越劇由歷史既定的“哀怨”基調,創立了清新明朗、昂揚向上的風格;且還在于呂瑞英每次創造一個角色,每次都會給人以清新明朗、昂揚向上的時代感。她飾演的九斤姑娘、君蕊公主、紅娘,以及在《三看御妹》中飾演的劉金定、《桃李梅》中飾演的玉梅等抒情喜劇角色,都令現代觀眾感到可親可愛;她在《凄涼遼宮月》中飾演的蕭皇后、在《花中君子》中飾演的陳三兩等抒情悲劇形象,又都能使觀眾從悲情中生發出崇高之感;她在《穆桂英掛帥》中飾演的穆桂英、在《三夫人》中飾演的岳夫人等正劇人物,同樣以剛柔并濟的狀貌韻味給人以強烈的精神感召。這一切,是呂瑞英善于用現代眼光看待劇中的、古代的人事滄桑,站在古今交匯的契合點上感悟角色之情,“因情立體,即體成勢”(《文心雕龍》)地塑造形象的成果。這樣的形象,既互不雷同,又超越時空,生發出鮮活的時代感。
繼往開來,獨樹一幟,古今契合,無戲不趨新,是呂瑞英表演藝術的特質。宋代詩人陸游說:“文章最忌百家衣。”演繹社會人生、堪稱時代之鏡的戲曲當不例外。遺憾的是,長時期以來戲曲舞臺上最為常見的,正是“百家同穿一件衣”的因襲現象,且越來越明顯地顯示出“一代不如一代”的退化走向。如何改因襲摹仿為繼承創新,是當前戲曲謀求新的發展的瓶頸。呂瑞英的舞臺實踐,呂派藝術的創始和發展過程,以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活力和經驗,給當代戲曲藝術的發揚光大、開拓創新,提供了一個鮮活的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