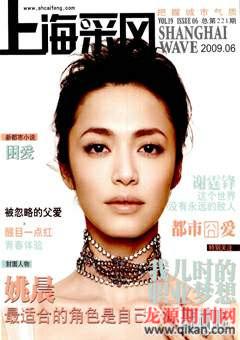爾冬強:以攝影為媒介的文化傳播者
胡凌虹
2009年3月27日,爾冬強在上海青浦朱家角的影廊開幕。在上海這片土地上,帶有“爾冬強”標志的固定場所越來越多,而爾冬強本人的蹤影卻越來越難尋。2000年做完上海題材,他開始進行宏大的“絲綢之路”視覺文獻計劃,足跡遍布中國河西走廊、新疆全境以及歐亞草原、蒙古國、伊朗、土耳其、匈牙利、埃及等地。
如果按通常的攝影師的標準來衡量爾冬強的話,他的攝影之路走得可謂“另類”。上世紀80年代,當國人拼命想擠進體制捧個“鐵飯碗”時,爾冬強卻辭去了報社穩定、高薪的工作,成為國內最早的自由職業攝影師。當大多數同行都忙著參賽、得獎時,爾冬強卻或跑到野外、鄉村、人跡罕見的地方拍風俗人情,或一條街一條街地深入拍攝上海的老街老房。當人們爭相追逐時髦、新潮的時候,爾冬強卻在周圍人詫異的眼光中,忙著收藏“老舊東西”。人們心目中的藝術家似乎應該是心無旁騖專注于藝術。爾冬強卻不,他作為獨立藝術家似乎一直在探索體制外的文化和藝術發展的可能性……他建起了自己的書店(漢源書店)、自己的出版社(中國通出版社)、自己的私人博物館和爾冬強藝術中心。

在采訪前,我是準備了滿滿一頁紙的問題去的,這位攝影師的“著名”加“另類”足以激發提問的熱情。但是爾冬強的回答似乎也很“另類”,往往讓我更生疑竇。“三十年來,你的攝影創作可分為哪幾個階段?”“沒有太大改變,我幾乎一直都是在做一個專題。”(從一開始就找準一個方向,三十年不變,太有遠見了吧?)“攝影家,收藏家、旅行家、董事長、學者,你最喜歡哪個身份?”“我覺得旅行家是當之無愧的,因為大多數人都沒有去過那么多地方,我走過的路比徐霞客還多得多。至于攝影家,現在已很普遍,以后攝影不再是獨立的專業……”(顯然“著名攝影家”的身份他并不特別看重。)“你拍多少張照片會成功一張?”“對我而言,不是數量的問題,想清楚了,拍出來就是有用的。”(似乎狂妄了點吧,事先想好,咔嚓一聲,完美的照片就出來了?成功率百分之一百?)……圍繞著攝影,我發現很難接近真實的爾冬強,仿佛在各自不同的世界里進行著看似連貫的問答。
不甘心,繼續追問。“在拍攝前,你會看很多書和資料,這對你的攝影有怎樣的幫助?”“攝影是一個手段,重要的是被拍的東西打動我了,我通過查資料有了更深的了解,并通過藝術的手法把它最大限度地再現出來。作品的意義,作品最打動人的是內容本身,而不是一定要打上‘爾冬強的烙印。”“你的興趣并不局限于攝影。辦公司,開漢源書屋,成立藝術中心,并舉辦各類文化沙龍,目的是什么?”“就像拍照一樣,也是為了傳播文化和藝術。”
忽然間豁然開朗。我發現一旦把眼前的爾冬強看成是“文化傳播者”而不是僅僅的“攝影家”時,很多問題似乎迎刃而解。也許,更確切地說,他是一個把“中外關系史”作為畢生研究課題的學者,攝影只是他最擅長的手段,而攝影作品是他的研究成果。所以在爾冬強眼里,作品的“好”不只是光影色上的藝術美,更在于作為視覺文獻的價值;所以爾冬強能有獨到的眼光,在他的鏡頭里,異域風情的美讓人震撼,而熟悉不過的建筑也顯出了與眾不同的魅力;所以爾冬強會涉獵多個領域,他收藏的之前不被看好的東西現在變得炙手可熱,他給舊廠房注入文化的元素,點石成金,使之成為了當今的時尚。但是爾冬強也有困難,“最重要的是口袋里的錢”,周游世界需要錢,傳播文化需要錢,體制外的他只能靠自己想辦法掙錢、籌錢,以達到收支平衡。
接下來,采訪話題轉到了他的研究上,爾冬強興奮了,開始滔滔不絕……
記者:你怎么想到做“絲綢之路”?
爾冬強:我原來做的是鴉片戰爭以后、西方文化影響下的中國近代中外關系史。曾用視覺文獻的手段系統梳理了中國近代的通商口岸、租界和租界地,獨立出版了《中國近代通商口岸》、《中國的教堂》、《中國的教會學校》等數十本畫冊。后來我在研究上海史的過程中,發現了拜火教徒在上海租賃土地的契約。我曾在吐魯番周邊的古遺址里看到過拜火教徒的遺存,那是漢唐時期的,這跟近代上海出現的拜火教有什么關系?那我就去追查了,專門到了起源地伊朗……這樣關節打通了,原來我研究的是近代中外關系史,現在的“絲綢之路”是古代的中外關系史。我主要是以人物為線索,比如我查斯坦因,我覺得他不只是強盜那么簡單,于是就去了匈牙利科學院圖書館,找出大量資料,又在資料里面發現了內藤湖南,很重要的漢學大師,曾到我們江南這一帶活動過,那我就專門去日本找內藤湖南的資料……拔出蘿卜帶出泥,越做越深,牽扯出的人物也越來越多。
記者:有個問題,攝影是你的主要手段,但是攝影也有局限性,比如你對很多資料的研究無法用圖像表現出來。
爾冬強:我只能做一方面內容,我找到的古代遺址或文獻資料,該拍攝就拍攝,能拿回來就拿回來。我成立了一個視覺文獻中心,北大、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的學者,都可以到我這邊查視覺文獻資料。我在國內碰到很多敦煌學的專家,因為經濟、年紀等各種原因,無法深入到中外的古代遺址,他們的研究是從書本到書本,而我可以通過拍照、做視覺文獻,跟他們合作,來彌補他們的不足。今年5月到7月在新疆有兩個大的考察我都得到了邀請,考察隊里有考古學家、歷史學家等不同研究領域的人,其中我負責視覺文獻的拍攝工作,大家做的學術準備都不同,在一起工作能互補。
記者:一般人理解的攝影屬于藝術范疇,不少人還喜歡玩觀念攝影,但是你更強調它作為“視覺文獻”的價值。
爾冬強:我覺得我們生活在一個多變的時代,中國在過去30年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能夠把它們記錄下來,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事。當初我在《上海畫報》工作的時候,開了一個“上海印象”的欄目,記錄上海的變化,那時我天天拍,拍那些戴著蛤蟆鏡,穿著喇叭褲的青年等等,為記錄上海也盡了一份力。但是后來我發現新事物不是一天冒一樣,是一天冒十樣,這不是我一個人能記錄得下來的。很可惜,整個中國的攝影界并沒有把這30年里中國的巨變記錄下來,看看我們的檔案館、圖書館,存有多少相關圖片資料?我覺得攝影要肩負起記錄時代的重任,攝影藝術不應該只考慮光影構圖,還應具有文獻價值,這也是目前比較忽視的。
記者:你密切關注的是快要消失的東西,而且比大多數人更早地發現它們的價值,但是除了旁觀的記錄,你是否也進行過呼吁,盡一切可能挽救?
爾冬強:一個人不可能扮演很多角色,我的作用就是把這種美的歷史信息傳播出來,傳播也很重要。我年輕時拍老房子沒有同行者,但是現在看多少人在寫老房子,拍老房子。當年我出《最后一瞥》一書時,送了幾百本出去,給很多作家、媒體的朋友,我想還是對人有影響的,時間會說明一切。
記者:怎么想到在青浦朱家角成立一個影廊?多久開一次展覽?一般會展出什么主題的作品?
爾冬強:因為像這些古鎮需要文化的注入,不然都是賣粽子、賣肉的。世界各地的游客那么遠跑到這里,應該能看到一些江南的地域文化,這也是朱家角為什么引進我的原因。每個月影廊都有展覽,以前我拍過的外國古鎮的保護、民間節慶活動等照片都會在那里展出,讓大家看看人家國外是怎樣保護民間藝術和傳統文化的,這能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