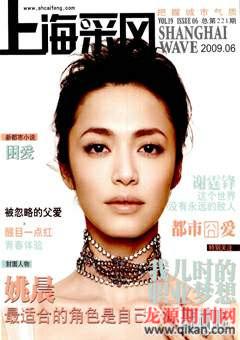趙旭東:上海城市居民的精神問題
胡凌虹
上海老年人的心理問題易被忽視
記者:2007年,你曾透露過一組數據,上海人心理問題發生率高達37%,平均3人就出現心理問題,有那么嚴重嗎?過了1年多,這個情況是否有所改變?
趙旭東:那是我轉述肖院長的,后來我問過她,她說這是小型社區的調查,并不是規范的流行病學調查。關于上海人的心理問題,現在有幾位精神衛生專家正在做大型流行病學調查,希望他們的成果早日出來。不過,有一個數據我們可以借鑒,根據最可靠的流行病學的統計,深圳有21.19%的人口可以被診斷有精神障礙,這是2006年統計出的數據,2007年宣布的。這里說的精神障礙就像彩虹譜,從較輕的心理問題到最重的精神病都包含。上海的情況估計大同小異。深圳是一個新生的移民城市,中青年居多,而上海是一個老牌的移民城市,已有三四代的移民,又進來500萬左右的新移民,人口結構上的不同在城市居民精神問題方面也會顯示出差異來。在深圳,主要是小孩、青少年、中年有麻煩,而在上海還多了老年人的麻煩。現在上海人的平均壽命已經超過80歲,老年人不僅患有慢性的軀體疾病,也有精神障礙,而后者往往容易被忽視。對老年人的麻煩提供照顧也成為了很多中年人的麻煩,形成了多重的問題。
記者:國內,大家對于心理咨詢或治療的認識還存在一定誤區,不少人在心理方面不夠重視或諱病忌醫,在上海等大城市,這方面的意識是否會強一點?
趙旭東:上海、北京、武漢、南京、成都、杭州、深圳等城市開展的心理服務相對好一點。現在,很多人對于心理咨詢和治療還是有顧慮的,但是現有行業內的人手已經忙不過來了,比如我的門診新的咨客預約需排半年的隊。這也說明中國人愿意尋求精神衛生方面的服務,但專業的人力是非常不夠的。
記者:在上海,金領、白領的壓力比較大,同時也支付得起相對昂貴的心理咨詢或治療的費用,所以在來訪者中,這類人群的比例是否較大?
趙旭東:來臨床看病的人,主要是有條件接觸到心理咨詢信息的人,多數有一定經濟實力,大部分是城市人,也有農村來的。同時,來做心理咨詢或治療的比較多的是女性,男性也有,但是表達方式不一樣,經常講身體上的不舒服,我胸悶心慌、坐立不安等等,不太會講心理痛苦。他們不少是由內科醫生介紹過來的,剛開始很不解,否認精神方面的問題,疾病觀念很強。一些成功人士的生活方式有問題,大都是不會休息,身體好的時候對身體過分自信。
記者:來你這里咨詢的人比較突出的是哪方面的心理問題?
趙旭東:來我這里看病的人,婚姻方面問題比較突出,比如配偶間缺乏信任,有情人,性生活質量低,交流貧乏等。最難以理解的是,很多很有文化的夫婦,性方面的知識非常貧乏,會犯很低級的錯誤。不少在家里做金絲鳥的貴婦人問題也很多,雖然一身珠光寶氣,但是生活很凄慘,一定程度上處于社會隔離狀態,家里地位低下。幾年前,有位夫人是帶著大墨鏡來咨詢的,坐下摘了墨鏡后,眼睛又紅又腫,他老公是外資企業老板,家里經常有暴力。還有常見的是來咨詢孩子的問題,學習、品行障礙等,其實歸根結底還是因為爸媽有問題。很多妻子生完孩子以后就一門心思做“中國媽媽”了,傳統的縱向的親子關系過強,不太突出橫向的夫妻關系,容易引發夫妻間的矛盾,也容易導致婆媳關系不好,孩子心理出現問題。還有些社會精英太專注于維持職業生涯、生計,把孩子過早交給替代的人,殊不知隔代養育也會帶來很多的不利因素。
記者:上海是一個很開放的城市,也較早受到一些國外觀念的影響,有些觀念又會與我們傳統的道德觀發生沖突,這是否也是造成家庭問題的一個原因?
趙旭東:對,這在涉外婚姻中比較常見,文化、生活習慣等沖突都會引發家庭問題。比如中國太太喜歡溫柔、文明一點,但有些老外比較古怪、變態,甚至還有受虐狂、施虐狂、雙性戀等,中國太太對于這些特殊性行為受不了。當然,中國夫婦間也會有這些問題。我們一般說,基本的人際關系有兩種,一種是互補,另一種是對稱。差異會產生吸引力,但是如果差異性太大,婚后就要花很大精力來調整,涉外婚姻時常是從天堂掉到地獄。還有的是門當戶對,生活比較平穩,但也會出問題,哪一天想要新鮮感,想找找刺激,那就要出問題了。
新移民家庭的孩子比爸媽還辛苦
記者:趙老師,你近年來一直在做“新上海人家庭問題的心理行為特征”的研究,能談談研究結果嗎?
趙旭東:現在我的幾位碩士生、博士生都在做這方面的課題,研究個人適應行為與家庭背景的關系。其中一位學生做的課題是關于05屆5000多名大學新生的心理障礙。我們搞臨床的都知道,大學一年級是心理問題相對高發的時期,而這些問題其實跟家庭氣氛很有關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大家庭跨入了小家庭時代,但是從家庭動力學上看,親子的紐帶更強了,即便出了遠門,也可以通過電話、網絡等密切聯系,這對青少年有特殊影響,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利因素。上世紀末就開始說大學新生笨,有些孩子生活不能自理而休學。這些故事不夸張,反映心理發育沒有跟生理發育同步。從小學、中學到高中,沒受到離開家的訓練,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自己需要的,什么東西是爹媽幫我做的。不少家庭比較沉悶,“不好玩”;判斷事情喜歡“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邏輯,缺乏靈活性;也有家庭缺乏個性分化,自我不夠強大,這都會使得孩子遇到麻煩時不知道要變通,不會站在別人立場上理解他人,人際關系往往會出現問題。也有些學生在老家很受寵,不把別人當回事,到了新環境就找不到北了。很多做大學心理輔導的老師知道,專業不對口也是引起心理問題的重要原因,這跟父母替孩子選專業很有關系。總體上講,城鄉之間也有差別,上海本地孩子適應壓力小一點,從農村里來的同學,面對變化較大的環境,經常傾向于對自己的健康不自信,遇到麻煩事,覺得沒有辦法,有一定逆來順受的思想。然后女同學比男同學總體心理相對更健康一些,也許這是因為女孩沒有承擔父母太大期望,發展更自然一點。
記者:你對上海新移民家庭也特別關注,研究中是否發現什么特別現象?
趙旭東:我的一個今年畢業的博士生調查了浦東5所不同中學的1059個學生及家長,一半以上是移民家庭。我們發現,父母親文化最高、最低的孩子心理問題最嚴重。特別在移民群體中,影響特別明顯,而且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的孩子心理問題比民工的孩子還嚴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們自己比較容易調整自己的心理問題,但是他們的孩子面臨著雙重壓力,一是新環境的壓力,二是父母親對他們不甘人后的要求。所以跟著爸媽來闖上海的孩子,其實比他們父母親來上海灘還辛苦。調查中,我們發現這些子女和父母對家庭的評價是不一致的,子女報告自我幸福感、對家庭的滿意度都低于父母親。
記者:之前你也在我們雜志上參與了“上海知識移民的文化休克”的討論 ,你作為引進人才來到上海,并且已經工作、生活了5年,有什么特別感受嗎?
趙旭東:經過這幾年的經歷,我不是太支持原來流行的對上海人的偏見,對上海市井生活消極、刻板的印象不那么濃厚了。我感到,我所接觸的社會生活里面,大方、寬容,粗獷、幽默還是不缺乏的。但是教育系統里的老師對孩子不寬容,這是我沒有料到的,讓我印象太深刻了,我最大的體會也來自于自己當爹。學校把太多精力放在考試上,老師與孩子較少有溫情的交流,更強調功利方面的成功,及更普遍的商業上、學業上的成功,把人分為上中下等。這里我不談論要怪誰,我談論的是教育中的功利傾向,體制性勢利,加強了人們對做普通人的恐懼,對普通工作崗位的鄙視。
記者:這應該也是不少學生出現心理問題的重要原因吧?
趙旭東:臨床上學生的心理障礙大多數跟這個有關,學業競爭非常赤裸裸,純粹用智力層面來衡量孩子生命的質量,很多孩子不快樂,成功了也高興不起來。我來上海最先學到的罵人的話就是“戇篤”,第二句話就是“拎不清”,以一個人腦袋好不好使來衡量,不是心理衛生的觀點,拿IQ來標定一個人是不全面的,雖然重要,但是太強調這點,會使社會太冷漠,離我們想要的溫馨、和諧越來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