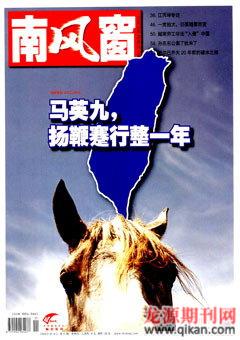權利反腐,箭在弦上
李永忠
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在不少地方和單位,越來越表現為權力的代表性滯后于人民日益增長的權利意識。這集中體現在反腐敗上,就是中國30年的反腐敗,在經歷運動反腐、權力反腐、制度反腐的歷程中,權利反腐已成弦上之箭。
生于197年前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偉大小說家狄更斯,在其《雙城記》的開頭,對所處的英國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時期,作了這樣的描述:“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智慧的時代,也是一個愚蠢的時代;這是一個信仰的時代,也是一個懷疑的時代;這是一個光明的季節,也是一個黑暗的季節;這是一個希望之春,也是一個失望之冬;我們面前有各種機會,我們面前也一無所有;我們可以直登天堂,我們也可以直下地獄……”
近200年后的中國,也正經歷著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陣痛。
“權利時代”的到來
涉及中國歷史,會發現很多有意思的事。民本思想,古已有之。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說法,早見于2000多年前,卻常常停于思想家的筆,止于清官忠臣的折,留于開明帝王的嘴,而很難付之于行……于是,千百年來,從來沒有貴過的老百姓,不得不把自身的全部權利和希望寄托于父母官,頂禮膜拜于好皇帝。
一個絕大多數人沒有宗教信仰的古老民族和古老帝國,居然平和地存在了幾千年,而且凝聚的力量遠大于分裂的力量。是一種什么樣的力量,支撐這么多的人,在這么長的時間,患難與共,同舟共濟?
上世紀80年代初,筆者探秘中國傳統社會2000年來“腐而不朽,垂而不死。死而不僵”的深層次原因,發現兩個有意思的現象。一是隋唐開創的科舉制,在理論上給了所有讀書人通過科考而非錢財、出身、關系、背景以出線(學而優則仕)當官的可能性。此舉不僅開了世界最早的還官帽之權于民的先河,也開了西方文官制度的先河。二是秦漢完備的監察制度,使傳統社會的權力結構達到一個幾近完美的程度。皇帝握有立法權,金口玉言,王言即王法;丞相及地方行政長官掌有執行權;獨立于行政系統的監察系統,即從中央的御史大夫到地方監察官刺史行使監督權。
這種“三權分立”的權力結構,維護了傳統社會權力機制的正常運行,使貪官污吏及不合格的官員能及時有效地清除出去。入口有比較客觀公正的科舉制,出口有相對獨立的監察制,從而確保了多數朝代都能維持二三百年。即使維持不下去,政權被農民起義推翻,新組建的政權也會照樣采用科舉制度和監察制度,以保證其權力機制的正常運行。而監察制度和科舉制度,基本上也與中國傳統社會相伴始終。
這就是制度的力量,也即權力結構的力量!
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意識到這點,不僅在西方三權分立的權力結構上,明確提出了五權分立,加了監察、考試兩院:而且將走向共和的歷程,明確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并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革命綱領。過了差不多100年,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了,被稱作新三民主義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改革開放30年,既是我國經濟實力增長最快的30年,也是人民群眾得到實惠最多的30年,還是廣大干部群眾權利意識覺醒和復蘇最廣泛的30年。第一次解放思想,在經濟上實現了最廣泛的還權于民。農民有了自己的地,困擾多年的吃飯問題,很快得以解決。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在深入基層調研中,引用了老百姓“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活。對這句話稍作分析,即可明白,“端起飯碗吃肉”說明經濟上還權于民,溫飽問題基本解決;“放下筷子罵娘”,影射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群眾權利還未實現。據此,胡耀邦前瞻性地認識到,人民群眾的權利意識已經開始覺醒和復蘇,而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還沒有及時跟上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
1988年3月2日,在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來自臺灣代表團的黃順興,在麥克風前說出的“我反對!”發出了1954年以來全國人大第一次公開出現的不同聲音。人大代表權利意識的公開表現,折射了人民群眾權利意識的復蘇。
身處改革開放的第一線,從大量案例中,既可以最早并直接感受到“權利時代”的到來,也可以深刻并真實地感受到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把“權力之虎”關進“權利之籠”
筆者以為,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體制已大體市場化了,而政治體制(特別是權力來源和權力結構)卻基本停留在計劃經濟時期。由于多年來不少地方和單位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穩妥有余,而積極不足,沒有做到十七大報告所指出的那樣,“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因此,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在不少地方和單位,越來越表現為權力的代表性滯后于人民日益增長的權利意識。
30年的改革開放,比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快更好地把我們帶入權利時代!我們必須以更加積極主動的態度,去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回應權利時代的挑戰!真正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違法要追究!
真切感受到權利時代的到來,有利于在反腐敗問題上形成共識。那就是,中國30年的反腐敗,在經歷運動反腐、權力反腐、制度反腐的歷程中,權利反腐已成弦上之箭。
馬斯洛理論把人的需求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由較低層次到較高層次的五種,而這五種需求可分為兩大層次。前三種屬于低層次需求,后兩種屬于高層次需求。經過30年改革開放,大多數人的低層次需求基本滿足,而權利意識的覺醒和復蘇,則是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在此階段的必然反映。當然,任何一種需求都不會因為更高層次需求的發展而消失,而是相互依賴和重疊。只不過高層次需求發展后,低層次需求雖然存在,但是對行為的影響力則大大降低。
網絡集合公眾意志對公共權力進行監督,是典型的“權利反腐”。這種民間的“權利反腐”與體制內的“權力反腐”將共同構建中國特色反腐敗的完整體系。
反腐的功夫,其實也在查案外!縱觀古今,橫看中外,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反腐敗,是單靠查案成功的!從反腐蝕到反腐敗的30年,我們猛然發現,組織部門對“一把手”的優中選優不可謂不精,宣教部門對“一把手”的教育不可謂不細,各級黨委對“一把手”的監督管理不可謂不嚴,紀檢監察機關對“一把手”的查案力度不可謂之不大……可是黨政“一把手”的嚴重違紀違法案件卻持續上升,乃至占同級領導干部嚴重違紀違法案件的40%左右,一些地方和單位甚至超過一半多!
這是因為,在30年經濟體制改革的強力推動下,我們雖然已進入了權利時代。但是,受“一手硬,一手軟”的影響,政治體制改革還未實質性推進,體制內的權力制衡還未真正形成,群眾的權利意識還未充分表達。正是這些地方和單位權利嚴重小于“公
仆”的權力的狀態,“權力之虎”不僅尚未實際有效關進“權利之籠”,而且還可以隨時隨地發威傷人!最近網絡關注度極高的“羅彩霞事件”,就是“權力之虎”在嚴重傷害權利人的經典案例。
身處權利時代,需要執政黨、全社會又一次廣泛深入地解放思想!農村改革的成功,關鍵就在于經濟上還權于民,從而為30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奠定了一個扎實的厚底!新世紀新階段的解放思想,需要堅持并深化“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生命”的認識,也需要扎實推進“以人為本”的具體做法和有效恢復普通黨員和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從而促進執政黨全社會權利意識的覺醒和復蘇,在經濟上還權于民的同時,逐步推進政治上還權于民。
筆者的一位律師朋友在概括中國現代化的內在維度上,列了三個重要維度,即:“以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為特色的政治現代化,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特色的經濟現代化,以公平、自由、文明為特色的文化現代化”。筆者認為,如果再把“以權力分解、權力制衡的權力結構為特色的制度現代化”,作為一個重要維度列入其間,那就滿足了中國特色現代化所必須的構成要素。
筆者以為,“權利時代”的進程快慢與權力結構的改進完善程度成正比。在廣大群眾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不斷增強,權利意識不斷覺醒和復蘇的新世紀新階段,必須加快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近30年前明確指出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而改革領導制度的核心,就是改革權力結構,就是在權力問題上正本清源。
危機在大智慧者、大軍事家和大政治家面前,通常也是機遇。以筆者之見,用金融手段解決金融危機,不過下策而已;用經濟方式解決經濟問題,不過中策而已;用政治體制改革解決政治危機,才是上策。因為,在世界金融危機來臨時,能看到房子這個物品問題的人,只算個戰術家;能通過房子看清金融危機這件事的人,可算個戰役家;能透過金融危機悟到政治危機,認識到以人為本,并勇于審時度勢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人,才是大戰略家。而馬克思、恩格斯就是透過物而見到人的大戰略家。因此不僅在其《共產黨宣言》中提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而全在《法蘭西內戰》中更明確地強調,“用等級授職制來代替普選制,是根本違背公社精神的”!
歷史證明,權力只有來自權利,權力才會真正代表權利;權力必須回歸權利,權力才能真正屬于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