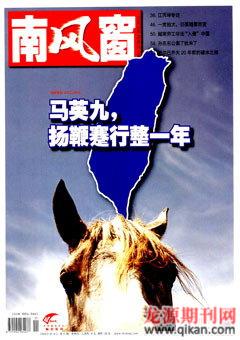中企“出海”浮沉錄
和靜鈞
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礦產需求大幅下挫,中國企業大舉進入澳大利亞資源產業,引發澳大利亞被中國收購的恐慌。澳新聞民意調查公司在3月底4月初做的一份民調顯示,澳大利亞六成以上的人反對“中鋁”擴大在全球礦業巨頭“力拓”中所持的股份。
前不久,中海油總經理傅成玉在博鰲論壇上表示,今后,中海油基本上不再收購其它公司,而是尋找合作伙伴,對其投資。“從來沒有把對外收購作為自己增長的手段,至少在金融危機期間,我們不會去收購其它公司,”此言道出了許多中資企業在“出海”十多年后的心聲。
5年前,麥肯錫咨詢公司中國問題專家森克·貝斯特萊因曾搖頭表示,中資企業在國際化進程中“失敗會多于成功”。的確,當時沒有多少人愿意把中國“走出去”戰略看成是“丁丁歷險記”的翻版,而愿意把躍躍欲試的中資企業看成是一窩蜂擠進豪華名牌連鎖店的暴發戶,這些資本市場上的“新貴”,持著“買個路易威登包”的簡單交易心態,在沒有全盤考慮的情況下就把錢袋子扔給了對方;也有很多論者把這些“還不會走就開始跑”的企業視為肩負著特殊使命的“紅頂商人”,認定這些早期“走出去”者多半折戟沉沙,遭遇“壯士斷腕”厄運。
如今,在經過載沉載浮的洗滌之后,中資企業開始表現出國際并購市場上一名成熟的角逐者的本色。它們從小口小口“吃”起步,到能開展大宗跨國并購,從培養能力和建立團隊著手,到能敏銳判斷一筆交易的內在價值,跨過了只是希望擴張全球網絡或規模的盲目期。這方面有中資銀行開始繞過“有毒資產”向海外尋找合作伙伴的良好開端,有中鋁通過與美鋁的戰略合作成功入股力拓的精彩案例,也有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謀求海外戰略轉型的報道。
近期一份研究表明,2009年第一季度中資企業在TMT(科技、媒體和通信)、能源等領域的并購市場上異常活躍。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胡曉煉表示,2008年中國對外收益達825億美元,增長8%,總體上看是盈利的。盡管成績已經今非昔比,但我們仍有必要回顧一路走來的“艱辛”,這其中有許多教訓,并不因時光荏苒而失去意義,反而在我們加速“跑”時更值得記取。
“繳學費論”下的“走出去”戰略
最早的時候,盡管“走出去”戰略聽起來如“蛟龍出海”般雄壯,但它埋下了“先有拓荒者,后有定居者”這樣的“繳學費”假設。而政府一再默許“繳學費論”是基于這樣的判斷:相對于吸引到的龐大外國直接投資而言,中國前些年來對外投資的比重明顯不夠。
還在1979年國門漸開之際,國務院一份《關于經濟改革的15項措施》就提出了“出國辦企業”的國家政策,但到1991年,12年過去了,“出國辦企業”效果不彰,投資額累計不足14億美元,平均一年1億,分攤到13億人口,人均0.1美元。
1997年,“鼓勵”出國辦企業的字眼正式出現在中央高層文件中,要求“有實力有優勢的國有企業……到非洲、中亞、中東、中歐、南美等地投資辦廠”。這種鼓勵信號,被視為中國爭奪初級資源市場的戰略部署,和配合國家利益的經濟外交政策的具體實施,并沒有被視為以市場為導向的正常資本全球性配置。由于2000年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上所提的“四大新戰略”中明確了“走出去戰略”。研究者們寧愿把2000年視為此戰略元年。
一大批國有企業聞風而動,民營企業亦步亦趨。有些地方,出現中資企業“打擁堂”的現象。如在新加坡,1992年注冊的中資企業僅105家,到2007年就已增至1500家。雖然數量驚人,但投資額卻不驚人,累計投資額不過6億美元。也就是說,一大批中資企業是趕去“湊熱鬧”的。
據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王勤研究員的研究,一些海外投資企業缺乏有效內部約束和風險管理機制,政府部門對這些海外企業疏于管理,人派出去了事,企業經營狀況很少有人過問,以至在一些人眼里,“走出去”戰略成了自己和親屬朋友出國旅行或出國留學定居的“綠色通道”,幾年下來,企業一本壞賬,國家損失嚴重。以這樣的方式“繳學贊”,繳得真讓國人傷心。
當然,真正做企業的也有一些做得不錯,如中遠集剛通過收購新加坡上市公司Sun Corpn,成立中遠投資(新加坡),2004年公司的凈利潤超過6000萬新元。但不可否認,早期“出海”者更多是交了高額“學費”。如在2004年11月,成立不到半年的中國航油(新加坡)股份公司披露,公司累計虧損大約4億美元,加上其它的損失,虧損合計約為40多億元人民幣。

而較近的例子,是2007年中投公司(CIC)投資黑石集團近30億美元,目前賬面資產僅剩1/3。讓中投董事長汪建熙發愁的是,中投每年需要為2000億美元的資本金支付5%的利息,而歐美市場的不景讓股權投資成為極其冒險的選擇,中投當下只能繞過不能投資“人民幣貨幣區”的限制打打港澳臺地區的擦邊球,這使得其每年向財政部特別國債基金專戶歸還100億美元利息的初衷難以實現。
同樣是在2007年,中國第二大壽險公司平安保險以近200億元人民幣參股位列歐洲前15大金融機構的富通集團,“高位殺進”,結果深度套牢,導致平安保險2008年凈利同比減少98%。2008年底,富通2100多名小股東聯名起訴,要求判定富通向巴黎銀行轉讓部分資產為非法。此案一度導致比利時內閣集體請辭。2009年4月底,富通的股東將就3月初比利時政府拿出的新分拆協議表決,作為富通單一最大股東的平安保險已表示將再投反對票。然而,在富通幾近破產的情況下,平安最終“翻盤”的機會可謂微乎其微。
“破爛王”遭遇重整成本
有一段時間,中資企業專去收購“過氣”企業和產業,偏愛收購深陷財務危機中的著名企業,被國際投資專家譽為資本市場上的“垃圾王”。
大多早期進入德國的中資企業,基本上采用收購破產企業的方法,以很低的成本進入德國市場。然而,在這些“破爛王”沾沾自喜于撿了一個大便宜時,卻被隨之而來的重整成本壓得變了形,功敗垂成。
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2002年TCL以820萬歐元的價格收購了德國的施奈德電視機公司,等到接手時才發現,他們所買下的“施奈德”只是個只有幾十名員工,其制造核心力量已經轉移到匈牙利的一個破產后剩下的“殼”而已。為了給這個“殼”背上的債務“贖身”,TCL付出了意想不到的代價,在德國的業務陷入困境,不到半年宣布放棄。TCL通過收購德國施奈德電子和法國湯姆森公司業務而成為世界最大電視機制造商的“虛名”也由此告吹。
如果說中資企業“出海”早期“繳學費”、“收破爛”不可避免的話,那么上汽收購雙龍案則值得認真反思。
2004年,上汽集團溢價收購了瀕于破
產的韓國雙龍汽車公司48.9%的股份。上汽的想法很單純,利用自己的資本優勢換回先進技術。然而,很多專家從一開始就不看好這樁跨國婚姻,原因是上汽不具備收購的技術優勢和歷史經驗。日本收購全球之時,依仗的是其雄厚的資金實力、技術實力和經營理念,日本甚至把美國的精神老巢好萊塢也收購了。世界上成功的收購都是“以大欺小,以強凌弱”,比如寶馬收購MINI。但中國收購方能拿得出手的只有資金實力和進入網內龐大市場的通道。
上汽“吃下”雙龍后,馬上就感受到各種之前沒有料想到的沖擊,先是工會的抗議和罷工潮,繼之“國產化”目標遲遲無法實現,而在不斷輸血之后,2009年,雙龍進入了韓國法院“回生”程序,這意味著這場中韓汽車業婚姻即將正式破裂。第一樁中國汽車跨國并購案,就這樣以慘敗結束。經過此案,吉利、長安、奇瑞等眾多中國汽車公司在借金融危機“抄底”美國底律特的提議面前,變得格外謹慎。這或許是中國“破爛王”形象開始轉型的信號。
缺乏軟實力形象下的工潮
正如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苗圩所說:“走出去最大的差距不是資金,不是市場,而是缺乏一大批具備跨國公司經營管理方面的人才,聯想收購了IBM的PC機,事實證明是不成功的,最后逼得老柳重新出山,楊元慶回到總裁的位置上,這也反映了我們人才缺乏的問題。”
不僅僅是跨國經營人才短缺,很多“走出去”的中資企業,對目的圍的文化差異、價值沖突、意識形態干擾考慮不足,也導致了公司在海外頻遭形象危機。上汽集團承認,他們一開始沒有意識到韓國雙龍公司的工會力量“這么大”。而一家在德同開辦實業的中資公司,開工第一天就引來當地環保部門的“查封令”,理由是工廠的噪音干擾了附近河里的魚兒的安寧。習慣了向河流直接排污、朝居民區排廢氣和噪音的企業,真不習慣把“關愛”延伸到河里的小魚。
這里還牽涉中企“出海”后能否拋棄國內陳舊危機處理思維的問題。中國是礦難發生率最高的國家,但國內的安全事故依然高發不止,假如“走出去”的企業認為“我們中國都這樣,你們也應該這樣”來對待別國的法律和安全生產條例,那無異于一場最失敗的同家形象公關。
2005年,一家在贊比亞的中資銅礦發生礦難,51名贊比亞礦工遇難。事故震驚了贊比亞,死者家屬對中國經營者事前沒有采取有效安全措施,事后只發放少量撫恤金十分不滿,終于在一年后,該銅礦爆發了工潮,礦場發生暴力騷亂。
2006年適逢贊比亞大選,反對黨愛國陣線主席薩塔威脅說,要把中國商人驅逐出境。薩塔雖然未能在當年大選中獲勝,但隨著2011年新一輪大選的臨近,中贊關系又面臨著考驗,不妙的是,自從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銅價大跌,中國小企業老板紛紛丟下贊比亞礦場“逃走”,令中國國家形象進一步受損。
“問題國家”資產安全風險
一些威權主義體制國家,由于政策變動經常出乎意料,對外來投資的沖擊也相當大,這直接影響到投資安全。遺憾的是,對這類國家,別人在退避三舍之時,來自中國的一些企業卻盲目進入,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據《北京青年報》馬寧報道,繼數十次發行面值如天文數字的鈔票之后,2009年2月2日津巴布韋又啟用新貨幣,這次新貨幣看上去不再令人“眼暈”,去掉了舊貨幣后面的12個零,即1津元相當于原來的1萬億津元。津元貶值到什么程度?記者報道說:“1億津元的面鈔丟在地上,都沒有人去撿。”
津元的狂“貶”,使在津巴布韋的近30家大型中資企業蒙受巨大損失。更不靠譜的是,津巴布韋借名“美元化”,要求企業交稅用美元,而給中資企業結算工程款時卻運來一車車無用的津幣。
以建設“21世紀社會主義”為口號的委內瑞拉,在能源價格上漲時,要么就利潤分成與外資企業產生摩擦,要么就執行國有化,派軍隊去接管。而在金融危機面前,石油價格一落千丈,從175美元的高位跌至30多美元時,委內瑞拉又裝出相當“好客”的樣子,邀請外國投資于委內瑞拉能源產業。
在國際石油投資界,“利潤對半分成”曾是委內瑞拉的首創,后來風靡到中東等地。而近幾年,在查韋斯“先進”到直接國有化時,委鄰國厄瓜多爾就突然來一招“99%的利潤分成”,把中國在厄瓜多爾的中石油和中石化兩大集團“打”傻了眼。
2007年10月4日,厄瓜多爾總統宣布,自即日起該國原定與各外國及私人石油企業的超額油價分成比例由50%提高到99%,只給企業留1%。這個所謂的“暴利稅”,完全不顧合同的神圣性,愛怎么著就怎么著。
先誘你投資,然后又祭出“國有化”、“暴利稅”牌的國家還真不少。俄羅斯和一些中亞國家也有這樣的惡例。這些國家的借口高度一致,資源,無論是石油、天然氣還是礦產,都是國有的,國有化或離譜的暴利稅是符合憲法的。
經濟民族主義引發的“反華情緒”
經濟民族主義加上政客的煽火點風,容易轉化為“反華情緒”,中國企業在海外并購時也吃盡了這方面的苦頭。
4年前聯想收購IBM全球個人電腦業務,就是因美國政府的壓力而被迫修改收購合同,失去了許多預期中的收益。而中海油收購美國尤尼科的失敗,則是敗給了赤裸裸的經濟民族主義,因為中海油的競爭對手就是美國的雪佛龍。再有,海爾競購美國最著名消費品牌美泰公司,對手惠而浦也是美斟的公司。美國政客揚言,海爾接管美泰后會關閉在美國的工廠。導致工人失業。事實是,惠而浦購得美泰后,立馬關閉了3家美泰工廠削減了4500個就業崗位,但卻沒人站出來說三道四。
同樣,2004年,中國一家大型礦產公司競購加拿大銅、鋅和鎳的生產商諾蘭達公司,政客們以攻擊中國人權記錄,阻止了這樁交易進行。
近段時間以來,澳大利亞“反華情緒”似乎一浪高過一浪。先是澳大利亞國防部長被揭發接受有中國政府背景的一名女商人的贊助,免費到中國訪問,接著就是反對黨領袖批評陸克文總理“過度親中”,是中國的“巡回大使”,然后《澳大利亞人報》曝出所謂小國情報機構人員侵入陸克文總理電腦的“中國黑客事件”。最新的一件,則是澳大利亞國防部鷹派到美國國防部訪問,向五角大樓兜售“中國威脅論”。據《澳大利亞人報》報道,國防部鷹派的觀點是:中國是新“冷戰”對象,澳大利亞應該圍繞未來與中國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來規劃部隊結構。
這些“反華情緒”其實都是奔著經濟民族主義來的。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礦產需求大幅下挫,中同企業大舉進入澳大利亞資源產業,如華菱鋼鐵集團收購澳大利亞第三大礦業公司FMC等,引發澳大利亞被中國收購的恐慌。澳新聞民意調查公司在3月底4月初做的一份民調顯示,澳大利亞六成以上的人反對“中鋁”擴大在全球礦業巨頭“力拓”中所持的股份。目前中鋁已經持有力拓9%的股份,正謀求擴大到18%。而在稍早前,澳大利亞官方曾以國家安全為由,否決了中國“五礦”公司以15億美元收購澳大利亞一家負債累累的沒落礦產企業。迫于壓力,五礦不得不提交一份修改過的收購方案,澳大利亞政府最后才放行。
有一個例子可以引來旁證外國的擔心是出自多方面的。據美國《時代》周刊報道,越南中高地帶盛產鉛礦,美日等國公司在該地帶開了大型露天礦。已經有段時間了。最近中國公司也準備投資該區域,結果引來越南國內一片反對,甚至越共元老武元甲都站出來反對。該項目后因環保問題沒有獲批,但深層次的原因則是越南對中同在其戰略要地擴張的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