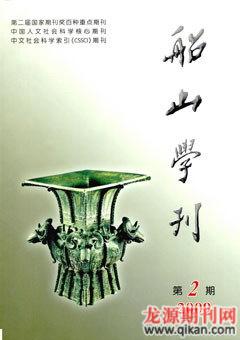論宋代詩學思想對日本《濟北詩話》之影響
黃 威
摘要:本文運用影響比較研究的方法,論述了我國宋代詩學思想對日本第一部詩話——《濟北詩話》所產(chǎn)生的深遠影響。
關鍵詞:宋代詩學思想:虎關師煉;《濟北詩話》
中圖分類號:110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7387(2009)02-0162-03
中國和日本作為一衣帶水的鄰邦,自古文化交流便極為頻繁,日本文化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其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批評也與中國文學關系密切。虎關師煉(1278—1346)為日本臨濟宗高僧,京都人,名師煉,號虎關,是日本五山文學的先驅(qū),著有《元亨釋書》30卷、《聚文韻略》5卷、《濟北集》20卷等,其《濟北詩話》為日本第一部詩話,也是五山時期唯一的一部詩話。《濟北詩話》共20余則,內(nèi)容以評論我國唐宋詩人為主。筆及李白、杜甫、王維、林逋、王安石等,篇末記其笞童學詩等瑣事。《濟北詩話》距中國第一部詩話《六一詩話》晚出270多年,它的寫作背景應該與大量宋人詩話傳入日本有關。檢讀《濟北詩話》。可以發(fā)現(xiàn)虎關常常引用宋人論詩觀點。如“趙宋人評詩。貴樸古平淡”:又如“楊誠齋曰”,直接引用宋代詩話的情況也不少。如“《玉屑集》:句豪畔理者”出自《詩人玉屑》卷3;又如引“《古今詩話》曰”,可知其涉獵頗為廣泛。虎關師煉的文學觀主要受到了我國宋代詩學的影響,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重視詩歌道德教化功能的文學觀
中國自古以來即肯定詩歌的教化作用。主張文學的功利性。在兩千多年的中國詩學史中,儒家的詩歌觀念一直起主導作用。即遵循崇尚孔子的文論。主張“詩言志”,強調(diào)文學的政治教化性。宋代儒學復興,“詩言志”的傳統(tǒng)觀念再一次成為詩學思想中的主流。張戒說:“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后詩,專以詠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詩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馀事。古詩蘇李曹劉陶阮本不期于詠物。而詠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復及。其情真,其味長,其氣勝,視《三百篇》幾于無愧。凡以得詩人之本意也。潘陸以后,專意詠物,雕鐫刻鏤之工日以增。而詩人之本旨掃地盡矣。”在理學的影響下,涵養(yǎng)心性,吟詠性情的詩教觀點漸人宋人心中。宋人從孔子的詩教觀出發(fā),多主張詩要起諷諫作用。同時期的日本鐮倉時代。五山文學興起,漢學在日本進入成熟階段,孔子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宋代理學特別是朱子之學輸入日本,極大地影響了日本儒家文化的發(fā)展。虎關也深受這種思想的影響,《濟北詩話》中言必稱周公、孔子。首則便稱贊周公、孔子為偉大的詩人,“今見三百篇,為萬代詩法。是知仲尼為詩人也。”提倡詩歌應“學道憂世。匡君濟民”。重視詩歌的載道貫道功能。虎關在詩話中指出:“古人作詩,非諷則懷,離此二,不茍出口矣。”他還說:“夫詩者,志之所之也,性情也,雅正也。”主張在詩歌中“辯邪正”,“昔者仲尼以風雅之權衡,刪三千首,裁三百篇也,后人若無雅正之權衡,不可言詩矣。”秉承儒家“詩教”傳統(tǒng),以三百篇為圭臬,以詩教為極則,主風雅教化之旨,強調(diào)詩歌的美刺功能。這些都是虎關與宋代詩學思想相一致的地方。
詩人的品行修養(yǎng)問題一直是詩學批評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宋代詩學批評中極重作家的人品,認為詩品出于人品,理學思想的影響更加劇了這種以人品定詩品的傾向。這從宋人對李杜的評價中就可以看出:“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為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于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系其心胸。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每以李杜并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無所優(yōu)劣也。至本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饑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云:‘李白見永王反,便從臾之。詩人沒頭腦至于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卻高。其救房琯亦正。”因杜甫之忠君愛國和政治品性勝過李白。盡管二人文學成就相近。宋人卻推尊杜甫。宋人把杜甫看作是忠君的典范,認為杜詩極合于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宋代詩學批評在對杜甫及其詩作內(nèi)涵高度肯定的同時,也為他罩上了幾圈神圣的光環(huán)。
虎關也繼承了宋儒的這種以人品定詩品的批評論,詩話中對陶淵明人品的討論就表現(xiàn)了這一點。陶之為人與詩歌。無論中國還是日本都是受到一致肯定的。虎關卻認為陶詩非“盡美”,人非全節(jié)。蓋因“詩格萬端。陶詩只長沖澹而已。豈盡美哉!文辭施于野旅窮寒者易,敷于官閣富盛者難”;潛“詩清淡樸質(zhì),只為長一格也。不可言全才矣。”對于陶之人品,虎關說:“又元亮之行,吾猶有議焉。為彭澤令。才數(shù)十日而去。是為傲吏,豈大賢之舉乎?何也?東晉之末。朝政顛覆,況僻縣乎?其官吏可測矣!元亮寧不先識哉?不受印已,受則令彭澤民見仁風于已絕。聞德教于久亡。豈不偉乎哉!夫一縣清而一郡學焉;一郡學而一國易教焉。何知天下四海不漸于化乎?不思此。而挾其做狹,區(qū)區(qū)較人品之崇卑。競年齒之多寡,俄爾而去,其胸懷可見矣。后世聞道者鮮矣,卻以俄去為元亮之高。不充一莞矣。”虎關認為“守潔于身者易矣,行和于邦者難矣”,潛避難趨易,所以“潛也。可謂介潔沖樸之士。非大賢矣。”最的,虎關指出:“其詩如其人。先輩之稱。于行貴介。于詩貴淡。后學不委,隨語而轉(zhuǎn)以為全才也。故我詳考行事,合于詩云。”舊虎關批評陶之詩“只長沖澹而已”,“只長一格”,“不可言全才”,而對陶避世隱居這一中國人視為高潔的行為,虎關也提出了批評,他認為,衰亂之世則士大夫更應當出仕,力圖有所為而漸挽狂瀾,所以陶只能算“介潔沖樸之士”而“非大賢”。虎關的觀點可以說是對陶淵明的苛責。也與中國儒家傳統(tǒng)的出處進退觀大相徑庭。虎關為人嚴于律己,對己對人要求極嚴。其淵博的學識和近乎至善的人品對當時的日本禪林的影響很大,他提出這種觀點與他這種個性有關。此外,對于日本批評家而言,陶淵明畢竟是一位外國詩人,因民族性格、文化差異的影響,虎關對淵明其人其詩作出這種批評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重才學好議論的批評特色
宋代文化的高度繁榮和崇文的氛圍使得宋代作家大多具有豐贍廣博的學識和堅實的學術功底,也造成了宋代文人自信力的高漲。宋人以“好議論”著稱于史,早已成為不爭的事實。虎關身上也繼承了宋儒的這些特點。加上虎關身上日本人極度自信自負的民族性格因素的影響,《濟北詩話》中展示自己才學、故作新論的議論文字頗多。
《濟北詩話》第五則謂:“古語,后人或誤用,風俗沿襲。而不可改之者多矣”,指出中國文人誤用“蒼生”之原意。第九則謂注者注杜詩“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一聯(lián)“非也”;第十則“杜詩《題已上人茅齋》者”謂注者“皆非也”;第十一則謂“老杜《別贊上人詩》”,“諸注皆非”,并自負地說:“千家之人。上杜壇者鮮乎。”第十二則更嘲諷
中國注杜家“以七佛為七祖,可笑也”,“儒人不見佛書,間有見。不精,故有斯惑。”宋人對“讀書破萬卷”的杜甫的非凡學力極為崇拜。認為杜詩“無一字無來處”。自己注釋杜詩時也認為:“老杜讀書多。不曾盡見其所讀之書。則不能盡注”,宋人對杜詩的典故來處極力搜尋。對杜詩的注釋可以說已達到了比較高的水準。而虎關作為一個外國人,竟能對宋人杜詩注解的錯誤之處提出辨證。可見虎關之才學和對中國典籍研讀之深入。而他常掛在嘴邊的“皆非”、“可笑也”也可看出虎關的自負和對自己學力的自信。
雖然《濟北詩話》深受中國詩話影響。但虎關對中國人的評論并非亦步亦趨。與宋儒一樣,虎關好議論,喜為傳統(tǒng)觀點做新解,做翻案文章。他經(jīng)常對中國詩話中的某些結論加以辨證,比如:“《玉屑集》句豪畔理者,以石敏若‘冰柱懸廉一千丈與李白‘白發(fā)三千丈之句并按,予謂不然。李詩曰:‘白發(fā)三千丈,緣愁若個長,蓋白發(fā)生愁里,人有愁也。天地不能容之者有矣,若許緣愁,三千丈尤為短焉。翰林措意極其妙也。豈比敏若之無當玉卮乎。”《濟北詩話》論“唐宋代立邊功”條,幾全篇為議論。而對中國人一般較認可的唐玄宗,虎關也說:“唐玄宗世稱賢主,予謂只是豪奢之君也,兼暗于知人矣”。“玄宗之不養(yǎng)才者多矣,昏于知人乎。上文所引的論陶淵明的例子則更明顯。虎關對陶淵明的批評可謂苛責。這種批陶的觀念不僅在中國,就連在日本也是極為少見。不能不說這是虎關為求議論驚人而失卻了公允平正。
盡管虎關的這些議論意見未必全部正確,但他努力在詩話中表達自己的意見、不以中國詩論為金科玉律的做法,還是頗值得我們欣賞的,這恰恰形成了其詩話的特色。而且,虎關的這種作風也對后世的日本詩話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力圖表達自己的觀點,不跟隨在中國詩話之后人云亦云也成為了日本詩話的一大特點。
三、主張適理平淡反對格律雕飾的風格論
平淡是宋詩的主體風格,如虎關所說:“趙宋人評詩貴樸古平淡。賤奇工豪麗。”雖然蘇黃等作家為宋詩對仗的精工、格律的嚴整做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但他們“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傾向卻受到了批評家們的非議。嚴羽便說:“押韻不必有出處。用字不必拘來歷。”虎關的觀點也與宋代批評家們一樣。反對處處講究出處、來歷的做法。認為一氣呵就、渾然天成的才能稱為上品之詩。《濟北詩話》以“適理”和“雅正”為批評基礎,認為詩只要“順時立言”便好,“圣人順時立言。應事垂文。豈樸工云乎?”連樸古平淡也不必去刻意追求,“夫詩之為言也。不必古淡不必奇工,適理而已。大率上世淳質(zhì),言近古樸;中世以降,情偽見焉,言近奇工,達人君子。隨時諷喻。使復性情,豈樸淡奇工之所拘乎?唯理之適而已”嗍,比宋人所追求的平淡又更進了一步,虎關認為上古醇補平淡不雕飾的文學才是真正完美的文學,他說:“然古人犯聲韻復字者,達懶也,非不能矣。”在最后一則詩話中,虎關記述自己教小童學詩時。讓其:“不用聲律。只排五七”,童子的作品卻“其中往往有自得醇全之趣”;教小童學書時,讓其“不用法格,只為臨摸”,“其中往往有醇全之書”。他進而得出結論:“世之學詩書者,傷于工奇。而不至作者之域者。皆是計較之過也。今夫童孩之得,愚聯(lián)無知,而有醇全之氣者。樸質(zhì)之為也,故日:‘學詩者。不知童子之醇意,不可言詩矣;學書者,不知童子之醇書,不可言書矣。”虎關主張文學要質(zhì)樸醇全、渾然天成。反對格律雕飾之作,“凡詩文拘聲韻復字,不得佳句者皆庸流也,“浮矯之言。吾不取矣。”同嚴羽一樣。虎關也強調(diào)詩賦應有漢、唐氣勢,他批評“朱淑真詩。其格律軟陋”,“詩賦以格律高大為上,漢唐諸子皆是也,俗子不知。只以夸大句語為佳,寔可笑也。”總之,虎關所主張的文學風格比起宋人的平淡更進了一步,已經(jīng)近于粗率樸拙了。
通過以上各方面的對比我們可以知道,日本第一部詩話《濟北詩話》可以說受到了中國宋代詩學思想的深刻影響,它誕生在中日文化交流的時代氛圍中。它是日本批評家吸收中國詩話營養(yǎng)而加以移植、模仿、并加入自身特色創(chuàng)造發(fā)展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