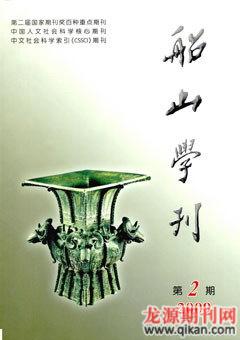傳統與斷裂:“信用”流變的歷史考察
劉高林
摘要:信用在傳統中國不僅是一種美德,更是維系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秩序,與傳統的農業經濟與身份社會達成和諧。但在現代以來,隨著工商業經濟和“陌生人”社會的發展。信用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發生了斷裂,這也是現代信用危機的根本所在。
關鍵詞:信用;傳統;斷裂
中圖分類號:110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09(02)-0200-03
近來。“三鹿”奶粉事件席卷全國,食品類“國家免檢”取消,舉國上下莫不側目。從“蘇丹紅”到“孔雀綠”,從“大頭嬰”到“結石兒”,我們震驚的不僅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食品安全問題如此頻發,而是痛切于整個國家陷入的信用危機,憾然于中國這個禮儀之邦竟淪人今日之道德沉淪的局面。“一個社會每當發現自己處于危機之中,就會本能地轉眼回顧它的起源并從那里找到癥結。”本文將對信用的歷史流變進行梳理。力求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尋找一些線索。
一、傳統
信用是由傳統的“信”字演化而來,它的初始意義是指祭祀時對上天和祖先所說的誠實不欺之語,《左傳·桓公六年》:“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在中國古代,“信的價值評判功能并不限于在商業貿易,而是及于各種社會交往甚至政治關系的‘約。”古代就對‘信的要求很嚴格,“凡大約荊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于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至中國思想史上光輝燦爛的春秋戰國時期,“信”已經發展成為諸子百家紛紛提倡的社會倫理和人生哲學。
道家的老子非常重視道德,他將道德哲學與歷史相聯系,歷史的意義只是相對于社會的道德意義而顯露出來。“信”的初義是說話要講求信用,即“善信”。“信”作為人們之間交往的原則體現了古代素樸的道德,“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并且,“信”應該是統治者的基本品德,“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法家崇尚統治之術,“信”是作為統治倫理基本準則而出現的。“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日權。……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民信共賞則事功成,信其刑則奸無端。”商鞅的“徒木立信”也說明這一點。法家另一位代表人物韓非子認為,“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于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
日后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對于信用非常重視。“信”是其創始人孔子所用的常識性的倫理概念,是他的仁學體系的重要支柱。“子曰:‘能行五于天下,為仁矣。曰:‘恭、寬、信、敏、慧。”《論語》中多次提到“主忠信,行蔦教。”“信”是為人的基本要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但不僅于此,“信”還是立國之本。《論語》中對此有生動描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這是儒家道德政治化的具體表現。其后孟子也將“信”作為人之“五倫”之一。
春秋戰國也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巨大的社會轉型期,信用作為重要的倫理道德為各家各派所重視。它不僅僅是人生哲學還是政治哲學。信用開始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儒學的發展,作為儒學重要支柱的信用開始意識形態化。漢武帝聽從董仲舒的建議,儒學成為官學。董仲舒重構儒學系統,將“信”與“仁、義、禮、智”并列為“五常”。從此,信用觀念取得了作為幾千年封建文化支柱——“三綱五常”——的地位。“‘信因而得以借助制度文化、意識文化之力深入中華民族道德意識深層。”作為儒家文化的一部分,信用成為一種觀念并同樣作為意識形態化的倫理深入人心。“故君臣不信,則國政不安。父子不信,則家道不睦。兄弟不信,則其情不親。朋友不信,則其交易絕。”這可以說是對信用觀念作為一種基本秩序在傳統社會的深刻寫照。
信用以儒家的“仁義”為核心,以一整套儒家行為標準為準則形成傳統倫理規范。也即信用機制借傳統倫理道德得以建立。在封建社會里,倫理道德規范常常具有法律的效力,它深刻的規制著社會中人們的日常生活。實際上,中國傳統社會就是道德文明秩序的社會。信用觀念就同儒家思想一道成為了維護以“家、國、天”三位一體的、以血緣宗法為核心的封建統治秩序的支柱,并以“三綱五常”的明確規則最終形成了一種制度的和諧,人們在這一種和諧所確立的社會關系中,按照封建統治意識去實施自己的行為,從而又形成了穩固的社會秩序。總之,作為維護傳統的身份倫理道德秩序的主要規則,信用經過漫長的歷史積淀而形成的基本觀念,成為維系世道人心的紐帶,并且在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中,傳統觀念與社會達成了一種自然的和諧。
1、經濟。傳統信用觀念生存與發展的經濟基礎是傳統的農業經濟。雖然中國地大物博。區域之間經濟并非整齊劃一,且又經過幾千年的發展,但自新石器時代以來中國即以農業為基本生產方式。精耕制與統治階級重農抑商政策的推行,人民安土重遷,中國經濟形態始終為小農精耕與市場交換的農村經濟。這里的“市場交換”主要在于不同經濟區域之間的差異滿足,強調的是自給自足,滿足農業需求而非發展貿易經濟。國家往往主導地區間物質交換而不是以民間自發為主導。因此,穩定的農業經濟更注重感情資源的調動,中國傳統的信用觀念與西方工具式倫理——自本杰明,富蘭克林總結,并由馬克思·韋伯所發揚為資本主義精神之一的“信用就是金錢”——大不相同。
2、社會。在農業經濟基礎上的中國傳統社會尤重血緣和地緣,但基本特點的鮮明的血緣宗法性。在血緣宗法社會里,以儒家的人倫與名分觀念為秩序中心,也就是通常所述的中國社會由皇帝而下縱向構造的“身份社會”。不同身份的人地位不同,用今天的話說,不同身份的人之間享有不同的權利義務。信用在不同身份的人之間含義是不同的。孟子曾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另一個重點——地緣——多體現于中國傳統社會最廣大的基層農村,也就是費孝通先生所描述的“鄉土社會”,這里除了血緣與地緣相結合仍適用身份之外,還有“熟人社會”的“差序格局”。在縱橫交錯里,信用在不同的象限有不同的含義,及至陌生人則基本無信用可言。
綜上所述,在整個儒家的價值體系中,“信”可算是唯一處理一般社會關系的道德準則,它是普通人解釋社會中交際行為且不只限于經濟行為的共識。傳統的信用并非表象上的簡單詞義所能涵蓋的,它是以維護封建統治的儒家文化為內核,以農業經濟、宗法血緣社會為基礎,規范著傳統社會秩序的一整套倫理規則。它隨著儒家倫理生成中國傳統秩序歷經兩千多年治亂相循而變化不大。意識形態化的文倫理成為維系人們日常行為的社會信用的機制,并且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內蘊和經濟社會底蘊。一方面。它服務于封建統治,表達了適應傳統社會的道德準則和
行為規范,是消極的、特殊的;另一方面,它作為中國傳統人生之道的經驗概括,又隱含著中華民族共同的基本生活原則,這種人們交往的基本挈矩之道又是普遍的、積極的,不能全面否定。以至孫中山在1924年《民主主義》(第六講)中斷言:“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
二、斷裂
中國社會自明清之際,社會已開始發生重大變遷,經濟、政治危機日益深重。傳統倫理思想雖仍占據主流地位,但已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中國開始進入一個“天崩地解”(黃宗羲語)的時代。
而自近代以來。隨著鴉片戰爭后中國的國門被打開,各種外來思想伴隨著“堅船利炮”一起涌人。中國進人了“千年來有之變局”(粱啟超語)的重大轉折。從學習洋槍洋炮到引進“制度”。中國開始了百余年來直到現在猶朱止歇的“洋務運動”。在這百多年來的大演進中。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新中國建立推翻“三座大山”。百余年來的劇烈變遷,使歷史經驗與現代社會不期然的產生了隔膜。
1、經濟。從明清以來,工商業的發展已經對農業經濟出生了巨大的沖擊,而自鴉片戰爭以來,先有“洋務運動”后有“工業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已經有了全面突破:建國后的“三大改造”直到如今大力發展的“市場經濟”,農業經濟作為一個經濟形態已被取代,商品交換和市場規律已逐漸成為社會主流。
2、社會。經濟形態轉換,社會結構更是變革劇烈。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社會顯然進入了一個大轉型時代。新中國建立以來,社會主義的大力改造,嚴格的血緣宗法社會與森嚴的等級制度已被摧毀,即使有人認為當今社會還存在著一些擬制的等級。但如封建似的等級制度確已消失。而隨著商品的發展,社會的劇烈變遷,人的流動性大大增強,“熟人社會”已經逐漸被“陌生人社會”所代替,“鄉土社會”中重土安遷的觀念逐漸改變,“差序格局”也逐漸因社會的變遷而消失。
馬克思曾以印度為例對東方社會的變遷有過生動的描述:“以純粹的人的感情上來說,親眼看到這無數勤勞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會組織崩潰,瓦解、被投入苦海,親眼看到它們的成員既喪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悲傷的。”
傳統的倫理文化更因激烈的批判和社會改造而消失殆盡。自“五四”以來,“反傳統”就逐漸成為文化的大旗。雖然對“五四”的爭論大半世紀來沒有停止過,或認為她開“全盤西化”之先河太過。或認為“五四”一代是以“反傳統”的姿態來發揚傳統。但“五四”確實是將傳統的批判發揚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對于傳統的重構或轉化卻做得不夠,在批判與否定中,在經濟與社會的巨大變遷中,傳統文化遭遇了空前的危機。
但更有甚者是“文化大革命”。建國之后,在經濟、政治、社會的改造上,我國確實取得了令人歡欣鼓舞的成就。對傳統文化的改良也可循序漸進。但一場“文革”卻把一切變得“面目全非”。“文革”由與“帝王將相”決裂發展到與一切傳統決裂。在“打倒孔家店”、“破四舊”、“掃除一切牛鬼蛇神”中,無論“精華”還是“糟粕”。都落得“孩子與洗澡水一起倒掉了”的境遇。余英時先生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以非理性乃至反理性的方式來消滅自己的文化傳統”,結局殊為悲慘。殘留下來的卻以糟粕居多,如權力統治所借助的集權思想和易于從形式把握的道學說教等等。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描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征:“資產階級除非使生產工具,從而使生產關系,從而使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革命化,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產方式,卻是過去的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生產的不斷變革,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馬克思在這里雖然只是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但他揭示社會轉型的一個特點,即一切固定的神圣的東西都不存在了。一切都只具有暫時性,傳統正是如此被消解掉了。傳統經驗就這樣與社會生活發生了斷裂。
改革開放之后,雖然國家大力倡導精神文明建設,但由于經濟建設國家發展的危機感,與抓住機遇的緊迫感的重壓,各種西方思想未加辨別的引入,傳統的精華尚未恢復便不得不在“封建傳統”的“帽子”下矮了西方一頭,致使更加難以發揮作用。總之,當代社會各種思想紛然雜陳。即使是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人們依靠歷史的殘碎記憶努力恢復傳統生活,傳統的影響也不會一時間消失無蹤,但傳統文化卻因為經驗的斷裂而“難復當日之勇”了。
信用作為傳統的支柱之一。境遇自然相似。原來適應已成和諧的經濟與社會已被基本消解,由等級制度和“差序格局”而形成的作用象限幾不可尋,它的內核——儒家思想——已經失去往日的權威,只能為一種“精英話語”廣泛存在,而于生活實踐的疏離感卻無可挽回。并且,在“文革”中的“陽謀”與“戰略”,市場經濟中的“金錢萬能”、“利益至上”的沖擊下,它的說服力日漸蒼白。剩下的或許只是“防人之心不可無”引導下的向傳統的回溯。卻或失去精髓或不合時宜。
就這樣,信用失去了它的經濟社會基礎。失去了它的儒家倫理文化內核的強大精神支撐和方向指導,失去了隱于其后的深刻社會文化內涵——它的意識形態性所確定的社會主體的行為方式及約束力。它變成了一個人們莫衷一是的“符號”。也即維系信用的社會機制喪失了其社會基礎而難以發揮作用,信用也就很難在人們的日常行為中展開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現在的“信用”是一個與傳統發生了斷裂的詞匯。它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期待著浴火重生。筆者提出應以憲法為根本,在構建社會主義法治的同時重建“憲法信用”,筆者將另行撰文,在此不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