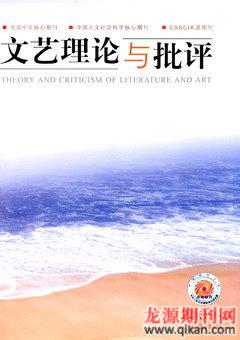由《潛伏》反思中國電影
米 靜
《潛伏》超出了觀眾的心理期待,給人以驚喜。從放映伊始,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在劇情上,扣人心弦;在情感上,能引起人們的共鳴;在精神上,又讓人在這樣一個思想混亂的時代,重新看到了一種革命的浪漫主義精神。《潛伏》主要講的是主人公余則成,一個國民黨特務如何轉變成共產黨的間諜,在敵內“潛伏”直到解放,繼續奔赴臺灣從事潛伏工作的故事。
《潛伏》的藝術性和思想性都在一個高水平上,情節曲折,節奏很快,符合現代觀眾的觀片心理,沒有拖泥帶水,似乎更少刻畫余則成的成長過程,這個人物從一開始就是成熟的,即使他的戀人左藍犧牲后,他也能一邊傷悲一邊繼續保持沉著的心態從事潛伏工作。故事從一開始就有一個接一個的情節,讓人也跟著緊張得喘不過氣來;在執行革命任務中,也交織進行著余則成與三位女性的愛情經歷,在革命與愛情之間設置了張力,使得故事更具可觀性。此片在敘事上也富有節奏感,每十集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單元,以左藍犧牲、晚秋赴西柏坡、翠平離開為標識,形成了一個個小段落,既有所區分又相互連貫,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藝術整體。
編劇姜偉在人物設置上也下足了功夫,主人公余則成的扮演者孫紅雷經常扮演的銀幕形象不是惡人,非常霸氣,每每出現都很有氣場,而此次出演一個具有小知識分子氣息的中共地下黨,由于種種細節的設置,又讓人很有信服感;片中余則成與之周旋的反派人物,吳站長、李崖、馬奎,甚至陸喬山都常常在其他影劇中扮演正面的角色,這些人的出現使這些反面人物大放異彩,各個鮮活,這些反面人物的臺詞是該劇中的亮點,比如吳站長對于“凝聚意志,保衛領袖”的精辟理解等等,吳站長的臺詞非常幽默又完全符合人物的身份。劇中三個女人,左藍,翠平和晚秋的形象與臺詞也恰如其分,這三位演員以前扮演過不同的形象,《潛伏》中有以往形象的影子,卻又完美演繹了自己的角色,讓人或敬愛,或憐愛,或同情。
畫外音也是此片的一大特色,在適當的時候,升華了觀眾的情感,比如余則成最后見左藍一面,畫外音響起:“這個女人身上的任何一點都值得去愛,悲傷盡情的來吧,但要盡快過去”;在送走晚秋的時候,畫外音是“即使終結了愛情,但卻復活了生命,上路時她有憾而無悔”;余則成誤以為翠平犧牲的時候,畫外音是“余則成知道,他只有這一夜悲傷的權力,明天還要繼續他的使命,上級已經下令撤離,但他不能走,一定要搞到潛伏特務的名單,每當身邊有人死去,他都會想到自己活著的價值,這是他更大的悲傷,他屢次告訴自己,你是殉道者,你要承受這些折磨,這些折磨就是理想的代價,必須全部承受,直到死”。這幾段畫外音是影片中最為感人的地方,將其放置在幾位女性離去的時候,也就是劇中余則成的心情最柔軟的段落,通過這種內心的獨白,引起了觀眾的共鳴,使觀眾進入人物的心理,并完成了接受一種思想感化的過程。
在中國電影整體不景氣的形勢下,中國的電視劇行業卻生產了不少深入人心的佳作,這是令人深思的現象。近年來出現的《星火》、《亮劍》、《大工匠》、《金婚》、《士兵突擊》、《人間正道是滄桑》、《敵營十八年》等優秀電視劇,叫好又叫座,不僅在普通觀眾中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在影視研究的專業領域也越來越受到注意,《潛伏》的出現可以說是一個新的例證。
中國電影目前存在的問題,大體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1)以張藝謀的《英雄》、《十面埋伏》和陳凱歌的《無極》為代表的“中國式大片”,追求音響與畫面的華麗、絢爛,但在思想內容上很蒼白,在敘事上也很混亂,甚至“講不出故事”,只能給觀眾以感官上的刺激,無法在心靈上給人以觸動;(2)以李安的《色,戒》、馮小剛的《集結號》和陸川的《南京!南京!》為代表的“新歷史電影”,試圖從新的角度講述現代中國的故事,但他們對歷史的闡釋缺乏邏輯的合理性,缺乏為人所接受的歷史觀與價值觀,有的甚至對中國人民的情感造成了嚴重的傷害;(3)以賈樟柯的《三峽好人》、《二十四城記》為代表的影片,試圖切人當下中國的現實,但他們所持的卻是一種外在的或“精英”的視角,對底層民眾缺乏真正深入的認同感,因而無法對“中國經驗”作出深刻的把握與闡釋;(4)以寧浩的《瘋狂的石頭》、《瘋狂的賽車》為代表的商業片或娛樂片,更多在技術上,或者說在故事的編織上下功夫,能給人以“炫技”之感,雖然具有一定的娛樂效果,卻似乎欠缺真正能打動人心的藝術力量。
以上所分析的,只是中國電影所呈現出的“癥候”,如果我們探討一下深層次的原因,便可以發現中國電影不景氣的根本原因在于:這些中國電影并不以中國人,尤其是廣大的底層民眾為預期的“觀眾”,它們所預期的觀眾是外國人尤其是某些電影節的評委,以及中國大中城市的精英或“準精英”階層。由此所帶來的問題是:它們并不站在中國民眾的立場上來講故事,它們所表達的價值觀念與中國民眾的價值觀有很大的距離,有時甚至不惜傷害中國民眾的情感,以取媚于那些預期的觀眾,或者顯示它們的精英姿態;它們在藝術上也不尊重中國民眾的審美習慣與審美趣味,而試圖以西方的某些藝術觀念去“引導”、“啟蒙”中國民眾,他們以這些觀念為“文明”或“進步”的標志,而視中國民眾的審美習慣為“愚昧”或“落后”,以讓普通民眾看不懂或不習慣為榮,正是這樣的“傲慢與偏見”使它們越來越遠離了中國民眾。
而電視劇恰恰相反,它們站在中國的立場上講故事,尊重民眾的審美習慣,以廣大的中國民眾為預期觀眾,這正是它們為觀眾所喜愛的根本原因。我們可以將《潛伏》與《色,戒》做一下比較,這兩部作品同樣是“諜戰片”,但其藝術上的趣味、側重點與價值立場迥然不同,所以被接受、評價的結果完全不同。
《色,戒》講的是一個愛國女大學生王佳芝成為國民黨間諜,被安插在汪偽重要人物易先生身邊,陷入了情與欲的掙扎和矛盾中,在關鍵時刻放走漢奸,最后被槍殺的故事。與《潛伏》相同,王佳芝也是“潛伏”在易先生身邊,但是該影片側重的并不是潛伏的故事本身,而是人物心理的細微變化。這部影片的藝術趣味在于探討人性本身矛盾的深幽和復雜,在鏡頭語言表達上也較為成熟,但其背后隱藏的價值觀念卻不僅瓦解了“革命”的價值觀,甚至挑戰了民族與國家的基本價值。李安借一個“潛伏”的故事,探討情與欲的關系,人物行為的動機是“刺殺任務”,而心理活動的動機卻是情與欲的矛盾,這是一個為西方觀眾所接受的主題,不管故事發生在任何時代,都有著超越時代和種族的意義,這是李安的聰明之處。但是由于他將故事放置在了中國特定的時代,人物的立場就會引起觀眾的廣泛爭論,因而在國內引起了激烈的批評。
在電視劇《潛伏》中,像《色,戒》中的那種“人性”范式得到了根本性的反撥:一個國民黨特務因為對一個女人的愛情、對自己原
來組織的失望,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敵我環境如此復雜的情況下始終毫不懷疑地執行自己的潛伏任務,甚至是在其深愛的女人被槍殺之后,他通過讀其留下來的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反而將這種私人的情感升華到對一個更加偉大事業的熱愛,他培訓了一個女游擊隊長從事潛伏工作,也挽救了一個布爾喬亞小女人的生命,使其忘掉自己心中的愛情,去追求更加崇高的事物。從人物的復雜性上講,《潛伏》不遜于《色戒》,《潛伏》呈現了時代中的人物群像,劇中各式人物形象都具有著其自在的復雜性,這些復雜性又沿著其自身的發展軌跡不斷完善,每個人最后都有著不同的歸途。全劇以一種高亢的革命浪漫主義精神超越小我內在的情欲矛盾,在各色人物復雜的關系沖突中,呈現了革命勝利前敵我斗爭的殘酷以及我黨地下工作者對共產主義信仰的堅定不移和革命必勝的信念。影片中也有情,甚至有欲,但是情不是主創要集中描述的,余則成所面臨的種種情感線索都是為了襯托出這個人物所具有的堅定信念,這些情感都要服從于這種信念,也升華了這種信念。
如果說《色戒》講的是一個女大學生心路歷程的故事,那么《潛伏》則是一個成熟的革命者如何堅定執著的完成“黨的任務”的故事,兩者的出發點和歸宿完全不同,而從《潛伏》這樣優秀的作品中,我們又能看到超越小我微觀世界的宏大視野,一種“我以我血薦軒轅”的革命浪漫主義精神。在今天,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都在經歷著太多的震蕩,我們該如何去觀照這個世界,如何擺脫自我的微觀世界,如何選擇我們的立場,電視劇《潛伏》如此受歡迎,給了我們很多啟示。喜歡《色,戒》的只是部分精英階層及“準精英”階層,包括白領、“小資”、知識分子、大學生等(持批評意見的,則是這一階層中更具思想性及反思意識的人),那么喜歡《潛伏》的人則遠遠超越了這一范圍,它不僅為部分精英階層所欣賞,而且也為廣大的中國民眾所喜愛,這是其成功的一個標志。
電影與電視劇有不同的制作、拍攝、發行方式。一般而言,電影投資較多,工程較為重大,在藝術上也更為人重視,按道理應該在創新方面走在電視劇的前面,但在當今的\中國卻恰恰相反,反而是電視劇叫好又叫座,不斷創出收視率的新高,而電影的受眾階層卻越來越狹窄,即使看的人也是“邊看邊罵”,這一現象不由人不深思。看來中國電影應該更接近中國觀眾,站在他們的價值立場上,尊重他們的審美習慣,這也是《潛伏》熱播所給我們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