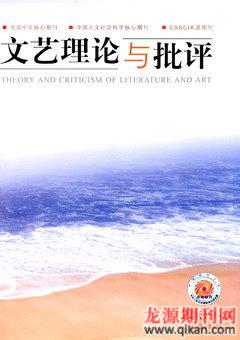論劉慶邦小說中的民俗系列
陳英群
民俗,即民間風俗,指一個國家或民族中廣大民眾所創造、享用和傳承的生活文化。文學起源于勞動,是用來反映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社會歷史生活的,自然與民俗結下了不解之緣。民俗文化凝聚了一代又一代民間百姓智慧和經驗的結晶,充分體現了一個民族的藝術才能和思想情感。自古以來,不少文人墨客的創作都曾受惠于民俗文化,從而寫出了流傳于世的不朽佳作。一些有過鄉村生活經歷的作家,深深地受到民俗的浸染和熏陶,自覺不自覺地在作品中融入了民俗色彩,打上了自己思想情感與個性特色的印記。劉慶邦正是這樣一位帶有鮮明個性的優秀作家,在其鄉村題材的小說里,無不傾注著他特有的鄉土情感。孩童時期耳濡目染的鄉村民俗,帶給作家無窮無盡的回味,引動著其創作的思緒和靈感。劉慶邦在描寫其故鄉的世態人情、風土習俗以及生活方式時,嫻熟地將鄉間民俗的描繪同刻畫人物和推動情節的發展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幅幅充滿詩意的鄉村風俗畫,使得其鄉土小說凸現了不同凡響的藝術魅力。
一
在傳統社會中,婚姻被當作人一生中的頭等大事。自古以來,青年男女的婚姻程序大都遵循著周代即已確定的“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迎親”這六種從議婚至合巹過程中的禮節。隨著時代的變遷,“六禮”的程序在不斷發生變化,婚姻程序總的演進趨勢由繁至簡。相親、相家、訂婚、結婚,這是大多數鄉村青年男女所要經歷的婚姻程序。
相家這一相傳很久的民俗,在農村一直延續至今。對于女方來說,若是自由戀愛,心甘情愿要嫁的另當別論;若是紅娘牽線,大多都要走一回相家程序,除非知根知底等特殊情況。相家,是女方父母為了女兒的前途、命運和一生的幸福在婚姻上把握的第一關。在豫東平原,相親之前要先相家。《相家》中的女孩子染已到了論婚嫁的年齡,她擔心母親聽信了表叔的“吹大氣”,不明就里地讓她貿然去相親。其實不然,只有母親真正對女兒的親事上心,她不為媒人的如簧巧舌所動,準備親自前往男方家相家。母親做著手上的準備工作,補了一雙棉襪,做了一雙新鞋,還借了一身適合相家時穿的褂子;其內心的準備則不為他人所知,人還未出門,夢里的相家已經去了好幾次。按照約定時間,母親走著去了21里外的男方家里,最終做出了不讓女兒跟人家相親的決定。劉慶邦以高超的創作功力,妙筆生花,將母女親情融入相家這一鄉村風俗之中,準確細膩地傳達出母女連心的微妙情感世界,展現出特有的鄉間生活氛圍里那份自然動人的魅力。
在擇偶方式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傳統社會中必須通過的第一個婚姻程式,婚事大權掌握在雙方家長手里。隨著社會的進步,“相親”的主角大多已由雙方家長換成男女當事人。雖然很多農村青年的婚姻還是經媒人撮合而成,但相親已成為大多數男女當事人必須親歷親為的一道程序。劉慶邦饒有興趣地以小說的形式涉筆“相親”這一婚俗,在多篇作品中娓娓述說了幾個不盡相同的相親故事。《閨女兒》中的女孩子香15歲,《紅圍巾》中的小姑娘喜如虛歲才15,就被大人們拉著相過一次親。誠然,農村的早婚現象比較普遍,尚未成年的少男少女較早涉及相親也不足為奇。喜如的相親是一個無言的結局,她把這次失敗歸結為沒有借到一條紅圍巾。紅圍巾確實是某個年代里一件代表著時尚的物品,也是鄉村姑娘夢寐以求的奢侈品。相過親的喜如有了心事,紅圍巾就是一個最大的心事。少女香心地如清泉般潔凈,對世間人事還朦朦朧朧,感覺自己將要成為相親中的一個角色并不十分好玩,恍惚間童年時扮新娘的游戲依然鮮活有趣。她看上去似乎對大人們的安排多少有一點點抵觸,最為擔心的是鄉鄰們知曉她此次活動的秘密。不管是否情愿,香還是跟在母親身后去了約會的河邊。她和同齡的那個中學生隔著些距離坐在綠草如茵的河坡上,兩人尷尬地搭訕了幾句,生澀地預演了一場本該由成年人做主角的游戲。平日里,勤快的香言語不多,心里常常自說自話,隨之笑意就從心底漫溢出來。幸福是什么?香正在感受著。無論相親的結果怎樣,香仿佛已經歷了一次人生成年儀式的洗禮,心理年齡陡然增長了幾歲,少女的心房有了屬于自己的秘密,快樂的生活中平添了些許淡淡的傷感。整篇小說勾勒出極具動感的鄉村風俗畫,流動著極其悠揚的村野小唱。
若相親成功,男女雙方便可進入訂親程序。在農村很多地區,訂親常常是男方所要面對的一道不能繞過的門檻,大多都要往女方家中送一定數量的彩禮。劉慶邦并沒有就聘禮這一習俗的具體操作發表議論,而是不吝筆墨地描寫在男女青年之間尚不敢大膽交往的那個年代當事人訂婚后的心理活動,絲絲入扣地呈現了此一方對彼-一方深切思念的淳樸感情。在《夜色》中,周文興心疼未婚妻高玉華在出嫁前要為娘家脫坯蓋房的舉動,恨不得馬上跑過去替下心上人。他不好意思大白天貿然到高家莊幫對象干活,就趁著夜色前去幫著翻坯。周文興發現高玉華躲在麥秸垛邊,哨悄觀察,上前想見,卻沒有喊出聲。《春天的儀式》開篇由三月三的廟會人手,溫煦的春風與熱鬧的廟會帶給人們無限遐想。年復一年的三月三廟會不知從何朝何代起,一年一度的這個廟會成了鄉民們的一個節日。這年的三月三對于女主人公星采來說非同往年,在她的心里陡添了一份期盼。在自由戀愛沒有得到普遍認可的環境下,鄉村常見的媒人介紹,星采看來還是滿意的,她已經開始心系那個只見過一面的對象,三月三給了她可以再次看到“張莊那孩子”的機會。劉慶邦不愧是一位描寫女性心理活動的高手,如明鏡般洞悉了一個青春少女的隱秘情思,把星采表面故作鎮定、內心卻波瀾起伏的微妙心理,一層層剝筍般展露出來,讓人讀來忍俊不禁。作者不著痕跡地將星采尋覓“那個人”的心思行為溶注進鄉間廟會這一民俗之中,使得一個再簡單不過的故事,點染上特有的鄉間風情,吹奏出詩意的鄉土樂章。星采置身于廟會歡慶的氛圍中,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她極力在擁擠的人群中尋找一個人的身影,而當朝思暮想的那個人顯然向她走來之時,她卻慌亂得不知所措。小說在此戛然而止,事情的結果倒顯得不怎么重要了。
二
婚禮意味著男女當事人正式攜手步入婚姻的殿堂,“鬧洞房”則是鄉村婚禮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習俗。歷來民間有“新婚三日無大小”的說法,婚后三天,賓客、親友、鄉鄰不分輩分高低,都可以擠在洞房里逗鬧新郎新娘,即使鬧得有些過分,新人也不能惱怒。《走新客》中的新娘大銀被鬧了個人仰馬翻,當一個又硬又重的枕頭砸在額頭上時,疼得實在忍不住了,就大哭著罵了起來,最后落了個“性子太野,不識玩兒”的評價。新郎長星也不怎么同情大銀,認為“人家跟咱鬧,是看得起咱,說明咱們家在村里人緣好”。《不定嫁給誰》中的新娘子小文兒心情不大好,對人們肆無忌憚地鬧房流露出煩躁的情緒。她一直在期待著一個人的出現,那就是曾和她
相過親的田慶友,正是因為自己當時的矜持,便永遠錯失了做這個人妻子的機會。《摸魚兒》中的男孩子春水才十四五歲,身體正處于發育的上升階段,已有了性欲的萌動,對同齡女孩子替的身體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利用高山婚禮上鬧洞房時,春水心懷鬼胎地等來了替,渾水摸魚偷偷摸了替的奶子,拽了替的褲子,第一次實施了對替的身體觸摸。春水掩飾不住成功的喜悅,故意讓替察覺他做了什么。而替在基本認定是春水對自己的身體侵犯過時,并沒有表示出真正的生氣,甚至不大忍心拒絕一起去“聽房”。在聽房的過程中,春水對替的身體進行了更大幅度的探索。春水“想跟高山學習”,替擔心“懷了孩子怎么辦”,但春水似乎已經得到了替的某種默許。果不其然,此后的一天中午,在一個廢棄的瓜庵子里,替裝作睡著讓春水終于得逞。隨后,兩個小人兒持續地進行著這種假裝睡覺的游戲,直到女孩子替真的懷孕了。春水原本只是想著玩一玩,最后只好把替娶進家門。一對少男少女從婚禮中學習了成年人的行為,過早地對性這個神秘領域進行探索,他們越過相親、相家、訂婚等婚姻程序,直接開始了漫長的婚姻生活。小說《摸魚兒》筆致從容,情節舒緩,充滿著濃厚的鄉野氣息和村野情趣。
婚禮的最后一項是“回門”,即新婚夫婦同去女家省親的婚俗。這一婚俗,從女兒方面來說,表示出嫁后不忘父母養育之恩;從女婿方面來說,除感謝岳父岳母恩德外,還有拜會結識女方親友的交際意思,帶有認親的性質。在農村很多地區都有“鬧新婿”習俗,所以“回門”對新女婿來說,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因新娘的姐妹們會放肆地嬉鬧新女婿。大概是“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吧,劉慶邦的《回門》中大姐新婚回門時并沒有新女婿的陪同,而當地的規矩是新女婿在新婚第一年的大年初二去拜訪新娘的娘家人。這一過程稱作走新客,“鬧新婿”的節目即在此時上演,且男青年是嬉鬧新女婿的生力軍。《走新客》中的新女婿長星對第一次陪妻子大銀回娘家感到發憷,還未前行就已憂心忡忡。原本滿身田野之氣的大銀,在丈夫的調教下已初顯女兒家的溫柔,很樂意接受長星“算大賬”的提議,并應承在丈夫受村人戲弄不堪之時搬兵搭救。長星最初也是想著忍忍了事,但當一個男青年用手掌打了他的腦瓜子時,感到傷了自尊的他以不再給那青年點煙表示抗議,雙方對峙陷入僵局,直至大銀悄悄搬來大奶奶才解了圍。正所謂男兒有淚不輕彈,當晚上大銀把受了委屈的丈夫擁入懷中時,觸覺到濕漉漉的淚水,便以小夫妻協議的“算大賬”的方法來安慰長星。劉慶邦借走新客“鬧新婿”這一習俗,含蓄地將一對新婚夫妻床幃隱情曝光,走新客帶來的一絲煩惱轉眼淹沒在“算大賬”的歡娛之中,尋常百姓家簡單而甜蜜的生活掀起層層詩意的浪花。
三
盡管各地各民族的風俗習慣不盡相同,但人的一生大都會閱歷無數的人生儀禮內容,若從大的方面看,很多地區都有童禮、婚禮、壽禮、喪禮等幾個部分。“既然一個人從降生到成年,都是處于周圍民俗事象對他的浸染和熏陶之中,他自己也總是處處摹仿;而且民俗在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如此舉足輕重,其潛在心理力量如此不可抗拒”。在現實生活中正是如此,很多民俗被人們一代又一代地傳承下來。歷史上有不少的文人,如曹雪芹、魯迅、沈從文等,嫻熟地在文學作品中隨筆點化民俗的色彩,為文學寶庫奉獻出不朽的佳作。劉慶邦的小說,通過豫東平原地方習俗成功地寫出人物性格和人物關系的例子很多,幾乎涉及了人生儀禮的各個部分。
在人生儀禮的眾多活動中,大都寄托著至愛親朋的美好愿望和祝福。在長篇小說《紅煤》中,宋長玉在明金風的母親生日之際,適時地送上了一個生日蛋糕,使得明大嬸兒驚喜不已,此舉為宋后來能夠娶到明金風奠定了很好的基礎。若干年后,宋長玉已富得流油,一次為岳父明守富慶賀生日時,他不僅定制了一個很大的生日蛋糕,還包了一桌十分豐盛的酒席,并委托妻子奉上一萬元的賀禮。醉翁之意不在酒,宋長玉得到時任村支書的岳父大人恩準,入黨一事順利解決。很久以來,祝壽禮儀在民間風生水起,大有愈演愈烈的勢頭。其形式上已融入了西方元素,成為親友們聯絡感情的一項重要活動。
生與死分別是人生跑道上的起點與終點,有關人的生與死的儀禮很多。童禮是與孩子出生相關的一些人生儀禮,有著一系列的儀式活動,用來寄托親友們對新生命誕生的祝愿和希望,這些祝愿和希望無不打上了信仰和宗教的烙印。如有的地區為嬰兒剃發時,要在嬰兒前腦門上留約一二寸見方的胎毛,家人以借留胎毛來表達望子成龍的殷切希望。在小說《尾巴》中,劉慶邦講述了一個過去年代時有所見的留胎毛故事。小旺從小就與眾不同,他的腦瓜上留有被稱作“尾巴”的一塊頭發。可以說,小旺是被人拽著“尾巴”開始長大的。父母拽他的“尾巴”,表達對他無比的寵愛;父母歡迎且有意讓村人們拽他的“尾巴”,他也不是十分反對。直到上學之后,小旺才真正感到“尾巴”帶給他的煩惱。同學們惡作劇地拽他的“尾巴”,讓他窮于招架。他哭鬧著要將“尾巴”剪去,母親告訴了他留“尾巴”的緣由,“尾巴”關系著他生命的存活。小旺十二周歲生日那天,其父母搞了一個隆重的儀式,把他的“尾巴”剃掉了。且不論“尾巴”是否真的有什么神奇的效用,父母祈求小旺健康成長的良苦用心確實不難理解。
誰不希冀自己的親人健康長壽呢?但世上畢竟沒有長生不老藥,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則是不可抗拒的。《葬禮》的背景在國家經濟最為困難的那一年,“我”的父親突然得了急病撒手人寰,當時連一片做棺材的木板也無處可尋,只好將家中的一個站柜改造了。吹響器就免了,別說沒有錢請響器班子,就是有錢請得起,餓著肚子恐怕也吹不響。除此之外,葬禮的各項儀式還是按部就班地進行。“我”是長子,負責為父親摔老盆和扛引魂幡。死者有多少個子女,就可由子女在老盆的底部鉆多少個眼,這樣死者到另一世界前需喝掉的水會漏掉一部分,不至于喝不完水被拒之門外,成為四處游蕩的鬼魂。在送葬的路上要將引魂幡上的紙帶一條條撕去,起一種路標的作用,引導死者的魂靈離開家門,順利上路遠行。在《黃花繡》中,三奶奶快不行了,14歲的小姑娘格明被選上來為三奶奶送終的鞋上繡花。格明從未繡過花,但她符合繡花人的三個條件,即家中父母雙全、兒女雙全、本人是16歲以下的童女。格明推卻不掉,只好臨危受命,務必要趕在三奶奶斷氣前繡出兩朵小黃花。她感到自己手上的責任重大,用了一整天的時間摸索著完成了繡花任務。雖說寫的是一件喪事,小說中并沒有太多悲痛的氣氛,反而透射出些許明亮的光澤。至少在格明的眼里,兩朵金黃色的花是那樣的光彩爍爍,繼而升騰出滿屋子的花朵。如果相信靈魂存在的話,那么逝去的親人應該安心過渡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豫東平原稱嗩吶為大笛,只有喪事才請
響器班子。《響器》中的高妮天生是大笛的知音,她如夢如幻地循著大笛的樂聲而去,“大笛剛吹響第一聲,高妮就聽見了。她以為有人大哭,驚異于是誰哭得這般響亮!當她聽清響遏行云的歌哭是著名的大笛發出來的,就忘了手中正干著的活兒,把活兒一丟,快步向院子外面走去。節令到了秋后,她手上編的是玉米辮子,她一撒手,未及打結的玉米辮子又散開了,熟金般的玉米穗子滾了一地。母親問她到哪里去,命她回來。這時她的耳朵像是已被大笛拉長了,聽覺有了一定的方向性,母親的聲音從相反的方向傳來,她當然聽不進去”。高妮站在離響器班子很近的地方,如癡如醉地沉浸在時而凄婉時而高亢的樂聲中,淚水不由自主地順著臉頰滑落。她不是為死人感傷,而是為樂曲動容。四五里地外斷斷續續傳來大笛的聲音,如仙樂夢幻般縈繞在她的耳畔,牽動著她的思緒,促使她逃脫母親的看管,奔向大笛響起的地方。大笛的樂聲在她的腦海里幻化成無數美妙奇幻的畫面,勁風吹過,蔥綠的麥田翻滾出金黃色的麥浪,滿地的高梁與天邊的紅霞連成一片,暴風雨敲著鼓點響起來了,漫天大雪飄飄灑灑覆蓋了整個大地。高妮仿佛就是為大笛而生,十四五歲的小閨女兒執拗地要學吹大笛,父母的軟硬兼施根本無法動搖她的決心。她最終如愿以償,拜大笛手崔孩兒為師,吹上了大笛,吹成了氣候,吹出了陽光燦爛的一片天。
劉慶邦不愧是文學創作領域的一位出色的大笛手,他的作品就是他的響器,他通過自己的小說發出了柔美響亮的聲音,吹出了一片具有獨特風格的文學天地。水有源,樹有根。劉慶邦把自己創作的根深深地扎在民間這塊廣闊的土地上,在很多作品中都注入了民俗文化的元素,溶進了豫東平原的民俗事象,點染出特有的家鄉風情民俗色彩,塑造出典型的鄉村人物形象。“由于民俗是構成民族生活文化史的主體與核心,作家在反映社會生活時,也就必然地在自己的著作中程度不同的溶注進本民族廣泛的民俗事象。而反映民俗事象的本質,也常常是檢驗一個作家和人民關系的微妙尺度”。劉慶邦從事文學創作30年來,始終真誠地面對底層,傾心關注底層,堅持選擇自己熟悉并感興趣的鄉村生活為素材,而不隨波逐流。不能否認,劉慶邦是文壇一位辛勤的勞作者,在自己創作的小說中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和誠實的心,把特定的社會生活和民俗現象熔鑄進文學作品之中,因而其不少佳作都發出了“驚心動魄”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