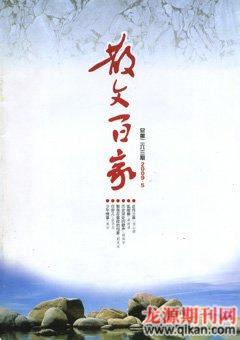走進徐志摩故居
王 英
進入詩人徐志摩的故鄉——古鎮硤石,就似乎有一彎溫柔的“新月”斜斜地彌漫了我的心頭。沿小街往左拐進一條弄堂,這弄堂就如同一行幽長而美麗的詩將我引行著向前。幾年前,金庸回故鄉探親,特意書寫了“詩人徐志摩故居,表弟金庸敬題”的條幅,首次揭開了一位新詩的開拓者與一位新武俠小說的開山者是表兄弟的秘密。現在“詩人徐志摩故居”的匾額便在眼前。
隨友人跨進那扇黑漆方庫門,穿過天井走入正廳,輕步登上那微微作響的木質樓梯,瞻仰我喜愛的詩人的“精神家園”。徐志摩為與紅顏知己陸小曼結成連理,與前妻張幼儀笑解煩惱結。1926年10月,徐志摩如愿以償娶小曼為妻,婚禮上雖有良師梁啟超以證婚為由予以譴責,仍然沖不淡他倆心心相印的濃濃愛情。不久,徐志摩辭去《晨報副鐫》主編之職,攜嬌妻從北京回硤石,雙雙棲在由父親為他營造的“香巢”。新婚燕爾,白天他與小曼到東山撿浮石,在西山覓沉蘆;傍晚倚窗望月,吟詩作畫,相互切磋,悠然自得、飄然欲仙的這份心情,可以從徐志摩給前妻張幼儀的信中體會到“從此我想隱居起來,硤石有蟹和紅葉,足以助詩興,更不慕人間矣”。他認為自己所追求的理想、愛情和自由終于有了個生根開花的家園。在這里他寫下了蜜月日記《眉軒瑣語》的第一篇,完成了小說《家德》的構思。不久,孫傳芳兵臨硤石,花艷稻香的江南,一時成了軍閥割據的地盤。徐志摩的“隱居”夢瞬間成了泡影,他和小曼只得匆匆移居上海,此后他便很少再回來居住。然而當我穿行于每幢小樓的房間時,仿佛感覺到詩人的靈魂還在,它與黑漆的門窗渲染出一種獨特的意境,這位浪漫的詩人是否每一篇杰作都孕育于這“草青人遠,一流冷清”的家園呢?
徘徊在故居中,我仿佛感受到詩人與小曼仍在這里生活,無論整套粉色家什和那架孿生銅床,他倆合用的“眉軒”書房,抑或那極富西洋風格的壁爐,似乎都滲透著志摩“恨卿來遲”的柔柔戀情。尤其是主樓后面小院中的“新月樓”,據說原來是徐志摩邀友人小聚的地方。他曾寫信邀請胡適、劉海粟“徑行來硤石,新廬盡可下榻”。院中的花草樹木,尤其是那口古井,水質甘甜,似乎還蓄存著詩人“濃得化不開”的深情:“眉(陸小曼的小名),這一潭清冽的泉水,你不來洗濯誰來,你不來解渴誰來,你不來照形誰來!”我仿佛聽見詩人情真意切的話語。
新月樓西側有一小樓,登上頂樓平臺,可眺望東西兩山,也可觀天望月,故名“望月臺”。據說這是詩人按照自己的詩篇設計的。徐志摩是位“想飛”的詩人,他喜歡觀花、看山、玩水,更樂意在天空中“飛翔”,如若不是,也就不會有日后“飛去云霄”的悲劇。然而我想像他一定是與小曼合牽著一只風箏,放飛一只矯健的紙鳶同時呼喊:“飛,快飛,到云端去,到云端去!”他當初一定如小孩般雀躍著,留下過非常深刻的印象,要不,詩人怎么寫出文思飛動的詩篇《飛揚》來呢?友人告訴我,詩人少年時代生活和讀書的地方是在保寧坊徐氏老宅。于是,我們走出新月樓,南行數百步,到了詩人的祖居,也就是詩人真正的故居。
這是一座富有江南特色的深宅大院,前后有四進。跨入第二進院門,右側是廂房,樓上是讀書樓,即以前家塾所在。詩人五歲時在這兒受啟蒙,六至十一歲師從查桐軫,他是金庸(查良鏞)的本家伯父,是位貢生。老夫子生性怪癖,但學問不錯,教了志摩五年。雖說志摩清風白云般的性格與晦澀難懂的文字格格不入,但也為他打下了扎實的古文功底。樓中間有一小天井,僅五步寬,方形鋪磚。我想,當年的志摩大概就是站在這里看云彩的變幻,星月的隱現,閃電與彩虹的游移。或許真是這陰深的大院老宅令童年的詩人感到沉悶與不安,以至于醞釀起“想飛”的念頭,從而產生了噴薄而出的輝煌詩篇。
出了院子,往北經過長廊,第四進樓是徐志摩父母的臥室。1897年1月15日(農歷12月13日),詩人就出生在這里。當我站在長滿青苔的長窗前,眼前仿佛浮現出孩提時代的志摩。據說周歲那天,徐家舉家慶賀,按照江南的風俗,行“晬盤之喜”。正當頸掛長命鎖的志摩在紅漆木盤里亂抓亂摸時,突然闖進一個名叫志恢的和尚,他在志摩頭上撫摸后說:“此子系麒麟再生,將來必成大器。”這一說法,似乎有些玄乎,但少年時代的志摩決定放棄父親讓他學習的金融專業,而后遠涉重洋,將自己的性靈融化在康橋的柔波里,譜寫出一道道優美而震撼世界的詩作,直到他僅四十五歲的生命像詩一般結束:“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
詩人去了。他被安葬在離祖居不遠的那座紫微山一個叫白水泉的地方。我走出故居,前往墓地。墓地雜樹縱橫,蕭條靜穆,顯得異常清冷。想起詩人一生遍游海外,友朋如云,死后卻孤寂地葬在荒山一角,不免黯然神傷。然而又想,歷史終究是人寫的,詩人終究也以他的輝煌業績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不該再有太多的遺憾吧!
詩人一生熱愛自然,追求光明崇尚自由,誠如他在一首詩中表白:“我是天空的一片云/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這故鄉的風,山中的月,天空的云,無不映襯著詩人的靈光。他投射的影子會永遠留在故鄉的天空,他放射出的光芒也會永遠留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