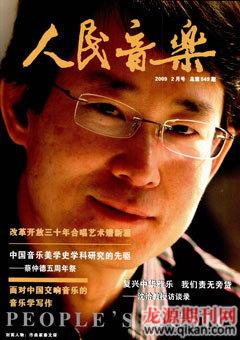音樂流淌 歲月留痕
陳 原
翻閱三十年來的《人民日報》,似乎也是在翻閱中國音樂發展的歷史,尤其是那一段艱難跋涉、步履蹣跚的歷史。從三十年來每個歷史階段的音樂與《人民日報》的關系,我們既可以觸摸到中國音樂的歷史脈搏,也可以感受到中國社會的歷史腳步。
鄧麗君、流行音樂、新潮樂派、搖滾樂、西北風,這些改革開放以來音樂發展三十年中的一個個關鍵詞,曾經有力牽動著三十年文化的歷史心弦,是社會思潮流變的鮮活表征。每個時代,對這些詞匯的感應也迥然相異,因而成就的每一種記憶,就是一個時代的生動形象。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鄧麗君、流行音樂、新潮樂派、搖滾樂、“西北風”,處于事實上廣為傳播,而話語上又相對無權的狀況。大潮勢不可擋,話語權卻長期缺失,其實這是幾乎任何一種新藝術、新品種、新技法在那個時代的普遍生存狀態。但沒有話語權就沒有生存地位,這也是那個時代人們的共識。
那個時代依然是政治主導一切,所以,身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可謂一言九鼎。這些不尷不尬的藝術能否在政治上取得一種合法的身份,也就是說能否由《人民日報》出面發言表態成為關鍵。為了支持藝術的多樣化,也是為了爭取話語權,《人民日報》發表了《崔健的歌為什么受歡迎》及《一無所有》的曲詞,使幾近喪生的崔健和搖滾樂轉眼間變得理直氣壯;《人民日報》相繼發表了居其宏、喬建中、繆也、魏廷格、王安國、梁茂春、金兆鈞、李西安、王次熠、王寧一、戴嘉枋等人的文章,從理論思辨到作品分析,闡述了流行音樂、新潮樂派、“西北風”對音樂發展和社會生活帶來的積極意義。以黨中央機關報的身份為這些藝術正名,今天看來是一種莫名其妙的舉動,但在那時卻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尤其是用半個版的篇幅為崔健正名和用半個版正面評價流行音樂這兩件事情,被外國媒體廣為報道。多年后我去美國,一位當年曾在華學習工作的美國人談及此事時還感慨不已,認為是我國文藝開放的信號。介紹崔健文章發表三個月后,我乘坐出租汽車,司機聽說我是《人民日報》的記者,興奮地轉頭告訴我他一直保存著這張報紙,并從屁股底下抽了出來,連連叫好。在一次政治環境的巨變中,流行音樂和新潮樂派又受到了一次沉重的壓力,中國音協的晨耕和張非兩位先生特意建議《人民日報》刊登李煥之主席的文章;在以后的政治風波中,上海的戴鵬海先生也專門寫來了賀綠汀大師的專訪,這些文字扶助了流行音樂和新潮樂派順利過關,避免了撻伐的戕害。1988年,《人民日報》和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這兩家正部級單位聯合舉辦“新時期十年金曲和金星”的推選活動,來自全國各地的幾十萬張選票選出的演員和作品中就有流行音樂、搖滾樂及其歌手。在隨后北京工人體育館和濟南體育館舉行的開幕式和閉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以及中宣部、文化部、廣電部、解放軍總政治部、山東省的主要領導一起到場,而壓軸的演員正是崔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對此全程直播,成為一個前所未有的文化事件。從此,流行音樂、搖滾樂堂堂正正地成為我國藝術事業的一部分。定格在此時記憶中,我們可以了解到,那個時代是一個摸索、奮爭、交鋒、爭執、進步的時代。
到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后,鄧麗君、流行音樂、新潮樂派、搖滾樂、“西北風”,雖然依然存在人們的記憶中,但是卻處于一種話語的淡化狀態,只做不說,所以沒有強烈的理論記憶話題。這是因為市場經濟在當時就是做得多說得少,如此行事,可以回避意識形態的重重困擾,達到徹底突圍的目的,并且,那時的人們也失去了爭論的興致,一律轉向務實派,賺錢第一。那個時代,在我們記憶里,鄧麗君是一種文化的象征,代表了流行、美妙和跨界;流行音樂則是一種根本擋不住的文化,不能不普及到每個角落;流行音樂的先鋒——港臺音樂更是大行其道,人們對港臺音樂討論也已經由應該不應該,限制不限制轉移到,出場費多少、大陸歌星報酬偏低這樣的經濟類話題。新潮樂派以及那一代作曲家,幾位風頭人物早已相繼出國,其余正埋頭用功,潛心創作,沒有人再關心這一樂派的生死或者去向。搖滾樂的后起之秀則層出不窮,崔健成了前輩,想唱也要先看市場,“唐朝”、“黑豹”的時代也是稍縱即逝,風光不再。“西北風”一頭鉆進了歷史,成為往昔的回憶,連曾經屬于不屬于流行音樂都成了一個問題。《人民日報》呢,盡管繼續刊載崔健的消息和介紹“唐朝”、“黑豹”的文章,并且首次開辟了音樂排行榜,但除了一次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有人質問《人民日報》為什么介紹“唐朝”和“黑豹”,一次“兩會”期間來自山東的農工民主黨政協委員提案質問《人民日報》介紹崔健是宣揚什么反對什么之外,無論是高層領導還是普通讀者中已無多大反應,對那些質問也覺得毫無意義。此時的社會,尤其是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式登場后,意識形態的爭論漸漸成了非主流,政治顏色在音樂中日益模糊直至退隱,什么事情只要大家接受也就理所當然地取得了自己的地位,無需《人民日報》這樣的輿論再加以左右。
現在,新潮樂派已經從人們的記憶中完全抹去,這個詞聽起來都讓人發噱。但值得玩味的是,新潮樂派的當家人物以及那一代曾受到強烈質疑的作曲家們,無論身份地位還是作品演奏,如今已經納入主流文化中心地帶,其話語也具備了霸權的可能性,日益成為文化乃至全社會的重要人物,其主流社會的位置也遠遠高出當年批判他們的人物。無論什么樣的音樂會,什么樣的影視劇,直至主旋律演出、奧運會開幕式,他們都不可或缺。遙想20年前,難免昨非今是、昨是今非之嘆。當你和今天年輕的一代再講述對王酩、李谷一的討伐、對蘇小明歌聲的過度反應、對鄧麗君的禁止,再講到流行音樂的各種爭論,他們一定會瞪大眼睛,覺得我們這幾代人有很大的毛病?現在的流行音樂唯恐不流行,只要有市場,其他根本不予考慮,但是即便如此,還常常陷于歉收的荒年之中。人們爭論的是盜版、侵權,沒有人再關心我們曾經認定是大是大非的那些問題。至于搖滾樂,現在需要憂慮的是如何留住觀眾;至于“西北風”,已經塵封在音樂的歷史記憶里;至于鄧麗君,那只是甜蜜蜜的美好回憶。這樣的音樂記憶表明,我們今天的時代已經是允許文化多元的時代,鼓勵流行文化的時代,推動市場文化的時代。當然,在一個網絡的時代,大眾文化的話語權也被廣泛下放,甚至出現濫用之勢:在一個多媒體的時代,文化的大眾性正被逼到不顧一切的位置;在—個充滿物質誘惑的時代,音樂家不能不趕緊急轉身,終極目標終于鎖定在經濟利益之中。《人民日報》也徹底從音樂文化的指導位置上退出,與其他媒體一樣,聽則有,不聽則無。最近,幾乎所有回顧音樂三十年的文字,沒有一字提及《人民日報》在三十年音樂發展的歷史作用。可見,在今天人們的記憶里,已經根本不可能將這家政治性極強的報紙與音樂聯系起來,多年前的政治環境、意識形態的主導結構及其操作方式,逐漸處于失憶的狀態。
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是社會變遷飛快的時代,由于變化太快,許多往事匪夷所思;由于變化太大,許多舊話更是莫名其妙。撫今思昔,難免感慨萬千。陳原《人民日報》文藝部高級記者
責任編輯于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