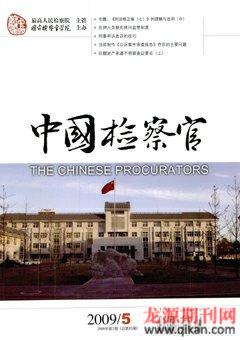接觸“村官”
念建平
接觸“村官”,是我們著手開始有關農村基層組織專題調研、為認識和剖析“村官”積累寫作素材所必需的實踐基礎和工作片斷。
《檢察日報》的一則短訊激起我們內心那些未有停歇的思慮。該短訊提示,目前我國腐敗態勢已由城市發展到鄉村,農村基層干部逐漸成為腐敗的高危人群。
據報道,我國現在只有深圳市消除了“城中村”,西安市同其他大中城市一樣還在積極改造“城中村”,發展和擴建城市,而在此過程中,作為一級組織成員的農村基層組織的“村官”們在干什么,他們能否嚴守自律?羈絆“村官”履職的因素有哪些,成為我們挖掘目前農村基層組織的調研主題。為保證這次調研的真實性、說服力和它日后的實效性,經過充分醞釀,我們決定通過實地調研尋找答案。調研藍本選擇了土地面積大、農村人數多、且由縣晉區時間不長的長安區,并以該區近年來對所轄“村官”培訓情況和“村官”職務犯罪統計數據作為調研的基本素材。
5月,祈望豐收的季節,車子行駛在鄉間通衢大道上。窗外不時閃過的成片別墅區以及零星的、尚在開發的、在建樓群,提示著這是一個正在被城市不斷擴張的農村縮影。
我們到達周家莊的時間,按往日農家習慣該是開始一天勞作的時辰,但通往村委會的路上,只看到清掃門庭的老人和恣意嬉戲的孩童。周家莊村委會門前,是一大片被某大學征用的土地,散亂的磚瓦,翻新的泥土,傲立的掘土機,無一不表示該村傳統農村土地經濟正在被顛覆和瓦解。出來迎接我們的是該村黨支部書記老劉。據他介紹,土地被征用后,村里近80%的農戶已以飼養業和運輸業作為主要生活支柱,即便是仍有少量殘余土地的村民,也因道路暢通了、商品流通了,更重要的是土地不多了,于生存、于發展,基本上都不依賴土地,而更傾向于發展多種經營。
說到如何做好“村官”,尤其是本村土地征用事項的談判和款項發放等,劉書記表示這是一個讓人頭痛、麻煩的事,但越是這個時候,越是檢驗“村官”公心私心、“村官”有無工作能力的時候。劉書記現在對此很自信。從31歲開始當村書記,他本人已有7、8年村辦企業任廠長的經歷,但說到為官之道,劉書記掩不住對過去的尷尬、愧赧之情,“以前搞工作,計劃生育、收繳公糧,我沖在第一。誰不聽話,我就扭他的胳臂,搬他家的電視機,用水灌他的麥。人家急了,把我往外掀,放狗咬我……”對工作方式的轉變,老劉的思路是:“工作咋就成了這樣子?鄉里鄉親的,以后還要在老先人丟的地上活人呢。我總結反省,改變自己。現在村里不再雞飛狗跳了,村里的大小事基本上都能平和地解決。”
劉書記認為,19年間,周家莊村委會換屆選舉,他能夠取得村民信任而得以連選連任的法寶,在于加強自身思想修養。1995年長安區組織部邀請他作為優秀村官代表在換屆選舉動員會上講話,他短短說了幾句:“‘村官要懂法,要學習《村民委員會自治法》,要知道自己的職責,要接受監督,要杜絕‘一窩挖錢。”交談中我們得知,由于工作成績突出,他被評為省先進文明個人、縣勞模。長安區還獎勵他一輛馬自達車。
另一個長里村,是一個典型的“城中村”。一切都顯示著長里尚留的鄉土氣息。
我們到達村主任家時,他像其他村民一樣,正忙著為自家的網吧更換電腦。對我們的調研,他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和耐心。在3個多小時的交談里,我們了解到他的“村官”經歷:被村里人從西安城里叫回,放棄自己經營紅火的餐館;競選村長,打理村內大小事務……
當談到長里的未來,他有些激動和些許擔憂。他的激動與擔憂來自四周熱火朝天的房地產業對長里的影響。自房地產業進軍長安以來,憑借地理位置的得天獨厚,長里和其他村一起卷入征地談判中。最初、簡單的想法是種地不掙錢,各種沓雜多,不如放棄土地,現賺現用。現在仔細琢磨,他認為,就長里這個特定的土地范圍,轟轟烈烈的房地產征地固然使農民的收入在短期內得以提高,但是于農民今后的生存及發展而言不是一個長期行為。如果把地賣完,按目前不盡合理的土地征用環節和價格設定,加之后續的社會保障和就業問題如果跟不上,那么對農民而言無異于“釜底抽薪”。所以對本村未被征用的土地,他想留著,盡最大的努力為本村村民謀利,因為畢竟不是每一個農民都具有從商的意識,和現代化社會要求的勞動技能。令他苦惱的是,村委會一班人的想法不僅得不到村民的理解,更受到包括親屬、族人在內的埋怨。
我們探尋老邢理想的長里該怎樣,他提出“是不是應該建長里自己的企業,安置無地勞力,由政府選派優秀人才,滲透先進的文化因素,帶來科學的企業管理模式?”
實地調研即將告一段落。夏夜,鋪開紙卷,落筆的思緒總被一個村落和一個人打斷,讓我們重新審視調研思路。村子叫祥峪溝,因夾在山谷中而得名。遠遠望去,半山坡上整齊劃一的紅瓦白墻,在青山映襯下,被一條清溪豁然剖開,遙相對峙。可我們調研決意要見的人,祥峪溝村黨支部書記老徐,卻未曾謀面。陪同我們的是祥峪溝30出頭、身形削瘦的村委會副主任小徐,隨和的性情、穩重的談吐顯示他少年老成、心存高遠。指點著村民漂亮的2層小樓,和戶戶門前依岸搭建、供游人歇息的涼棚桌椅,他侃侃談起祥峪溝怎樣由過去的窮鄉僻壤變為如今的旅游盛地。
言談話語中,由然流露著對前輩老徐書記的敬佩,但也透露出對徐書記個人生活的期望。小徐說,徐書記是全省唯一一位來自農村基層組織的省人大代表,為祥峪的未來和發展殫盡竭力、奔波不停,祥峪面貌改觀了,戶戶住上了小洋樓,可他因忙于公務,自家至今仍借住在村委會的破房里,全年的工資也只有200元左右。“村官”們反映,他們的工資主要源于“三提留五統籌”,而工資數額,在長安區大村(指2000人以上的村子)基本在260元左右,而小村,較之大村則有百元的差距。“村官”們毫不隱諱工資待遇對工作積極性的負面影響。改善工資待遇,是他們企盼已久的事。
穿梭于選點村落的街頭巷尾,零距離接近“村官”,他們舉手投足間散發的銳氣改變了我們以往觀察“村官”的視角。這些“村官”,膚色黝黑不光亮,衣著隨意欠光鮮,他們土生土長,鄉音厚重,但他們曾走出黃土地,吮吸過域外之風,當兵做生意、打工跑運輸的不凡經歷,造就他們睿智果敢、厲行干練,也加深他們固有的圓滑刁蠻。對“村官”顯露的傳統和現代性格元素,村民常冠以“能人”稱謂。豪氣與霸氣、果敢與獨裁、堅守與僭越,各種力量在他們的意識和行為中此消彼長。所以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有他們帶領村民致富路奔忙的身影,而回望高墻鐵窗,也有他們扶欄鐵窗懊喪的面容。
與個人性格元素共同影響農村社會生活、左右“村官”走向的因素,還來自千百年來在農村積淀的宗族血緣。在長安區,無論是我們經過的村莊,還是未踏足的堡子,“血濃于水”這句古訓痕跡猶存。追溯長安歷史,面對族親宗親糾集的人情現實,“村官”們坦言:“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所謂“成敗”,一桶油,兩盅酒,幾句家常話,凝合族人情感,促成競選“村官”的愿望,而若人少勢寡,縱使你有天大能耐,也無法與大族旺戶相抗衡;所謂“成敗”,能使你在工作中一呼有百應,也可使你取財于不義,身陷囹圄……對于農村人情世故,我們無“村官”切膚的體驗,但通過“村官”的傳遞,無疑說明:傳統宗族文化,超越農村原始的土地耕作和血脈流傳的需要,它的須根枝蔓依然頑固地伸延遍及農村社會生活方方面面。
離開鄉間時,文章初稿已在腹中醞釀成形,而心情卻處于不安和忐忑中。對于農村,但凡與其有千絲萬縷聯系的人,想必都飽含著一些感激、懷念的情感。而當祖先的血液在血脈里汨汨流淌,當我們抖掉落在祖先身上的黃土、泥沙,拋卻先人執過的镢頭、鐮刀,融入現代化都市,成為“城里人”后,我們是否踐行過對父老鄉親曾經的許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