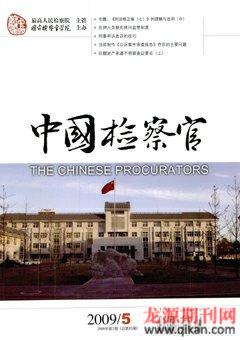索賄后瀆職之行為定性
吳培淵 雷 池
基本案情
被告人馬某某,原某市區稅務稽查大隊稽查員。
2007年10月9日,該區稅務稽查大隊稽查員馬某某、趙某某查獲內銷進口建材不入賬的四本自制收據,計35.6萬余元。據此,馬某某于10月28日制作了簽報,作出了補交稅款、滯納金及罰款共計23.7萬元的處理,至同年11月21日上述稅款收繳入庫完畢。11月26日,區稅務案件偵查室又將該室收到的該建筑公司偷逃稅的舉報材料移送至稽查大隊,該材料再次轉入馬某某手中。馬某某發現該建筑公司偷逃稅問題十分嚴重,其既不向領導匯報,又不進行查處,而于當晚私自打電話與建筑公司會計金某某聯系,以舉報材料中反映的問題相要脅,向其索要20萬元人民幣,并許諾滿足其要求后對舉報材料反映的問題不予查處。2007年12月被告人馬某某將建筑公司開具的16.34萬元轉賬支票打入其個人的物資公司的賬戶上。由于馬某某隱藏了該公司偷逃國稅的舉報材料,對該公司偷逃國稅的行為不予查處,致使不征應征稅款人民幣37萬余元。
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馬某某為達到受賄目的,屬于目的行為和手段行為的牽連,按照對牽連犯的“擇一重罪”處斷的原則,應以受賄罪從重處罰。
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馬某某的行為應認定為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刑法》第401條中的“徇私”,已包含貪贓受賄的內容,受賄應作為徇私的情節,在量刑時從重處罰。
第三種意見認為,被告人馬某某的行為同時符合受賄罪與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的犯罪構成,應認定同時構成這兩罪,實行兩罪數罪并罰。
評析意見
關于受賄后為他人謀取利益而瀆職的應如何處理,刑法學界存在四種觀點:(1)牽連犯論。有學者主張對于牽連犯,法律有規定的,依照法律規定;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依照牽連犯的理論,從一重罪處罰。(2)想象競合犯論,即謀利行為和受財行為共同結合為一個受賄行為,如果其中的謀利行為觸犯了其他罪名,屬于一個行為觸犯數個罪名的情況,構成想像競合犯,應擇一重罪處罰。(3)法條競合論,即國家工作人員在受賄的過程中,其謀利行為又構成其他犯罪,對這種情況應從一重罪處罰。(4)認為受賄后瀆職的行為,不是刑法上的牽連犯、想象競合犯,或者說存在法條競合的任何一種情形。持該觀點的論者認為,這一行為同時符合受賄罪和瀆職犯罪的犯罪構成,應當認定為受賄罪和瀆職犯罪,實行數罪并罰。
我們認為,根據《最高法院關于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因挪用公款索取、收受賄賂構成犯罪的,依照數罪并罰的規定處罰”、“挪用公款進行犯罪活動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數罪并罰處理”的規定精神,鑒于我國歷來對貪污賄賂嚴厲打擊的立場,對于此類受賄后而瀆職犯罪的案件,如果沒有法律的特別規定(《刑法》第399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貪贓枉法,同時又構成受賄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我們認為應按照從重處理的精神,對該種情形以數罪并罰來處理,是較為妥當的。本案中,馬某某身為國家工作人員,索賄后瀆職,應以受賄罪和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實行兩罪數罪并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