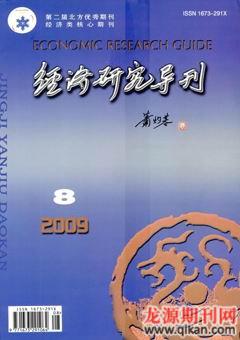試論締約過失責任在合同有效條件下的適用
白化秋
摘要:合同有效條件下的締約過失責任于1896年德國學者萊昂哈德提出后,對世界各國立法及學說均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締約過失責任作為誠信原則權威性、有效性的體現(xiàn),應適用于整個合同領域,作為一般性責任原則存在,而不應僅作為特例存在。這樣更有利于全面保護締約當事人的利益,更好適應時代變化發(fā)展要求。
關鍵詞:締約過失責任;合同有效;一般適用
中圖分類號:D923.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8-0177-03
締約上過失責任自羅馬法開始,即為立法及學說上討論的重要問題。但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系統(tǒng)、深刻和周密的分析始自1861年德國法學家耶林在其所主編的《耶林法學年報》第四卷上發(fā)表的《締約上過失,契約無效與不成立時之損害賠償》。耶林在該文中精辟地指出:“從事契約締結(jié)的人,是從契約外的消極義務范疇,進入契約上的積極義務范疇,其因此而承擔的首要義務,系于締約時須善盡必要的注意。法律所保護的并非僅是一個業(yè)已存在的契約關系,正在發(fā)生中的契約關系也應包括在內(nèi),否則,契約交易將暴露在外,不受保護,締約一方當事人不免成為他方疏忽和不注意的犧牲品。契約的締結(jié)產(chǎn)生了一種履行義務,若此種效力因法律上的障礙而被排除時,則會產(chǎn)生一種損害賠償義務。因此,所謂締約無效者,僅指不發(fā)生履行效力,非謂不發(fā)生任何效力。簡言之,當事人因自己過失致使契約不成立者,對信其契約有效成立的相對人,應賠償基于此項信賴而生的賠償。”[1]由此可見,其所提出的締約過失責任僅存于合同成立前階段。我國理論界目前對締約過失責任適用條件的主張已經(jīng)擴大到合同有效之場合,但對締約過失責任在合同有效場合的適用是作為特殊適用還是作為一般性責任原則適用尚有爭議。筆者從法理的角度認為,締約過失責任作為誠實信用原則權威性、有效性的體現(xiàn),在整個合同締結(jié)、履行過程中,都有它存在的價值和法理學基礎,故其應作為一般性責任原則適用于整個合同領域。
一、誠實信用原則作為締約過失責任的正當性基礎,為締約過失責任作為一般性責任原則在整個合同領域適用提供了法理學基礎
誠實信用原則源于羅馬法,在羅馬法上,誠實信用原則觀念表現(xiàn)在一般的惡意抗辯中。其被稱為系屬帝王條款,君臨法域之基本原則,是現(xiàn)代民法的最高指導原則,學者稱之為“帝王條款”。近代以來,各國民法典基本上均規(guī)定了這一原則,也是合同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它作為有實際約束力及效果的原則,適用于整個合同領域。締約過失責任是指當事人在訂立合同過程中,因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給對方造成損失所應承擔的損害賠償責任[2]。締約過失責任作為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責任,理應作為一般性的責任原則存在于整個合同領域。否則,拒絕締約過失責任的有效合同如同沒有窗戶的屋子,必然成為黑暗的盡情之處。實踐上的合同關系具有多樣性、復雜性、發(fā)展性,而人的理性是有邊界的,如果試圖用事先的契約規(guī)定合同當事人將來所有合同權利義務的想法,是不科學的,事實上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就如同法理上眾所周知的成文法具有極強的穩(wěn)定性及某種程度的滯后性、保守性的特點一樣,總是在流變、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的社會生活面前處于捉襟見肘的窘境。因此,承認締約過失責任應作為一般性責任原則適用于整個合同領域是必要的,也是有著深厚的法理學基礎的。
二、從合同義務的視角,在合同有效場合應有締約過失責任適用的空間
締約過失責任是違反先契約義務,造成相對方信賴利益損失的結(jié)果,而先契約義務是基于誠實信用原則產(chǎn)生的。締約過失責任所保護的信賴利益,是誠實信用原則所要求的尊重他人利益、以對待自己事務的注意對待他人事務、恪守良性交易行為準則、不得損人利己的必然結(jié)果。在民法理論中,義務與責任是相對應的概念。義務是責任的前提,有義務才有責任。而契約過失責任對應的即是先合同義務,這是締約過失責任與違約責任、侵權責任的主要區(qū)別所在。所以,違反先合同義務是締約過失責任的內(nèi)在核心。所謂先合同義務,是指締約人為簽訂合同,在相互磋商過程中依誠實信用原則和一般交易慣例而逐漸產(chǎn)生的注意義務,它包括相互協(xié)議、互相保護、相互通知、相互保密等。締約人因故意或者過失違反先合同義務,給對方造成損失的,即應承擔締約過失責任。所以,判斷當事人是否應承擔締約過失責任,應以當事人是否故意或者過失違反了先合同義務為判斷標準,而與合同是否成立及其效力情況無關[3]。根據(jù)法理,締約人因過錯違反先合同義務的情況下,即使合同有效成立,仍應承擔締約過失責任。從另一角度看,合同債之關系,除給付義務及附隨義務外,尚有所謂的“不真正義務”(Obliegenheit,一譯間接義務)。不真正義務在保險法上最為常見,如投保人于保險標的的見險增加后的告知義務;不真正義務在民法上也有,典型的表現(xiàn)為減輕損害的義務(《民法通則》第114條;《合同法》第119條、370條)等[4]。違反合同給付義務當事人所承擔的責任是違約責任,而違反合同附隨義務及不真正義務是適用違約責任還是締約過失責任呢?筆者認為,由于合同附隨義務和不真正義務均以誠實信用原則為法理學基礎,且一般均沒有納入合同條款,故其內(nèi)容需以誠實信用原則進行確定。在這種情況下,附隨義務和不真正義務的確定不再取決于當事人之間的意思自治,而是來源于誠實信用原則,因此,違反附隨義務與不真正義務應當構成締約過失責任,而不屬于違約責任[5]。
三、一些國家和地區(qū)的立法例和司法實踐為締約過失責任適用于合同有效之場合提供了先例
關于合同有效場合之締約過失問題,在學說上最早是由德國學者萊昂哈德于1896年提出,1912年4月26日被德國法院判決采納,此后,肯定合同有效締結(jié)場合的締約上過失一直成為通說見解。
從司法實踐看,德國的判例與學說將締約過失責任發(fā)展為“不僅適用于合同不成立、無效或被撤銷領域,而且還適用于某些有效成立的場合。例如,賣方在合同締結(jié)前的說明未涉及標的物的特質(zhì)或瑕疵時,可承認擔保責任與締約上過失責任的競合;在具有專門知識的賣方與無經(jīng)驗的買方的合同中,即使賣方對標的物品質(zhì)的說明與瑕疵并無關聯(lián),也可成立締約上過失責任。”[6]例如,在德國有這樣一個典型案例:一個私人工程公司與一個市立公司就在街道地下鋪設排水管工程簽訂了合同,合同的內(nèi)容之一就是把排水管埋設在一定深度的地下水水平線以上,為了使私人工程公司估算工程的報酬、費用,市立公司在違約之際提供了設計圖紙,隨著工作的進展,私人公司發(fā)現(xiàn)市立公司提供的圖紙有錯誤,私人公司不得不規(guī)避錯誤,做了正確的工作,但結(jié)果超出了其預算估價。法院認為,因雇主過失錯誤陳述,相對人可撤銷該合同,但因為該案私人公司沒有選擇這種撤銷權予以救濟,而是善意的修正后履行了合同,此合同有效,對于私人公司所受的信賴利益損失,于締約階段存在過錯的市立公司應負締約過失責任,賠償其多支出費用之損失。在德國,賣方在合同締結(jié)前的說明未涉及標的物的特質(zhì)或瑕疵時,可承認擔保責任與締約上過失責任的競合;在具有專門知識的賣方與無經(jīng)驗的買方之間的合同中,即使賣方對標的物品質(zhì)的生命與瑕疵并無關聯(lián),也可成立締約上過失責任[7]。但后來隨著德國民法典債務法的修改,情況有所變化,即對于賣主于締約交涉之際對標的物的性質(zhì)未作必要說明,且有應可歸責事由的場合,以及收買企業(yè)時賣主關于純收益做了錯誤的報告,判例對此否定瑕疵擔保請求權,而一般有相當長時效期間的契約締結(jié)上過失的請求權,對買主予以救濟[8]。日本的判例與學說也認為,締約過失責任可以適用于標的物有瑕疵和締約人違反保證但合同仍有效的場合[9]。在我國臺灣地區(qū),締約過失責任適用類型有:(1)合同不成立;(2)合同無效;(3)締約之際未盡通知等義務致使他方遭受財產(chǎn)損失;(4)締約之際,未盡保護義務致他方身體、健康受損失。顯然,后兩種類型并不排除在合同有效成立的情況下適用締約過失責任制度的可能。
從立法例看,一般只是規(guī)定締約過失責任的成立要件為當事人在締約過程中因過錯行為違反先合同義務且造成對方損害,并不以合同是否有效成立為成立要件。例如,《希臘民法典》第197條規(guī)定:“從事締結(jié)契約磋商行為之際,當事人應負遵循誠實信用及交易慣例所要求的行為義務。”第198條規(guī)定:“于為締結(jié)契約磋商行為之際,因過失致相對人遭受損害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即使契約未成立亦然。”此規(guī)定隱含了締約之際因過失致相對方損害,即使契約已成立,亦應負締約過失責任。又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440條規(guī)定:“如果詐欺不是能夠?qū)е聬阂庑纬傻脑p欺,則盡管沒有詐欺該契約會根據(jù)不同的條件締結(jié),但是契約有效;不過,惡意締約人要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可見,在意大利民法中,締約過失責任可以存在于合同有效的情況。再如《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第三章“合同的效力”中第3.18條規(guī)定:“無論是否宣告合同無效,知道或理應知道宣告無效理由的一方當事人應承擔損害賠償?shù)呢熑危允蛊鋵Ψ疆斒氯嘶貜偷轿丛喠⒑贤瑫r的相同地位。”此規(guī)定實際上確認了當事人承擔締約過失責任并不以合同是否有效為依據(jù)。
四、我國目前的法律規(guī)定為締約過失責任適用于合同有效之場合提供了空間
從我國目前的法律規(guī)定看,在合同有效成立情況下適用締約過失責任制度的結(jié)論實際上也包含在對《合同法》第42條、第43條的合理解釋范圍之內(nèi)。
合同法第42條規(guī)定:“當事人在訂立合同過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一)假借訂立合同,惡意進行磋商;(二)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者提供虛假情報情況;(三)有其他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
該條第1項規(guī)定,一般認為是締約過失責任適用于合同未成立的情況。因非本文論述內(nèi)容,故在此不加以論證。
該條第2項規(guī)定的情況,實質(zhì)構成民事欺詐。如果因受民事欺詐而簽訂合同,受欺詐的一方可依據(jù)《合同法》第54條的規(guī)定,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合同被撤銷后,受欺詐方有損失的可依《合同法》第58條之規(guī)定請求賠償。對于合同被變更后的法律責任,我國《合同法》未作明確規(guī)定。筆者認為,因可被撤銷或變更的合同,其原因均為當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實,所以對于合同被變更后的法律責任,可適用于合同被撤銷相同的法律規(guī)定。依據(jù)《合同法》第54條的規(guī)定,受欺詐訂立的未損害國家利益的合同,并不當然無效,其效力決定于撤銷權的是否行使,而是否行使撤銷權乃由受損害締約人自己決定。對于因受欺詐訂立的合同,受損害締約人未行使撤銷權的,該合同有效。此時,受欺詐的締約人受損害的,是否可依《合同法》第42條第2項規(guī)定獲得賠償?欺詐人承擔責任的性質(zhì)是什么?筆者認為,在締約過程中,以締約人是否已訂立合同為標準,按欺詐人欺詐行為造成的損害所發(fā)生的階段,可將損害區(qū)分為締約人尚未訂立合同時已發(fā)生的損害和締約人已經(jīng)訂立合同后發(fā)生的損害。據(jù)此,筆者認為,《合同法》第42條第2項規(guī)定的損害賠償應包括兩種情形:一是欺詐行為成立于締約階段,受欺詐的損害結(jié)果發(fā)生在合同訂立之前的損害賠償,屬于合同不成立時締約過失責任的一種;二是欺詐行為成立于締約階段,受欺詐的損害結(jié)果發(fā)生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的損害賠償。在這種情況下,情報提供義務的確定不再取決于當事人之間的意思自治,而是來源于誠實信用原則,因此,違反情報提供義務應當構成締約過失責任,而不屬于違約責任或侵權責任。需要指出的是,非欺詐而因過失違反情報提供義務,在無過錯方所受損害發(fā)生于合同成立前,并且最終沒有成功締約時,可構成合同未成立時的締約過失責任;而在無過錯方所受損害發(fā)生于合同有效成立后,也可構成合同有效時的締約過失責任。
該條第3項規(guī)定表明,該條規(guī)定的理論依據(jù)即為誠實信用原則。其內(nèi)容包括因顯示公平或重大誤解等違反誠實信用原則而導致合同被撤銷或變更的情況。當然也涉及到因撤銷權消滅或可撤銷合同被變更而導致合同有效情況下締約過失責任的承擔問題。因筆者在對該條第2項進行法理分析時已涉及這方面內(nèi)容,故在此不再進行論證。筆者主張,締約人在訂立合同過程中,因違反誠實信用原則而給相對方造成損失的,如該損失發(fā)生于合同有效成立后,可構成合同有效時的締約過失責任。
由以上論證可以看出,《合同法》第42條的規(guī)定實際暗含著只要締約人在訂立合同過程中存在締約過失行為,且給對方造成了損害無論合同效力如何,均應承擔締約過失責任的含義。
《合同法》第43條規(guī)定:“當事人在訂立合同過程中知悉的商業(yè)秘密,無論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當使用。泄露或者不正當使用該商業(yè)秘密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此規(guī)定實際上也說明,即使在合同成立生效后,只要締約人存在違反保密義務并給對方造成損失的行為,即可適用締約過失責任。
五、合同有效之場合信賴利益賠償范圍的確定
關于締約過失責任中信賴利益賠償范圍問題是爭議較大的,目前存在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信賴利益損失,是指締約當事人因信賴法律行為的成立和有效,但由于該法律行為的不成立或無效所蒙受的損失[10],締約過失責任中的信賴利益損失只存在于合同不成立、被撤銷或者無效的情況下;另一種觀點認為,因締約一方過失致使相對方額外增加了交易費用和成本,即使合同有效成立,對于這些本不需要支付的額外增加的費用和成本仍可請求信賴利益的賠償。
筆者認為,信賴利益中的信賴,應當是對締約相對人締約行為的信賴,而非對合同的信賴,合同的生效成立只是被信賴的締約行為的結(jié)果,而不應作為確定信賴利益的前提。因此,將信賴利益損失限定于合同不成立、被撤銷或者無效是不全面的。在其他情況下,如在合同有效成立的情況下亦存在適用締約過失責任的可能。雖然在一般情況下,合同有效成立后,信賴利益會從合同的履行中得到補償,因此,不產(chǎn)生信賴利益的賠償。但在某些情況下,因締約人違反先合同義務,如應告知而未告知,應說明而未說明,致使相對方額外增加了交易費用和成本,即使合同有效成立,對于這些本不需要支付的額外增加的費用和成本仍可請求信賴利益的賠償。
因此,筆者認為,在合同有效成立的情況下,仍然可以存在信賴利益的損害賠償。此時,信賴利益不僅包括各種正常締約費用,而且包括締約人因信賴而額外支出的交易費用。
參考文獻:
[1]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1)[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88-89.
[2]孔祥俊.合同法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9:136.
[3]北京朝陽區(qū)人民法院民一庭.論合同有效成立情況下的締約過失責任.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43.
[4]韓世遠.合同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92.
[5]康曉磊,陳洲.締約過失責任在合同有效條件適用的法理探析[J].遼寧行政學院學報,2008,(5).
[6]劉莉萍,吳智峰.淺談合同有效場合之締約過失責任[J].福建商業(yè)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4).
[7]崔建遠.締約上過失責任論[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2,(3).
[8]梁慧星譯.德國民法典債務法的修改[J].外國法評譯,1993,(1).
[9][日]本田純一.關于契約締結(jié)上的過失[J].現(xiàn)代契約法大系(1).有斐閣,第193頁/轉(zhuǎn)引自崔建遠《締約上過失責任論》.
[10]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5)[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