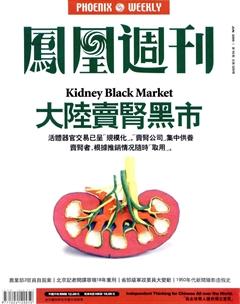中國的傳統與再生
維舟
《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美]列文森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在世界各國步入現代的進程中,中國的儒家文明是各主要文明中唯一一個遭到滅絕命運的。與伊斯蘭教、基督教等不同,當代新儒家在生活中僅僅只以學術思想的形式存在,與生活不甚相干。這一事實的背后是中國人自近代以來極為深刻嚴重的思想危機:由于儒家思想一貫重視以普遍王權來整合維持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所以當中國傳統的政治體制崩壞之后,文化秩序也隨之瓦解。
兩百年前絕不會有中國人預想到這一結果,那時人們還沉醉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之中。當后人回顧這一歷史階段時,卻不禁要將之視為一個悲劇。自黑格爾提出中國是“沒有歷史”、處于長期停滯的帝國之后,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對這一理論的合唱中來。韋伯在比較研究諸文明之后,認為儒家和道家思想均不利于從內部自發演化出資本主義精神,這種精神唯有從基督教新教的倫理中才能誕生。這一有爭議的理論隨即深刻影響了許多學者——其中也包括本書作者列文森。
在近代深重的政治、文化雙重危機下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分子也認識到:現代化是一個必然且不可逆的歷史進程。但關于傳統怎樣向現代轉化,卻是一個有著極大爭論的龐大議題。隨之而來的是“精英的分裂”——一些人主張中國傳統與現代民主存在內在沖突,所以要全盤西化;另一些人則不承認西方的入侵為中國帶來了資本主義,認為中國原本也能內在產生現代化,卻被西方的入侵扼殺和摧折了,這就是所謂“明清資本主義萌芽說”。這兩派的觀點都有偏頗,但主要的核心則是一樣的即中國能否自發實現現代化?列文森的答案是否定的,而且答得相當決絕。
列文森從思想史的角度進行論述,在他看來,中國傳統社會的思想脈絡決定了其自身的歷史走向。在他的術語中,“歷史”是一個特定概念,相當于“發展”,涉及傳統向現代的轉變。無疑,這是一種線性進化論的歷史觀。由此他區分了兩種變化:傳統社會內部的變化,及傳統到現代之間的變化,而只有第二種才有歷史意義,因為在他看來第一種實際上是停滯而無發展的“高水平均衡”狀態。這方面他列舉了一系列例證,如中國傳統上科學不具有社會聲望,官僚沒有專業化等,以此證明中國自身很難孕育出科學精神等現代價值。
中西文明有著極大的內在異質性,因此當這種轉化在巨大的壓力下驟然降臨時,中國的知識分子面臨著精神上的嚴重困境和內在沖突。他們最初提出的主張是“中體西用”,試圖在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前提下利用西方思想。列文森雖然對此抱有同情,但他也以一種無情的冷靜洞察指出:“西學越是作為生活和權力的實際工具被接受,儒學便越是失去其‘體的地位。”越到后來,這一點越發明顯,原本是為了強固民族文化生命而吸收西學,到后來卻變成為了吸收西學和實現現代化,必須揚棄傳統。
這種異化帶來中國20世紀思想界的極大混亂和一系列矛盾行為。許多人一面激烈反傳統,一面又抱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自尊心,以至于形成一種列文森所說的“躁動不安的”民族主義。在這一進程中,中國傳統實際上被客體化對待了,成了博物館里的陳列,這些價值雖然仍有人聲稱珍視之,卻并非深感其價值和理念仍有效用,只是引為它們能加強民族尊嚴。換言之,他們僅僅是在利用,而不是實踐著中國傳統文化。
的確,在中國當代思想中儒家思想已經只是“游魂”(余英時語),現實中無可附麗。列文森在四五十年前寫作本書時雖然無從預見這些年中國傳統文化和國學的大量回潮,但他尖刻直率的洞察倒也恰能刺穿這一現象的膚淺:“這些碎片所以能保存下來,是因為他們能夠滿足現代人的愛好,而不是由于他們包含有某種無與倫比的傳統的精粹。”
但是,中國的復興還剛剛開始,我們也許不必那么早下斷言。說真的,在一兩百年前,有幾個人會想到日本競能成為唯一一個實現現代化的非西方國家?又有誰規定現代化只能有一條道路呢?在這一點上,我們應保持更為開放的心態。而歷史也確實正在以中國的復興來為世界提供又一個新的現代化發展模式,這是我們當代人比列文森幸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