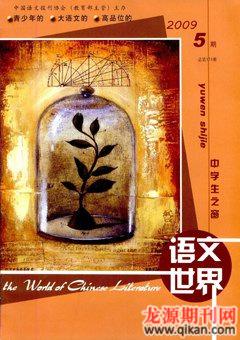獲首屆中國當代女性文學創作獎的作家:陳染
張榮民
作家檔案
陳染,1962生于北京。幼年學習音樂,18歲興趣轉向文學。1986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學士。曾在北京做過四年半的大學中文系教師,后調入中國作協作家出版社做編輯。曾在澳洲墨爾本的英國倫敦大學、愛丁堡大學等旅居生活和講學。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發表詩、散文,以小說《世紀病》在文壇脫穎而出,被視為“純文學”“先鋒小說”嚴肅文學女作家中的最新代表。重要作品集中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代表作《與往事干杯》《無處告別》《私人生活》等。她以強烈的女性意識,不懈的探索精神,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位獨特而重要的女性作家代表。曾獲首屆中國當代女性文學創作獎等。她的小說在英、美、德、日等國家以及港臺地區均有出版和評介。根據她的小說《與往事干杯》改編的同名電影,被選為國際婦女大會參展電影。
作品選讀
城市的棄兒
陳 染
不知不覺又是夏天了。仿佛是柔和晴朗的細風忽然之間把全身的血脈吹拂開來。我是在傍晚的斜陽之下,一低頭,猛然間發見胳臂上眾多的藍色的血管,如同一條條歡暢的小河,清晰地凸起,蜿蜒在皮膚上。
夏天的傍晚總是令我愜意,在屋里關閉了一整天的我,每每這個時辰會悠閑地走到布滿綠陰的街道上。我一會兒望望涌動的車流,一會兒又望望歸家心切的人們在貨攤上的討價還價。我的腳步在夕陽照耀下瞬息萬變的光影中漫無目的地移動。
一只貓忽然擋住了我的去路。這是一只骨瘦如柴的流浪貓,它揚起臟臟的小臉用力沖我叫。我站住,環顧四周,發現這里有個小自行車鋪,過來往去的人們司空見慣地從它身旁走過,沒人駐足。而這只貓似乎從眾多的人流里單單抓住了我,沖我乞求地叫個不停。
我覺得它一定是渴了,在要水喝。于是,我在路邊的冷飲店給它買了一瓶礦泉水,又頗費周折地尋來一只盒子當容器,給它倒了一盒水。貓咪俯身輕描淡寫地喝了幾口水,又抬起頭沖著我叫。我又想它可能是餓了,就飛快跑到馬路對面一個小食品店買來肉腸,用手掰碎放在盒子里,它埋頭吃著,吃得如同一只小推土機,風卷殘云。我在一旁靜靜地看著它,直到它吃飽了,才站起身。然后,我對它說了幾句告別的話,轉身欲離開。可是,它立刻跟上來,依然沖著我叫。
一個溜狗的婦女牽著她家的愛犬繞著貓咪走開了,那只狗狗皮毛光潔閃亮,神態倨傲,胖胖的腰身幸福地扭動。
我再一次俯下身,心疼地看著這只又臟又瘦干柴一般的貓咪。我知道,它對我最后的乞求是:要我帶它回家!
可是……
我狠了狠心,轉身走開了。它跟了我幾步,堅持著表達它的愿望,我只得加快腳步。終于,貓咪失望地看著我的背影,慢慢停止了叫聲。直到另一個路人在它身邊停下腳步,貓咪又揚起它臟臟的小臉開始了新一輪乞求的叫聲。
我走出去很遠,回過頭來看它,心里有說不出的滋味……對不起,貓咪!非常對不起!我無法帶你回家!
天色慢慢暗淡下來,遠處的樓群已有零星的燈光爬上人家的窗戶,更遠處的天空居然浮現了多日不見的云朵。晚風依舊和煦舒朗,小路兩旁濃郁的綠葉依舊搖蕩出平靜的刷刷聲。可是,這聲音在我聽來仿佛一聲聲嘆息和啜泣,我出門時的好心情已經蕩然無存,完全湮沒在一種莫名的沉重當中。我情緒失落、憂心忡忡地走回家。
第二天黃昏時候,我又鬼使神差來到自行車鋪一帶。
我先是遠遠地看見車鋪外邊的幾輛自行車車縫間的水泥地上丟著一塊臟抹布,待走到近來,才看清那塊抹布就是昨天的貓咪,它酣酣地睡在不潔凈的洋灰地上,身子蜷成一團,癟癟的小肚皮一起一伏的。它身邊不遠處,有幾根干干的帶魚刺在地上丟著。
我心里又是欣慰,又是發堵。想起我家那備受寵愛的愛犬三三,經常吃得小肚子溜圓,舒展地睡在干凈柔軟的席子上,甚至我不得不經常給它乳酶生吃,幫助它消化,這時我忽然發現:
這個世界別說是人,就是動物也無法公平啊!
我沒有叫醒貓咪。只是厚著臉皮上前與車鋪的小老板搭訕,也忘記了應該先夸贊他家的自行車,就直奔主題說起這只貓咪。小老板看上去挺善良,熱情地與我搭話。他說,每天都給它剩飯剩菜吃,不然早就餓死了。說這只貓已經在這一帶很長時間了。我誠懇地謝了他,并請他每天一定給貓咪一些水喝,我說我會經常送一些貓糧過來。我們互相說了謝謝之后,我便趕快逃開了。
街上依舊車水馬龍、人流如梭。貓咪就在路旁鼎沸的噪聲中沉沉酣睡,熱風吹拂著它身上干枯的灰毛毛,如同一塊舞動的臟抹布,又仿佛是一撮灰土,瞬息之間就會隨風飄散,無影無蹤,被這個城市遺忘得一干二凈。
我不想等它醒來,讓它再一次看著我無能地丟下它落荒而逃。
流浪貓已經成為眾多城市的景觀。負責環保的人們,你們在忙碌大事情的間隙,可曾聽到那從城市的地角夾縫間升起的一縷縷微弱然而凄涼的叫聲?
折斷的時間
陳 染
早年,我曾在多處畫冊中看到過達利的《記憶的殘痕》這幅畫,畫面上是三只時間完全停滯的柔軟扭曲的鐘表。記得當時我每次看到這幅畫,內心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矛盾感,至于怎么個矛盾法,我一直沒來得及深思與沉淀,匆匆忙忙地就被新的事物所沖刷和覆蓋了,就像一朵浪花撞擊另一朵浪花,轉瞬之間便歸復于平靜,涌動的暗流便潛藏于深水之下。
據我對畫面的表層理解,我想,達利似乎在傾訴一種對“原始記憶”的閃現和拉回的渴望;倘若再往潛意識深處探尋的話,根據弗洛伊德主義的理論,手表或鐘表是一種規律和紀律的象征,那么也可理解為達利對現實秩序以及現實規則的一種破壞的欲求。
回憶起來,在我反復觀看現代派畫冊、畫展的那個時期,也正是我叛逆情緒最為飽滿的青春期。那個時候,我對現實說“不”,對約定俗成的觀念說“不”,對所有的束縛人精神的條條框框說“不”!按說,以我當時的心理狀態,對于達利的《記憶的殘痕》描繪出的彎折扭曲的鐘表所蘊含的精神指向,是不應該感到別扭的。但是,我就是有一股說不出的別扭。
隨著歲月的流逝,更隨著我對自己的本質的日漸清晰的理解,我恍然知道了這種內心的沖撞發生在哪里了——雖然,在思想觀念上,我始終是一個不喜歡墨守成規、人云亦云的逆向思維者;但是,在現實生活的具體常態下,我又是一個喜歡遵循秩序、規則和紀律的人,這種遵循甚而到達刻板的程度。比如,我喜歡恪守時間的朋友,并要求自己守約守時;我喜歡購物環境是明碼標價的場所,不喜歡那種誰有本事誰砍價的浮動價格的游戲規則;習慣日常起居的規律化,不習慣恣意妄為、任性散漫;喜歡社會各種秩序的規范化、法律化,不喜歡見人行事的隨意化、人制化……總之,我依賴于有“紀律”的日常狀態,而這種“紀律”完全來自于一種自我的意愿和自我的束約。
一方面,是喜歡思想意識上的不安分和自由感;另一方面,又傾向于在具體的日常生活上相對的秩序化和規范化。我想,現在回憶起來,早年達利那幅畫帶給我的內心沖突大致源于此吧。
其實,秩序和規則從來不是自由的對立面。所有的自由都是仰仗一定的制約而得以實現的。也可以說,沒有制約,根本就沒有自由!
美國有一位心理學家叫斯科特·派克,他曾說,“紀律是解決人生難題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有四點:不逞一時之強,承擔責任,忠于真相,保持平衡”。青春年少之時,不懂得節制的我們也許會對此嗤之以鼻;時過境遷,當我們擁有了足夠的歲月積淀之后,當鉛錠一般沉甸甸的思緒堆在心頭時,我們便恍然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力量。
超級鏈接
人民網與陳染關于文學的對話
人民網:《私人生活》一直被中國當代文學史譽為女性主義文學經典之作,它的廣泛影響和所引發的激烈爭議也使你成為“私人化寫作”的肇始者。到了今天,你怎么看?
陳染:《私人生活》是我青春期時候的小說,青春是激情的敏感的也是痛苦的,有太多的憂戚與深思。此書在香港、臺灣和美國出版后,也有很大反響。
人民網:你怎么看待時下所謂的美女作家這個稱呼和她們的寫作?
陳染:這個話題可以從兩方面說:第一,美女作家這個提法是上世紀90年代后期出現的,而我是80年代出道的作家,所以從輩分上講應該是“老前輩”大姐了,和她們的寫作姿態也完全不同,真正文學界的作家、批評家們以及負責任的媒體記者,沒有人把我納入美女作家的行列。一些不大清楚文學發展脈絡的媒體有時候為了炒作新聞,對稍有點姿色的女性作家統統推入“美女作家”行列,對大眾造成了一些誤導。第二,美女作家從事的是時尚類寫作,而我對時尚一直是心懷警惕的人,時尚中有優秀的東西,也有糟粕的東西,良莠不齊。總之“美女作家”是新生事物,是我從事寫作十余年后出現的,我不在這個群落中。而且,我一直覺得,是否漂亮與寫作無關,請媒體不要再誤導。
人民網:你覺得文學創作給你帶來最大的收獲是什么?是財富、名聲還是其他的什么?
陳染:首先是我內心的一種喜愛,一種滿足。當然,它也會帶來一些財富。我覺得我現在過著一種感恩的生活,我希望人們不要在生活中總是懷揣著刻薄、仇恨、敵意等心理。“感恩的生活”不是膚淺怠惰,不是廉價的知足常樂,而是一種大氣的從容的深刻的感情。
人民網:你怎么評價文學界的浮躁?你怎么看待各種文學獎?
陳染:文學界的確存在浮躁。但現在胡亂寫書的并不見得是真正的作家。我不大介入文學界和文學以外的是非問題。關于各種文學獎我一直不想說什么,因為也許有的好作品歪打正著被評上獎了,不好亂說。但是現在的國內評獎內幕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不必看得過重。我最近看到李國文先生的一篇文章,其中談到要想獲獎你得付出的各種獎級的(銀子)價位,我覺得李國文前輩真是太幽默了。評獎問題我覺得有三點:一是主旋律作品,二是評委的文學價值取向和審美尺度,三是(也許還有)參獎者的十八門武藝,這幾乎是最重要的,中國是一個“關系學”大國,全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的關系學如中國這樣普及和發達。人家也很不容易啊,我心里很平衡。
人民網:與鐵凝相比,你似乎是游離于體制之外,這對你的生活與寫作有何影響,或者這僅是你的某種生活選擇?
陳染:有不少作家都有官職,比如王蒙,他曾經出任中國文化部部長,女作家當中比如鐵凝、舒婷、方方等等也都擔任某些官職,這些作家都是我喜歡的朋友,他們說的都是“人話”,具有深厚的人文關懷。我的情況是,我對人群有恐懼感,不太會交際,總有一種逃避感,這其實不是什么選擇,是我的性格弱點使然吧。
人民網:最近在寫作什么?
陳染:寫得很少,總想尋找一個新的突破口,這很難。現在,寫一些短篇小說和散文。我感覺,歲數越大,想說的話越少,經常是想一想之后,覺得不說(寫)也罷,算了。也許是我提前“老了”,越來越理解張愛玲晚年只字不寫、閉門索居。宏觀上我對自己的未來是悲觀的。雖然理論上講,今天活著,還是笑著活是比較聰明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