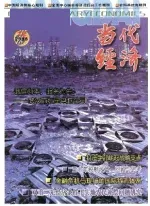歐元危機的成因分析及其影響
○徐杰華 (安陽工學院 河南 安陽 455000)
一、引言
隨著全球三大評級公司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于2009年10月、2010年4月、2010年7月陸續調降歐元區國家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和意大利的主權債務評級,促使其主權債務融資環境日趨惡化,導致市場對歐元前景看空,歐元兌美元匯率已經從去年底的1.4324,于2010年5月貶值到了1.2570,貶值幅度達到12%,更在6月3日的紐約盤中觸及四年新低1.2111,可見歐元危機愈演愈烈,充分印證了歐洲經濟和政策面臨的嚴峻局勢。
根據歐盟統計局2010年5月2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歐元區16國和歐盟27國政府2009年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分別達到6.3%和6.8%,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分別達到78.7%和73.6%,遠遠超出1992年簽署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的3%和60%的底線要求。可見,歐洲主權信用危機的實質,是西方發達國家面臨的龐大債務危機。
二、歐元危機成因分析
瑞士信貸董事總經理、亞洲區首席經濟分析師陶冬(2009年3月23日)指出,金融危機放大了歐元依托的結構和財政狀況存在不穩定性的缺點,加上歐盟在東歐的成員及歐洲銀行面臨的高風險和歐洲實體經濟的惡化,歐元前景不容樂觀。
1、迪拜危機
希臘危機是歐元危機爆發的導火索,其爆發與迪拜危機有著密切的聯系。迪拜財政部2009年11月25日突然宣布,由政府持有的迪拜世界公司及旗下的房地產分支棕櫚島集團將推遲償付590億美元的債務最少六個月,以便進行債務重組。棕櫚島集團的35億美元債務也延期償付。11月25日至27日,穆迪投資和標準普爾則都大幅下調了眾多迪拜政府相關實體的債務評級,市場及媒體導向都將迪拜危機指向歐洲金融機構,皆因其逾一半債權由歐洲銀行持有(部分債權人名單見表1)。隨后,12月16日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將希臘的長期主權信貸評級下調一檔,這已是繼12月8日惠譽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將希臘主權信用評級由“A-”降至“BBB+”后的第二次信貸評級下調,一周內兩次遭到“降級”,讓全球投資人對于主權債務危機的擔憂再度升溫,導致市場恐慌加劇,歐美股市全線大跌1%以上。

表1 迪拜債權人機構部分名單(歐洲)
2、美元與歐元的博弈
自歐元問世以來,國際儲備貨幣的競爭格局發生了變化:一方面全球歐元儲備規模持續擴張,據IMF的“全球官方儲備貨幣構成統計”數據顯示,歐元問世的第一年即1999年,全球歐元儲備總規模為2469.50億美元,2003年末達到5592.46億美元,2007年末達到10822.76億美元,2009年為12499.54億美元,以1999年末的全球歐元儲備作基數,2000—2009年,全球歐元儲備增長了4.96倍;另一方面美元的國際地位相對下降,歐元成為美元最主要的競爭對手,1999—2009年,全球外匯儲備中美元份額由71.01%下降到62.14%,下降了8.87個百分點;英鎊、日元等其他貨幣所占份額基本沒有變化,而歐元的份額由17.90%上升到27.37%,提高了9.47個百分點。也就是說,美元失去的份額全部流入了歐元。此外,2009年,在歐元兌美元1∶1.43時,歐元區創造的GDP高達一年13.72萬億美元,僅次于美國的14.85萬億美元。
從利益的角度來分析,美元與歐元是不共戴天的,歐元打破了美元的壟斷地位,分享原被美元獨享的一系列好處,比如鑄幣稅收入等。因此美元開始全面沽空歐元,首當其沖是對沖基金輪番做空歐元,其次是投資銀行的雙重角色,從“希臘政府債務危機”的遮掩者,搖身一變成沽空歐元的助推者。如高盛、美銀美林及巴克萊銀行等大型投行已推出一種更激進的“沽空歐元型”結構型金融衍生工具,造成歐元匯率大幅下跌。
3、制度缺陷
體制問題是誘發主權債務危機,乃至蔓延為歐洲債務危機的重要原因。首先,歐元區的主要問題在于貨幣政策的統一與財政政策的分割之間的矛盾,即歐元區只統一了貨幣政策,卻沒有統一財政政策。這一體制缺乏對區內成員的財政監督和干預。其次,由于歐元區沒有統一的“財政部”,當區內某一成員發生債務危機時,它只能用本國的財政作擔保,勢單力薄,再加上歐盟條約和歐洲央行的“不救助”條款,基本上處于孤立無援的狀態,因此很容易受到投機者的攻擊,成為打壓歐元的突破口。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充分暴露歐元機制的這一漏洞:歐元區各國忙于救助各自的金融系統,但在歐洲央行“一刀切”貨幣政策下,希臘等承受債務重壓者喪失本幣貶值的危機救助手段。
索羅斯在英國《金融時報》也發表文章稱,即使歐元區借助某種權宜之計暫時克服希臘債務危機,歐元設計存在的機制性缺陷今后將使歐元面臨更大難題。他認為,任何一種成熟貨幣均需中央銀行和財政部“護航”。當金融危機襲來時,央行能提供流動性,而財政部能處理債務。由16國組成的歐元區只是一種貨幣聯盟,而非政治聯盟;機構設置上,只有歐洲央行,沒有單一的“歐洲財政部”。
三、歐元危機的影響
1、歐元危機改變了全球貿易格局
歐元匯率的變化,讓新經濟體國家在歐洲貿易無利可圖,并且出現逆差。截止到2010年5月14日,歐盟作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在5個月中人民幣對歐元累計升值了14.5%,導致我國對歐洲出口競爭力大幅下降,給中國的出口商造成巨大的成本壓力。據相關數據顯示,中國在2010年3、4兩月,對歐洲貿易出現逆差。
2、全球資產價格泡沫開始破滅
2008年下半年以來,次貸危機越演越烈,美元指數跌至74點,貨幣危機開始出現。隨著美元的走低,全球大宗資產價格出現暴漲,國際原油價格從36美元一路上揚至83美元,銅鋁鎳鋅錫更是假借各種題材出現暴漲;黃金價格更是出當貨幣儲備抵御通脹的先鋒,從920美元上漲到1250美元;各種農產品價格也在不斷攀升。然而,這些不斷上漲的價格泡沫基本都輸送到像中國這樣的新經濟體國家。美元走強,這些資產價格泡沫會陸續破滅。
四、結束語
從根本上講,一些銀行在希臘債務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中的表現并無大的區別,即大量地使用衍生產品,將實際的債務和風險轉移出資產負債表,將真實的風險掩蓋起來,因此,加強金融監管,從制度上穩定金融體系,應在世界各國提上議事日程。此外,在監管模式方面,國際協作顯得十分必要。
最后,歐元危機進一步證明了,國家信用不是無限額的,這對于全球經濟體系是一個重要的警醒,對未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提供了重要的教育意義。
[1]管清友: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根源[J].中國經濟周刊,2010(20).
[2]王慧卿:歐元危機導致人民幣匯改重啟延遲[N].第一財經日報,2010-05-20.
[3]馬光遠:歐元危機不會逆轉全球經濟復蘇[N].東方日報,2010-05-11.
[4]李石凱:國際儲備貨幣競爭與歐元危機[J].中國金融,2010(11).
[5]苗剛:希臘危機與主權信用危機[J].金融·資本,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