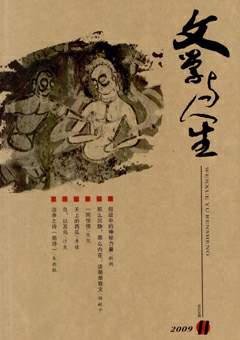恨水東逝
尋尋覓覓,踏遍四股頭、鼓樓巷、南門口、大井頭弄巷的角角落落,我試圖從中找出點童年、少年時代張恨水游玩過的痕跡,終一無所獲。我依然沒有灰心,一有空閑,就像地質(zhì)勘探隊員抱著發(fā)現(xiàn)新大陸的決心,連一塊瓷片、一截殘垣、一棵古樹都不放過,竭力尋找,并把范圍擴大到馬王廟、金龍崗、茶廠路、箭道巷、水南街等地,甚至我把眼光瞄向了軍分區(qū)深遠、森嚴的大院內(nèi),百年前此乃樹木參天、鳥鳴啁啾、松鼠雀躍之地,恨水能不樂這里?網(wǎng)知了、捉蛐蛐、躲貓貓……我實在是編不出進去的理由,警惕地環(huán)繞無情的院墻欲做窺探,又怕惹是生非。天氣晴朗時,疲倦了,就坐在信江邊發(fā)發(fā)呆,回望身后日新月異的城市,恨水東逝。
張恨水,人們見的他最多的一張黑白照片是,左側(cè)像,頭發(fā)一絲不茍地往后梳,眉毛清爽,目秀而有神,透射出睿智的光芒,雙耳靈俊,嘴角流露出一絲難以覺察的微笑,中山裝上衣的領(lǐng)口牢牢地扣著,充溢著一個嚴謹?shù)奈逅奈娜说男蜗?瀟灑、和善、親切。
老行署大院內(nèi)那幾棵柚子樹是前清一位知府栽種下的,年年開花結(jié)果,仰望濃蔭碧綠的柚子樹,想必恨水小時候玩耍、學習、射箭時曾經(jīng)偷摘過未熟透的柚子。夏季來臨,傍晚時分,泡在信江的孩童中,一定少不了恨水調(diào)皮的身影,蕩漾著恨水夾雜饒腔、徽調(diào)的追逐嬉笑聲。岸上,曾國藩部將、得紅頂花翎三品銜的爺爺張開甲酷愛孫子,捋須笑呵呵,陶醉在夕陽下的信江,或者陪同孫子擊水暢游。
信江還見證了他兒時坐在高頭大馬上與爺爺馳騁水南街,接受黎民注目禮,稱道嘖嘖。光緒二十一年恨水出生在上饒,直到光緒三十一年爺爺病卒才隨當稅務小吏的父親依依不舍離開上饒。
在一個蒙蒙細雨的春天,一家老小撐一船,回眸“署中騎老羊,習弓箭,日以為課”之情景,歷歷在目;回望高大的南城門,蕩悠悠的浮橋,漸漸遠去,沿信江而下,過鄱陽湖進入南昌,從此恨水一生顛沛,輾轉(zhuǎn)南北,放棄了將門尚武而執(zhí)筆從文,一支筆蕩氣回腸寫盡人間悲歡離合,寫出一大家人的柴米油鹽,寫就了一代現(xiàn)代章回小說的宗師。
然而,多少人談到恨水時,往往忽視了降生、養(yǎng)育恨水成長的上饒,大都只是蜻蜓點水一筆帶過:出生在廣信府(今上饒),甚至連一位稱研究張恨水二十余年、披閱6000多萬字、走訪張恨水十余位家人的學者在寫張恨水情歸何處時,仍然草率恨水十一年的上饒情結(jié),整本書關(guān)于張恨水與上饒的點點滴滴真是惜墨如金,讓我這個后來進入上饒的人也扼腕嘆息,繼而失笑。恨水情系桑梓,有文章佐證:1939年9月的《前線日報》曾發(fā)表恨水的一篇散文《我與上饒》,里面就寫道:“……真愧對昔日上饒街頭觀我坐轎父老也。”而且整篇文章洋溢著濃釅的故鄉(xiāng)情懷,“每出郊,常過一橫跨河面之浮橋。兒時以浮橋為奇,故上饒之橋于予印象較深也。”如今讀來,仍然看得出正值創(chuàng)作高峰的張恨水對上饒的一往情深。
閱讀張恨水《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啼笑姻緣》、《北雁南飛》等主要著作,心細者會發(fā)現(xiàn),里面隱約閃爍著很多上饒的風物脈絡,尤其是《北雁南飛》第二節(jié),簡直就是上饒南門口信江兩岸在紙上的再現(xiàn),似乎讓我們看到了當年的浮橋、水南街、上灘頭、東瓦窯、丁家洲等處所,十分親切,這是恨水把對故鄉(xiāng)的思念化作文字,寄托了一種追思、感懷、記憶。
離別上饒后,恨水是否再來過上饒?抗戰(zhàn)時期,他活動地點主要在陪都,辦報、寫小說,但透過《前線日報》,以及上饒一些老人的回憶,他當時確實在上饒活動過一段時日,與許多的文藝界進步人士一起共同用手中的筆宣傳抗日。自此之后,恨水就再也沒有踏上上饒這方故土。
名字是一個人出生后的符號,隱藏預兆,筆名卻蘊涵著更廣泛的意義。誰能破譯恨水的密碼?恨水是他的筆名,心遠才是真名,好男兒志在四方,恨水十一歲離開上饒就預感到自己的一生將是漂泊的一生,很難再回故鄉(xiāng)信水河畔,第一次投寄作品遂借李煜的詞句“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表達對滄桑歲月的無奈。解放十七年,恨水多病加上當時的外部環(huán)境,他都沒能回到生他養(yǎng)他的上饒走一走看一看,常常念叨上饒,抱憾終身,在1967年那個料峭的初春悄然謝世,僥幸避免了一場更大的文化浩劫。
上饒沒有忘記恨水,1995年版《上饒市志》對于張恨水是有一定篇幅的記載的。有一點遺憾的是,上饒沒有張恨水紀念館之類的憑吊處,連一條路或者某個弄也沒有安上與恨水相關(guān)的符號,是否與長期以來沒有公正、公道的對待有關(guān)系呢?
墻內(nèi)開花墻外香,十一歲從上饒走出的張恨水,享譽文壇,這是上饒的驕傲。無論外面怎么搖旗吶喊張恨水是哪里人氏,無論張恨水寓居過多少城市、鄉(xiāng)村,甚或張恨水面對世俗的偏見而處于兩難境地作出違心的選擇,但有一點可以不容懷疑,恨水沒有忘記上饒。1967年初,北京磚塔胡同內(nèi),一個老人春眠易曉,常常佇立門口,望斷南飛雁,返回書房寫不盡故園的魂牽夢縈。在張恨水看來,鄉(xiāng)愁是當年離去的茫茫水路,浮橋、城墻、茅草洲都成為了記憶的郵票,塵封在歲月的信封上。
我常常思考,何以如此執(zhí)著地去追尋一個與我不著邊際的歷史人物呢?以致依然會在尋常日子里,腋下夾一個小包像裹著飽滿的答案去求證,徜徉上饒昔日府署地,去尋找恨水的遺跡,他才走了多少年啊,就蕩然無存了嗎?歷史上有多少東西都摻雜了后來好事者的畫蛇添足?張恨水是怎樣撞進我的視野里的?我實在回憶不起來,但是自從我知道張恨水是上饒人后,就特別的亢奮、激動,這就是我說服自己癡迷張恨水的理由吧!
其實,我又何嘗不在尋覓中獲得了一種精神上的給養(yǎng)、愉悅?
石紅許:1967年5月生于江西鄱陽。中國作協(xié)會員。現(xiàn)任上饒市文學院副院長、市作協(xié)副主席。著有散文集《青蔥歲月》、《在城市流浪》等。散文見諸《散文百家》、《散文世界》等刊物,入選《江西散文十年佳作選》等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