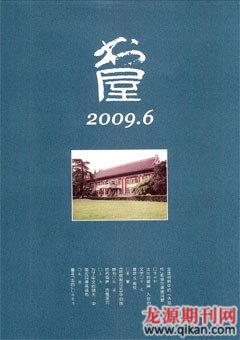名士軼事四則
裴毅然
愛開會的周揚
1961年春,周揚、以群等人到杭州討論電影劇本《魯迅傳》與《文學原理》,《文學原理》是以群主編的大學文科教材。夏衍秘書、上海女作家李子云當時因病在杭州屏風山工人療養院休養。當她得知周揚、以群來杭州,便跑到岳墳杭州飯店去看他們。不知誰建議大家去虎跑喝茶,十余人便乘一輛面包車去了。進入山寺,在茶室里坐成一個以周揚為中心的橢圓形。當時氣氛很好,不少人想利用這一難得機會向周揚討教,開始語聲嘈雜,逐漸四座安靜,周揚開講。周揚夫人蘇靈揚卻十分氣惱,她對李子云說:“這個人就知道開會,離了開會就過不了日子,難得出來走走,坐下來又開上會了。真沒辦法。”李子云感慨萬千:“我突然感到一種對周揚同志的同情。一天到晚不知疲倦地開會,這種生活該有多單調。許多領導同志公余都有一些愛好,周總理愛跳舞、看越劇,陳老總愛下圍棋(路過上海機場停留幾小時都叫棋友去下棋),潘漢年愛打百分,夏公愛集郵,周揚同志業余可喜歡什么呢?我沒發現。似乎除了開會就是變相開會的談話。”
1953年春,李子云第一次見到周揚。她說:“周揚同志正值壯年,精力充沛,講起話來,一口湖南口音,滔滔不絕。即使兩三人談話,周揚同志講話也像開會一樣,言必馬列,有條有理,一絲不茍。到了開會場合,那就更不用說了……他不僅言必馬列,而且言必工作……約到他家談話,他的談話也很少超出工作的話題……周揚同志似乎更習慣開會,似乎從開會中能夠得到一很大的樂趣。”
“文革”后,周揚復出,許多單位請他去演講和作報告,周揚幾乎有求必應,一些至愛親友再三勸阻,還是其習難改。至于文藝界的會議,他更是每會必到,每到必講。1984年秋,周揚病勢漸重,躺在醫院里起不來,腦血管障礙使他經常說錯話,但當王蒙去看他,告辭時另一探望者問王蒙即將在京西賓館召開的文藝座談會,周揚眼睛一亮:“什么會?”口齒不再含糊,語言再無障礙,笑容不再隨意平和,目光如電,“他恢復了嚴肅精明乃至是有點嚴厲的審視與警惕的表情”。弄得王蒙與另一位探望者哈哈大笑,勸他老人家養病要緊,不必再操心這些事情,自有年輕同志去處理。王蒙說:“這是我最后一次在他清醒的時候與他見的一面,他的突然一亮的目光令我終身難忘。”這道因“開會”亮起的目光,蓋因使王蒙刻骨銘心,數年后成為悼文標題《周揚的目光》。
當今青年及后人必生疑惑:最最令人頭疼的開會何以會成為周揚的樂趣?更何以在生命之火漸趨熄滅時還會激起一道回光返照的目光?他們不知上世紀五十年代,參加各種會議成為中國人民新生活的一大標志。文藝革命起家的左翼文化人自然十分習慣看重思想革命。從源頭上,革命必須開會乃是來自蘇聯的“光榮傳統”。1922年,初次訪蘇的張國燾就抱怨:“在莫斯科,各種各樣的會議是永遠開不完的。這些會議所花的時間也冗長得可怕。”鄭超麟回憶莫斯科東方大學生活:“每次開會常常兩個、三個、四個鐘頭,緊張、興奮、熱烈。有甚么工作做呢?沒有工作做。有甚么學問研究呢?沒有研究理論問題。開會時間大多數消磨在‘個人批評上面,所批評的并非具體的事實,而是一些抽象心理形態,例如:你個性強,你驕傲,你有小資產階級習氣,你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等等。被批評者也想出類似的批評以批評批評者。結果大家面紅耳赤,心里種下仇恨的種子。總之,大家學會了孔夫子寫《春秋》的筆法:誅心;又學會了宋儒的正心手段,不過不是用來責己,而是用來責人。”
1942年,一位共產國際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訪問延安,沒多久就發現:“在軍隊里也像在特區(即陜甘寧邊區)各地一樣,惟一的工作就是開會。”這也許有點夸張。不過,那句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著名流諺“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出處居然是周揚本人。1960年春,上海作協在中宣部統一部署下召開反修正主義會議,旗號為“批判修正主義文藝思想,重新估計近代資產階級文學”,意在“破除對資產階級文藝的迷信,攀登無產階級文藝高峰”,聲勢浩大,調動復旦、華東師大、上海師院中文系學生到作協參加,華東師大中文系女生戴厚英就是在這次會上得譽“小鋼炮”。此會長達七七四十九天,開會就是工作,工作就是開會,實在超出今天年輕人能夠想象的范疇。至于這次長會的成果,“在這次會議中,除去領導這場批判的三五成員之外,當時上海知名的美學家、文學理論家幾乎無不受到了傷害”,如錢谷融、蔣孔陽、羅稷南等。最著名的觀點是:“越是‘精華越反動,毒害越大。”本來上海“四十九天會議”要推廣至全國,因上峰考慮到以如此簡單的方式橫掃西方國家的“國寶”,尤其蘇俄文學也橫掃在內,涉及國際關系,這才作罷。“文革”時,哈爾濱某女知青嫁給聾啞人,問及原因,乃是此男享有“會議豁免權”——不用參加任何會議,能有時間多料理家務。
上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會議之多之長確為意味深長的歷史一景。當時從上到下,動輒就開幾十天的會。如1959年夏驚天動地的廬山會議,會期四十六天;1962年初空前絕后的“七千人大會”,二十八天。基層每縣初冬的“三級干部會議”,年年必開,一開也要十天半月,甚至二十多天。廠礦學校商店也是大會小會不斷,一開就是半天。后人一定會問:“有那么多要說的事兒么?有那么話么?既然有那么多內容,為什么不寫下來發給大家?”但那時候的人是不敢這么問的,會也開得很認真,有作用沒作用至少大家聽得十分認真,這才有喜歡開會的周揚。否則,聽眾沒精打采無所謂不耐煩,他在上面“對牛彈琴”,還會有什么精神頭?
“文革”以后,隨著“思想革命”重要性的下降,會議銳減。進入二十一世紀后,市場經濟也不允許開那種無效的冗會。謝天謝地,總算饒了我們,開會不再成為普通百姓的日常必修課。不過,當我們回首“愛開會的周揚”,一絲苦澀,一聲輕嘆,在咀嚼內中諸多歷史信息的同時,自然也一并丈量出歷史跨邁的距離。
蔣光慈讓美女
“五四”時期異軍突起的創造社,向以提倡浪漫主義著稱,風習所向,社團成員又正值鼎盛春秋,自然免不了發生一些浪漫花絮與風流韻事。1927年“四·一二”后,廣東梅縣學子黃藥眠只身赴滬,進了其時由成仿吾主持的創造社出版部。黃先生晚年在回憶錄《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中記載了幾件浪漫故事。
首先是郭沫若第二本詩集《瓶》中的女主角,即日籍李安娜女士,與創造社出版部管財務的成紹宗發生戀情。成紹宗乃成仿吾親戚,這位老兄裹卷出版部現款攜帶安娜女士私奔外逃。其時,郭沫若因參加南昌起義,隨部隊撤退廣東汕頭,轉道經香港去了日本,以逃避蔣介石的通緝。李安娜在上海只身帶著孩子,住在創造社出版部內,與成紹宗同樓相居,歲值春秋鼎盛,朝夕相處,日久生情,亦在難免。
第二件花邊新聞的主角是一位安徽人,名喚梁預人,文化程度不高,長相也一般,乃創造社出
版部工作人員。武漢政府失敗后,他的安徽老鄉帶著年輕妻子跑來上海。這位安徽老鄉詩寫得不錯,頗有一點才華,但在上海找不到合適工作,只好回安徽去。不料,那位年輕妻子突然不想回去,而同梁預人要好起來。兩位男性老鄉公開談判,詩人說是尊重女性意見,既然她愿意跟梁預人,便留下她在上海以遂其愿,詩人只身回皖。可是,詩人半途生變,忽然想不開了,沒有搭船回去,第二天一早來找梁預人“結賬”。梁預人剛從床上坐起身,詩人便一菜刀劈下去,幸好有墻擋著,只劈了第三者腦袋的一部分,不然可真就只剩半個頭了。后來,經諸多朋友左右相勸,那位“紅杏出墻”的女人跟著詩人回了安徽,事情才算平息。此事若放在今天,恐怕就沒那么簡單了,梁預人肯定會訴至法院,告詩人一個故意傷害罪,不僅能夠正大光明地得到所愛之人,而且還能撈到一筆不小的賠償。
黃藥眠先生乃1903年出生,其時二十四、五歲,正值青年英俊。他在上海站穩腳跟后,這位廣東高師畢業生既在創造社出版部當編輯,做校對,又外出兼課教書,還譯書賺版稅。一年多后,他每月已有一百八十元左右的進賬,去咖啡店消費,一杯兩角錢的咖啡,常常扔下一塊錢結賬,不要找頭要派頭。店里的女招待自然極其歡迎他,每次去時,“就投懷就抱,調笑一番”。
蔣光慈也是安徽人,留蘇生,當時也才二十六、七歲,在創造社出版部吃飯。那年初春,桃花盛開,一位摩登小姐手抱一束桃花來找蔣光慈。恰好黃藥眠在出版部,便對這位光艷照人的摩登小姐說:“蔣光慈先生不在,要到吃午飯的時候才來,要嘛你在這里坐坐等著他。”摩登小姐躊躇了一會兒,答曰:“那么我等一會兒再來吧!”抱著一束花悻悻而去。黃藥眠見有美女如此公然“倒追”,十分艷羨,不免暗想:“人生在世,固不當如是乎?!”蔣光慈回來后,聽聞此事,笑著對黃藥眠說:“你喜歡她嗎?我可以轉介紹給你。”黃不好意思地說:“這樣美的姑娘還不好嗎?你接受她的愛吧!”蔣光慈又笑了:“這一類的女子,我實在太多了。我有點應付不過來了。”黃藥眠心里有些矛盾,嘴上說:“我不要!”但心里卻想:他不要的女人,我接收過來豈不令人笑話?有本事就自己去找,戀愛也有個策略問題,應該使對方來追求我,然后由自己決定是否接受。若卑屈地去向女人苦苦哀求,實在有失男人氣概。
青年黃藥眠當年能有如此“戀愛真經”,較之當今青年,可謂著實先鋒超前。至于較之筆者這一代,簡直就是“顛覆性革命”。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們這一代人的青年時期,哪里會有“女追男”的道理!若哪位女青年有此勇敢,那么也只能得到一個字——“賤”!
1930年,蔣光慈娶紹興柯橋來的女學生吳似鴻為妻,但1931年5月就病倒,入上海同仁醫院治療腸結核,6月30日逝世。吳似鴻在《大風》雜志上發表紀念丈夫的文章,內中有一段:“光慈的為人,和他的思想完全相反,是很守舊的。他的理想中的女性,是一個具有良妻賢母的資格、能料理家務、終日不出、日日夜夜可以在閨房里伴他著書的女性。這,我卻辦不到,因此在他的晚年,每有和我意見相左的地方。”
詩怪林庚白
南社詩怪林庚白,福建閩侯人,十余歲便負笈北京,熱心政治,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加入京津同盟會。民國元年,在上海與陳勒生等創辦“黃花碧血社”,專以暗殺帝制余孽為急務。“二次革命”失敗后,浮沉宦海,初任參議院秘書,一度代理秘書長,年方二十二歲。少年得志,卻郁郁不歡,不久發憤為詩,師事“江西詩派”陳石遺,才氣艷發,思想新穎,人多以李義山目之,后有“中國一代詩人”之譽。其人個子不高,膚色潔白,眉清目秀,鼻子高挺,有點洋人相。自稱:“十年前論今人詩,鄭孝胥第一,我第二。倘現在以古今人來比論,那么我第一,杜甫第二,孝胥還談不上。”哄堂大笑,他本人卻若無其事。曹聚仁在南社雅集時演講,說到南社與辛亥革命之關系,認為辛亥革命乃是浪漫氣氛很濃的政治運動,南社詩文就是龔自珍氣氛的詩文,林庚白就是活著的龔自珍。柳亞子點頭為是,而林庚白卻大不高興:“我心目中尚且無李杜。更何有龔定庵?曹某比我作龔定庵,未免太淺視我了。”時人自然皆指為詩狂。柳亞子與他訂交三十余年,眼高于頂的柳亞子置評:“庚白的詩,理想瑰奇而魅力雄厚,雖余亦愧謝弗如。當代抱殘守缺者,又足當其劍頭一啖耶?”
詩怪一生玩世不恭,游戲人間,猶如龔自珍所說的“亦癡亦黠”。但這位老兄潛心研究命理之術,甚喜占卜,自謂大有心得,著有《人鑒》一書,其中預言章士釗入閣、林白水橫死、孫傳芳入浙、廖仲愷死于非命,時人評日“皆言之確鑿如響斯應”。汪精衛走狗梅思平請林庚白排八字,梅思平為人卑污,詩怪對他并無好感,且當時上海正有某女法官因貪贓案發,喧騰報章,鬧得滿城風雨,林庚白便笑著對梅思平說:“照你的八字排來,你的命恰和某女法官一模一樣。”梅大斷。
另傳袁世凱稱帝,冠蓋滿京華,一片彈冠相慶。林庚白笑對友輩預言:“項城(袁世凱字)壽命將終,那些彈冠相慶者,徒以冰山為泰山,殊不知皎日既出,豈不盡失所恃么?”朋友聞言,自然追問其故,再曰:“項城命中,厥祿太多,祿可比之于食,腸胃有限,而所進過量,不能消化,積滯日久,必致脹死。”友輩均不信,林庚白特撰一文,擬發表于刊物。友輩勸阻:“項城氣焰方熾,安得攫其逆鱗以取禍耶?”林庚白答:“既如此,此文留待他年作證,姑且藏諸行篋。”不久,袁世凱果死,所書項城死去年月日,絲毫不爽。這時,人們大驚,以神視之,求推算者日眾,林庚白應接不暇。于是,規定潤例,每算一命,須致百金,且以當年米價為準,每石十金,百金之數,易米十石。以每石五十公斤計,五百公斤求算一命,門檻相當高了。
林庚白后來專仰看相算命為生,擯絕詩文而不為。架上案頭,盡是五行六甲之書;枕畔榻旁,全是玄機妙理之籍,幾近汗牛充棟。
1941年末,林庚白在重慶當立法委員,他為自己算命,深知不妥,有過不了年的恐慌。為避日機轟炸,千方百計攜眷走避香港,以為如此可逃厄運。不料,抵港僅八日,即遇日軍偷襲珍珠港,日軍旋即進占九龍,一周后林庚白夫婦在尖沙咀設法渡海,因誤會,一群日軍開槍射擊,詩怪胸部中彈,倒臥血泊而咽氣。因倒斃途道,無人辨識,暴尸數日,后為閩南同鄉會中人認出,為插一浮簽。友人聞之均再三嘆惜,謂其雖通命理,奈何昧于古訓“劫數難逃”。
夫人林北麗(其母其姨均乃秋瑾高足)右臂中彈,受重傷而未死,臥病孤島,1943年回內地后,窮愁度日。
南社詩翁柳亞子嘗笑謂詩怪乃“客廳社會主義者”,以喻其缺乏實踐精神。
羅隆基花生米
大名鼎鼎的羅隆基,字努生,江西安福縣楓田鎮人。九歲喪母,自幼受父親熏陶愛好古典詩詞,天資聰穎,有神童之稱。1913年以江西總分第一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堂。五四運動以學生領袖身
份,沖殺在示威隊伍最前列。1921年,羅隆基考上公費留美,先后入威斯康星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因敬慕著名政治學家拉斯基,赴英求學于拉斯基教授門下,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1928年學成回國,任教于上海光華大學,創辦《新月》雜志并任主編。因發表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言論而被捕。“九·一八”事變后,在上海各大學公開演講,主張武力抗日。“皖南事變”后,積極發起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任中央常委兼宣傳部長。他與張瀾、沈鈞儒等民盟參政員一起支持中共參政員,譴責國民黨的倒行逆施,拒絕出席國民參政會。后羅隆基宣布脫離國社黨,赴昆明西南聯大任教,創建民盟昆明支部,擔任主委。
就是這位羅隆基,人生前半段政治上風光,感情上風流,很有點花絮。大約1928年間,羅隆基夫婦海外歸來,路過新加坡,登岸拜謁其泰山岳翁。羅妻也是留英生,乃新加坡華商張永福千金。羅為撰寫“英國選舉”博士論文,師從拉斯基教授時得識張小姐,由追求而相戀,由相戀而相愛。后來,羅隆基看上徐志摩前妻張幼儀,于是偽裝其兄張君勱信徒,加入張君勱領導的國社黨,以為鄰水樓臺可近月。不料,張幼儀對他毫無感覺,避之惟恐不及,羅的追求毫無希望,但羅認為這可能是因發妻存在之故,遂決心擺脫束縛,但又怕妻子討要贍養費,便每天抓住太太頭發亂打亂捶。張小姐也是弱不禁風的千金,哪里經得起這般拳腳,什么要求都不敢提,只求自動下堂。羅與元配離婚后,還是沒追成張幼儀,第二位羅太太乃是有名的王家右,曾在北方為國民黨做婦女工作。但這位王家右似乎不怎么在乎羅隆基,羅再怎么討好她,她還是要求“拜拜”。盡管羅一直不承認與王家右離婚,王卻嫁給已故影星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做了唐的第五任太太。
二戰期間,羅在昆明西南聯大教書,“佳話”不斷,聯大稍有姿色且家道素豐者,都被他追過。一次,他從圓通街經過,看見一位頗具風韻的少婦,頓被迷住,便使用跟蹤慣伎,沿途還打聽少婦住處。少婦無可奈何,只得走進街口小鋪子買花生米,想等羅走過去。不料,羅追進鋪子,從后面伸手替她付錢,兩人當時便發生口角,事情鬧大。少婦控訴至昆明地方法院,其夫也是某大學教授。開庭那日,旁聽者人山人海,擠得水泄不通。羅隆基未出庭,由律師代理,又巧這太太聽覺不佳,法官審理時有些話聽不清楚,她便索性將羅如何跟蹤尾隨,直至小鋪買花生米,原原本本吐出。羅之律師也無法為羅聲辯,惟一的辯護理由是:“羅太太非常漂亮,羅先生不會在外面攪七廿三尋花問柳的。”后來,這樁艷案在另外幾位大學教授出面斡旋卞,不了了之。但是,那家小鋪子的花生米卻因此聲名鵲起,每位游公園者,幾乎人手一包,呼為“羅隆基花生米”。
1947年11月,南京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民盟要員一一遠走高飛,羅隆基準備避走杭州,定于19日晚于梅園新村民盟總部與愛人浦熙修話別,羅、浦艷聞早已風傳,只是始終沒有完全公開。那晚,浦小姐如約前往,兩人正在情話喁喁,離情萬千,浦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驅車趕到,惹出一幕桃色大案。那天,因民盟總部全部撤離,辭退所有傳達侍役,袁子英趕到時,門口無人阻攔,袁直撞內室,目睹羅、浦熱烈擁抱,盛怒之下,上前各掮羅、浦一記耳光。羅、浦聯合反擊,上演一出全武行。直至警察趕到,這才平息,各自走人。事后,羅、浦關系徹底曝光。此時,浦熙修三十七歲,與袁子英結婚也有十余年,育有兩女一子,且快成人。但她堅持與袁離婚。袁子英乃華中礦務局副局長,素有“好人”之譽,他早就知道浦熙修紅杏出墻,為了名譽顏面不愿捅破這層窗戶紙。據說他幾次命子女環跪浦熙修膝前,苦苦泣諫,然而女人要離婚八匹馬都拉不回,終未挽回。袁只得延聘律師與浦正式離婚,浦也“寧為愛情死,不受舊禮教束縛”。只有羅隆基還想為自己辯護幾句,但他此時因政治,行動受限制,不能自由發言。
羅、浦桃案喧騰一時,三位主角,一為政治家、一為女記者、一為官員,均有頭有臉,成為社會各階層酒桌上的談資笑料。同代人溫梓川先生評羅隆基:“為人急于功利,而性格又異常倔強。”近年讀章詒和的《往事并不如煙》,內有章伯鈞誡女之語,說羅對女人有特別磁力,想來大致不錯。
1949年后,羅隆基任政務院委員、森工部長、全國政協常委、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副主席,以及使他真正名揚天下的大右派。1957年3月19日。羅隆基在全國政協二屆三次全會上發言“加強黨和非黨知識分子的團結”,光明磊落的態度和誠懇的“直諫”引起與會者強烈反響,爆發出雷鳴般掌聲。6月21日,羅隆基出席科倫坡世界和平理事會議回國,等待他的是一頂沉重的右派帽子。1958年1月26日,被撤民盟中央副主席職務;31日,被撤人大代表及森工部長,工資從四級降到九級。香港有人邀請他赴港辦報,周恩來約見羅隆基,轉告香港方面的邀請:“如果你想去的話,隨時都可以去。不論去香港,去美國,都可以。我想你是不會去臺灣的。”羅隆基很堅決回答:“總理,謝謝你的關心,我哪兒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這里。”他確實哪兒也未去,在北京乃茲府度過人生最后的悲涼歲月。
1965年12月7日子夜,羅因突發心絞痛,孑然一身猝離人世。此時,他無妻無子。因戴著“右派分子”帽子,沒有追悼會。1986年10月24日,民盟中央在全國政協禮堂三樓大廳隆重紀念羅隆基九十誕辰。人大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代主席楚圖南講述了羅隆基生平事跡。中共統戰部長閻明復追述了羅隆基的一生,肯定了羅隆基對革命的貢獻,認定他是知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動家。羅主要著作有《人權論集》、《政治論文集》和《斥美帝國務卿艾奇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