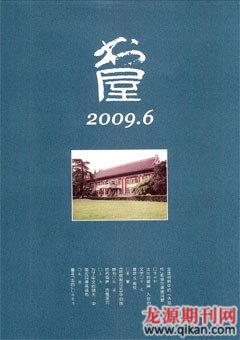磚石有聲 古雅深沉
王 杰
2008年2至8月,我在英國(guó)曼徹斯特大學(xué)“藝術(shù)、歷史與文化學(xué)院”從事學(xué)術(shù)研究,主要合作者和聯(lián)系人是該院的“泰勒講座教授”、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píng)家和文化理論家特里·伊格爾頓。與伊格爾頓的接觸,我總體印象是他對(duì)中國(guó)文化的現(xiàn)狀以及中國(guó)理論界的現(xiàn)狀了解不是很充分,因而我邀請(qǐng)他今年到中國(guó)進(jìn)行學(xué)術(shù)訪問。
中國(guó)正在發(fā)生著劇烈的變化。因?yàn)檫@個(gè)變化與我們自己有著太多感情上和行為上的糾纏,也因?yàn)檫@些變化離我們太近,因而反而不容易看清楚甚至出現(xiàn)某種認(rèn)識(shí)上的“盲區(qū)”,這是目前中國(guó)人文學(xué)科起碼是美學(xué)和文學(xué)批評(píng)的某種現(xiàn)狀。加強(qiáng)國(guó)際合作與交流也許有助于我們更全面地看清自己和現(xiàn)實(shí),也許因?yàn)檫@個(gè)原因,德國(guó)藝術(shù)家湯瑪士·雅可比(Thomas Jacobi)的作品引起了我的很大興趣,他用自己的方式再現(xiàn)了中國(guó)的現(xiàn)實(shí)。
一個(gè)十分偶然的機(jī)會(huì)我得以接觸到湯瑪士·雅可比的藝術(shù)作品。雖然這種接觸是膚淺的,但還是觸動(dòng)了我。他的藝術(shù)觀念、表現(xiàn)手法,以及對(duì)歷史“記憶”的特殊激活方式在我看來都很有意義,可以為我們思考當(dāng)下的中國(guó)文化、全球化條件下的中國(guó)文化提供一個(gè)特殊而有趣的視角。我們先看看藝術(shù)家本人的一段簡(jiǎn)短陳述:
2005年秋,通過中德藝術(shù)家交流計(jì)劃,我初次來到福州,我的福州朋友把我?guī)У揭粋€(gè)他們稱之為“德國(guó)”的地方,我被那里帶有歐洲風(fēng)格的建筑景觀所震驚。據(jù)說那里是十九世紀(jì)外國(guó)人居住以及工作的地方。包括商業(yè)特區(qū)、辦公樓、大使館、學(xué)校、教堂、醫(yī)院以及花園等,顯示了當(dāng)時(shí)歐洲人在那里生活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以及對(duì)于該城市的重要性。如今,我們只能看見少量的舊房舍以及殘存的痕跡。中國(guó)城市的巨大轉(zhuǎn)變帶來一種建筑知識(shí)與傳統(tǒng)的失落,把先前歷史的存在抹去了,但這種殘存建筑的存在卻提供了先前歷史的經(jīng)驗(yàn)。關(guān)于我們所處社會(huì)的歷史。往往只是被簡(jiǎn)單地在特意選擇的地圖、照片、書籍以及博物館展覽有所展示。我的取名為“德園”(German Garden)的中式掛軸試圖以紀(jì)錄的方法來把“人類學(xué)的現(xiàn)場(chǎng)”轉(zhuǎn)化到我的作品中。拓印刻在石頭上的書畫一直是中國(guó)的傳統(tǒng)。在這里成為引起一種意識(shí)的材料,這就是歷史本身以及依托于歷史的物質(zhì)文化。歷史是活的記憶的過程。對(duì)我而言,她塑造與追溯人類的思想、激情以及行為,從而有利于確定我們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
“德園”是一組以中式掛軸的形式呈現(xiàn)的作品,作者努力用最樸實(shí)、最物質(zhì)性的l方式來呈現(xiàn)和再現(xiàn)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感悟和對(duì)歷史記憶的追溯。這一組作品的創(chuàng)作時(shí)間大約從2005年起持續(xù)到2008年,創(chuàng)作的手段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用中國(guó)傳統(tǒng)的拓印石刻的方式拓印歷史的遺跡以及現(xiàn)實(shí)中殘存的物品,以這種方式把過去和當(dāng)下的生活經(jīng)驗(yàn)聯(lián)系起來;另一種創(chuàng)作手法是將歷史遺跡中的磚瓦等建筑材料研磨成粉制成顏料,通過最簡(jiǎn)單的刷涂,形成某種審美形式,這些作品以其特有的質(zhì)感和“空虛”,向我們呈現(xiàn)出歷史中某種深沉并且仍然在向我們不斷言說著的存在。
中國(guó)的現(xiàn)代化過程不同于英國(guó)和德國(guó),這是一個(gè)不爭(zhēng)的歷史事實(shí),因而中國(guó)人和藝術(shù)家解讀歷史的“視角”,或者說對(duì)歷史敘事的選擇也不同于英國(guó)、德國(guó)的人們和藝術(shù)家,這是可以理解和應(yīng)該尊重的。我想,湯瑪士·雅可比用他的一系列作品向我們提出來的問題是:人們對(duì)歷史和生活的感受是否會(huì)因?yàn)楝F(xiàn)實(shí)的利益而遮蔽一些東西呢?如果存在著這樣一種現(xiàn)象,那我們是否可以,或者說怎么樣用藝術(shù)的語言去恢復(fù)歷史本身,或者說去激活歷史的記憶呢?關(guān)于中國(guó)的現(xiàn)代化、關(guān)于中國(guó)現(xiàn)實(shí)中的各種社會(huì)現(xiàn)象和文化現(xiàn)象,我想不同的社會(huì)群體和社會(huì)集團(tuán)會(huì)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見,在目前和今后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內(nèi),這種分歧都會(huì)存在和持續(xù)。湯瑪士·雅可比這一組藝術(shù)創(chuàng)作用最物質(zhì)性的材料和質(zhì)樸的藝術(shù)語言來闡釋和顯現(xiàn)自己的感覺、思考和觀點(diǎn),努力用藝術(shù)的形象把觀眾帶到“人類學(xué)的現(xiàn)場(chǎng)”,或者說讓觀眾感受曾經(jīng)存在的歷史經(jīng)驗(yàn),這種努為和藝術(shù)創(chuàng)作建立在嚴(yán)謹(jǐn)?shù)乃伎己屯评淼幕A(chǔ)之上,無疑富于創(chuàng)造性和現(xiàn)實(shí)的文化意義。
拓印是一種十分古老也完全中國(guó)化的復(fù)制藝術(shù)作品的技術(shù),它的基礎(chǔ)在于中國(guó)石刻藝術(shù)的發(fā)達(dá)以及中國(guó)特殊的藝術(shù)觀念。在古代中國(guó),漢代的磚石畫像、魏晉的石碑刻、唐宋的摩崖佛像石刻都是中國(guó)古代藝術(shù)史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漢代的石畫像藝術(shù)和魏晉的石碑刻藝術(shù)都是在外來文化進(jìn)入中國(guó)(例如佛教傳入)之前的藝術(shù)類型,因而具有十分純正的中國(guó)風(fēng)格。拓印是復(fù)制石畫像和石碑刻、摩崖石刻的基本手段,也是將非藝術(shù)性的石畫像、石碑刻、摩崖石刻等等轉(zhuǎn)變成藝術(shù)作品的基本手段。在中國(guó)文化中,那些石畫像、石碑刻、摩崖石刻等等原是具有重要社會(huì)功能和文化功能的,不是隨便可以用來欣賞的審美對(duì)象,只有拓印并且裝裱之后,這些或神圣、或威嚴(yán)的法器才成為藝術(shù)作品和審美對(duì)象。以漢代畫像石為例,它最初就不是為了審美的目的而創(chuàng)造的,把它們看作藝術(shù)作品其實(shí)是后來的事。1980年出土于山東嘉祥縣宋山的一塊畫像石上的“題記”中就明確刻著這樣的文字,說明這些石畫像的特殊作用,并警告所有的不敬之人:
唯諸觀者,深加哀憐,壽如金石,子孫萬年。牧馬牛羊諸僮,皆良家子,來如堂宅,但觀耳,無得刻畫,令人壽;無為賊禍,亂及子孫。明語賢人四海士,唯省此書,無忽矣!
這塊畫像“題記”告訴我們,這些畫像石是為緬懷和紀(jì)念一個(gè)名叫“安國(guó)”的地方小官所建的祠堂創(chuàng)作的,是記錄歷史事件所用,因而所有觀看的人都應(yīng)敬重它,如此則得到好報(bào),否則會(huì)禍及子孫。可見石畫像是神圣而威力無邊的,當(dāng)然,這種神力在拓印和裝裱之后自然就消失了。因此拓印也是一種藝術(shù)再創(chuàng)造,它使“神跡”轉(zhuǎn)變成了審美對(duì)象。因?yàn)樵谥袊?guó)美術(shù)史中,在現(xiàn)代化時(shí)期以前沒有油畫和水彩等具有較強(qiáng)“再現(xiàn)”表現(xiàn)力的藝術(shù)手段,因而拓印石像和石刻成為中國(guó)藝術(shù)中一種十分獨(dú)特而重要的表現(xiàn)手法和技術(shù),它使對(duì)歷史事件的再現(xiàn)成為可能。湯瑪士·雅可比選擇拓印的方式來再現(xiàn)和表現(xiàn)中國(guó)的歷史和文化,的確是很有創(chuàng)造性和文化眼光的。
石頭是自然材料中十分堅(jiān)硬的物質(zhì)材料,但時(shí)間和歷史仍然會(huì)作用于畫像石、石刻等,使其呈現(xiàn)出歷史的滄桑,并向我們言說某種“存在”。因此在中國(guó)文化中,拓印就成為一種手法和媒介,它是在我們和歷史之間的一個(gè)中介、一個(gè)翻譯者、一個(gè)傳達(dá)者,它使歷史的無言變得可以聆聽。湯瑪士·雅可比用拓印的方式,但拓印的不是畫像石、書法石刻等人工制品,而是拓印歷史的“物品”,和遺跡,這就使他的拓印不同于一般的復(fù)制而成為一種藝術(shù)創(chuàng)作,對(duì)我而言,現(xiàn)在的問題是,,這種手段表達(dá)的是一種什么樣的美學(xué)觀念,傳達(dá)一種什么樣的審美效果呢?
首先我們看看用傳統(tǒng)拓印手法對(duì)物質(zhì)原件和歷史遺跡的拓印,與對(duì)畫像石、石刻的拓印有什么不同。湯瑪士·雅可比的拓印包括當(dāng)年福州“德園”院子門樓上“德園”兩個(gè)字的拓印、“德園”
建筑內(nèi)地面的拓印、搓衣板的拓印、院內(nèi)殘留的宣傳標(biāo)語的拓印,以及石頭上各種動(dòng)物化石的拓印等等。通過對(duì)歷史殘存物品的拓印,湯瑪士·雅可比將這些已經(jīng)被歷史過程淹沒和沖刷掉的“存在”以形象的方式重新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給觀眾帶來視覺上的沖擊和心理上的懸念:這些是什么?這些東西與中國(guó)的過去和現(xiàn)在是一種什么樣的關(guān)系?
在中國(guó)的福州,“德園”仍然存在,雖然因?yàn)樗臍v史重要性對(duì)于一般的市民不是很大而沒有列入福州市的歷史文化保護(hù)遺址的范圍之內(nèi),但它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存在著。湯瑪士·雅可比對(duì)“德園”感興趣自然首先是因?yàn)檫@里曾經(jīng)是歐洲人居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其次,也許還因?yàn)椤暗聢@”以特殊的方式表征和呈現(xiàn)了中國(guó)近代以來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特殊性和復(fù)雜性。可以同樣說明問題的是湯瑪士·雅可比“德園”系列的另一幅作品,這幅作品源于對(duì)一件木制日常生活用品的拓印。搓衣板是中國(guó)社會(huì)現(xiàn)代化之前大部分中國(guó)家庭中都有的日常生活用具,用于搓洗衣物,它是與漢畫像石、碑刻等完全不同的日常生活用品。隨著洗衣機(jī)的普及,搓衣板已退出中國(guó)人的日常生活,僅僅在語言遺跡等文化形式中殘存,一個(gè)例子是北京奧運(yùn)會(huì)閉幕式之后關(guān)于籃球明星姚明是否會(huì)回家“跪搓衣板”議論。湯瑪士·雅可比對(duì)歷史殘存物的“拓印”類似于人類學(xué)家的“田野調(diào)查”,可以把失落了的過去的“存在”和被塵封的“記憶”重新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成為我們思考、反思中國(guó)現(xiàn)代化的一個(gè)標(biāo)本和參照。
在美學(xué)上我更感興趣的是湯瑪士·雅可比2007--2008年創(chuàng)作的仍然題名為“德園”的作品。這也是一個(gè)系列,但作品不是具象式的拓印,而是用中式掛幅,用來自中國(guó)歷史遺址的破磚碎瓦研磨成粉作為作品顏料,用類似于潑墨的大寫意的方式所創(chuàng)作的作品。這一組作品所營(yíng)造的意境以現(xiàn)代藝術(shù)語言的形式,把古老中國(guó)文化中那種“豐富性的簡(jiǎn)樸”和“空白性的豐盈”很好地呈現(xiàn)和展示出來了。用這種既不是自然的又不是人工的顏料進(jìn)行寫意性涂抹而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作品,把藝術(shù)家的思想、情感、價(jià)值評(píng)價(jià)等與具有^類學(xué)現(xiàn)場(chǎng)感的物質(zhì)材料結(jié)合起來,其作品簡(jiǎn)樸而獨(dú)特,從中我感受到了這位藝術(shù)家對(duì)中國(guó)歷史和文化的理解以及獨(dú)具個(gè)人風(fēng)格的藝術(shù)“再現(xiàn)”。
作為一個(gè)中國(guó)學(xué)者,此前我的確看不懂西方繪畫中的簡(jiǎn)約主義,那種用十分簡(jiǎn)單的色塊構(gòu)圖創(chuàng)作的美術(shù)作品。看不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許是我的藝術(shù)修養(yǎng)還不夠,也許是因?yàn)槲覀冞€不熟悉這種藝術(shù)語言和藝術(shù)形式的經(jīng)驗(yàn)基礎(chǔ)。但湯瑪士·雅可比的作品“德園一號(hào)”(2007年)卻讓我沉思良久并感受到某種東西。在這幅作品中,所有的“中國(guó)元素”都經(jīng)過了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換,或者說所有的藝術(shù)符號(hào)和語言都被思想的批判所仔細(xì)地洗刷過,只留下了似乎純粹但卻充盈著韻味和意義的簡(jiǎn)單形式,就像電影已經(jīng)結(jié)束但仍然持續(xù)著的音樂,純粹而又意味深長(zhǎng)……
在曼徹斯特工作和生活期間,我兩次參觀了“工業(yè)與技術(shù)博物館”,數(shù)次參觀了曼徹斯特美術(shù)館和“中國(guó)藝術(shù)中心”。曼徹斯特和利物浦作為全世界工業(yè)革命的發(fā)源地的大量史料和當(dāng)年的遺址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此外,讓我感興趣的還有德國(guó)思想家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這里生活并在這里醞釀了《共產(chǎn)黨宣言》的寫作,在馬克思當(dāng)年讀書的地方我很興奮地“留影”。現(xiàn)在德國(guó)藝術(shù)家湯瑪士·雅可比關(guān)于中國(guó)文化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也在這里完成并展出,在我看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2008年4月在曼徹斯特開幕的“首屆亞洲藝術(shù)三年展”上,我看到一組中國(guó)藝術(shù)家陳劭雄的作品,題名為“集體記憶·城市風(fēng)景”,是兩幅用人的指紋組成的大幅中國(guó)畫,畫面分別是北京的圓明園遺址和曼徹斯特市政大樓的形象,展示了一種歷史的記憶和情感的邏輯,這是許多當(dāng)代中國(guó)人所熟悉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邏輯。相比較而言,湯瑪士·雅可比的“德園”系列作品也呈現(xiàn)了一種歷史的記憶和情感的邏輯,在我看來,這卻是許多中國(guó)人所不熟悉的另一種歷史記憶和情感邏輯,但顯然不同于“集體記憶·城市風(fēng)景”。這兩種記憶和情感邏輯無疑都是真實(shí)的,都與我們的某一部分生活經(jīng)驗(yàn)相聯(lián)系,但是卻標(biāo)志著我們對(duì)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的不同的理解,作為一個(gè)現(xiàn)實(shí)中的個(gè)體,我們是否應(yīng)該學(xué)會(huì)聆聽這不同的藝術(shù)向我們傳達(dá)的信息和聲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