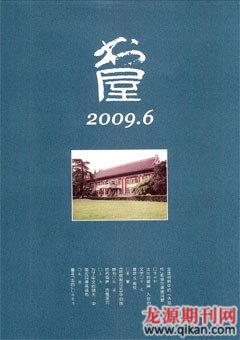關于“孩子的教育”
韓一宇
通常意義我們會以為,對于孩子來說,怎么會有什么哲學思維呢?可是美國的加雷斯·皮·馬修斯的研究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他告訴我們“許多人在孩提時代就已經在運用哲學了”。他的任務就是要糾正這個偏見,“就是引導學生重新進行他們曾經喜愛過而且是被認為與生俱來的一種活動,不過這種活動后來為適應社會生活需要而放棄了”。馬修斯“沉浸在對兒童的哲學思想的深思苦索后,就發現這個主題是多么迷人,而且發現它還吸引了課堂內外的人們”,因此他開始闡述他的觀點,“從事一些非正規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并且搜集他人的反映和想法,其中有哲學家和非哲學家、家長、教師以及其他喜歡孩子的人”。
長期以來,我們漠視了兒童心靈的豐富性,我們以成人世界并不成功的人生經驗、終不知是否正確之故的成見、習以為常的心理習慣去迫兒童就范。現代教育的悲劇就在于它的赤裸裸,帶著功利的好惡,要像調教狗一樣調教人。馬修斯認為這是人類的愚昧和偏見。例如他在自己的《哲學與幼童》里首先舉例:一個哈蒂姆的六歲孩子,偶然在吃了一樣從未吃過的好東西后,就不可思議去問:“媽媽,請您告訴我,我今天為什么會吃到這么好吃的東西,這是不是在夢中?”但母親不僅無論如何說服不了孩子,而且還會固執地認為這是不成其為問題的問題;而孩子經過思索說:“媽媽,看來這不是在做夢,因為我會在夢中問我自己是在做夢么?”不管孩子解決了這個問題沒有,在馬修斯看來,這就是孩子的哲學思維:好奇、沖動、提出問題,并試圖解決問題——符合所有哲學思維所具有的程序與品格。亞里士多德說過,哲學起源于懷疑和好奇。英國哲學家羅素告訴我們,哲學即使不能解答我們所希望解答的許多問題,至少有提出問題的能力,使我們增加對宇宙的興趣,甚至在日常生活最平凡事物的表面現象下,看到事物的新奇與值得懷疑之處。維特根斯坦則說:“哲學家的行為經常與小孩的行為差不多。小孩在一張紙上胡寫亂涂后問大人:‘這是什么?——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大人曾幾次給小孩畫圖畫,然后說:‘這是一個人,‘這是一幢房子等等。后來小孩又涂畫了一些符號,問道:‘那么這又是什么?”用我們東方思維來說,這同樣是一個有趣的人生哲學問題,因為這個孩子等于演繹了一個類似于“莊周夢蝶”的故事。莊周不是在夢中問自己,究竟是蝴蝶變成了莊周,還是莊周變成了蝴蝶嗎?笛卡爾在他的《沉思》里,也曾經為辨別夢還是生活頗費躊躇。對于這個故事,博爾赫斯同樣感到驚異,他在《博爾赫斯談藝錄》里,就曾經質疑,為什么莊周會夢見蝴蝶?為什么夢見的是蝴蝶而不是汽車呢?這顯然是個很可笑很無用的問題。是啊,這是多么可笑的幼稚的問題!但是,哲學思維就這樣與生俱來地啟動了。接著這個孩子又給母親提出了更加荒唐離奇的問題,“請問媽媽,人長著一張嘴,只能吃一種東西;為什么人長著兩個眼睛,卻不能看見兩個媽媽呢?”——除去生理學的角度,誰能說這不是和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列特提出的“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的命題相似呢?
孩子的哲學思維是心靈的、美學的。孩子的思維具有成人世界難以想象的超常性和詭異性,因此我們有必要充分注意理解、尊重兒童的這個思維的特點并和他們去耐心地對話。馬修斯指出,兒童的哲學思維主要表現為“陣發性”的、生動的“簡短的生活軼事”;但也不排除孩子哲學思維關注的“持久性”和“堅毅性”。在討論哲學與幼童時,作者便充分注意到了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放過在孩子生活的任何細節處去搜尋有趣的例證。在不足八萬字篇幅的著作里,馬修斯討論了“困惑”、“游戲”、“推理”、“故事”、“幻想”、“焦慮”、“純樸”、“對話”等九個和孩子哲學思維息息相關的問題。
《世說新語》肯定不是一個討論兒童與哲學思維的著作,但也無意識地講到了哲學思維和幼童相關的趣事佚聞。說晉元帝司馬睿很喜歡自己的兒子司馬紹,即后來的晉明帝,有_天長安來了一位客人,晉元帝為炫耀兒子的聰明,就問兒子,你能告訴客人是太陽遠還是長安遠嗎?兒子說當然是太陽遠。元帝問何以故?兒子回答說,因為看到了長安來的客人,卻沒有看到從太陽來的客人。第二天晉元帝故伎重演,問兒子太陽和長安到底哪個更遠,沒想到兒子卻出爾反爾回答是長安遠,晉元帝驚詫問何以故?兒子回答說,因為我們抬頭就可以看見太陽,卻無論如何看不到長安。正是由于看到了孩子心靈世界的博大,明代的李贄提出了“童心說”,在宋明理學法網恢恢的時代,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偉大創見。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的一生如果有過慧眼,那就應該是孩提時期。可川端康成固執地認為,是“臨終的慧眼”。如果這不是別有用心,就是企圖為他的自裁找一個自圓其說的理由。《哲學與幼童》是一本啟人心智的著作,作者用大量有趣生動的案例告訴我們,兒童與生俱來擁有運用哲學的能力。他/她們天真純樸的心靈對于萬有的宇宙和人生所萌發的種種匪夷所思的疑問、困惑,“都含有探索真理的意味,符合深奧的哲學原理”。譯者陳國容說:“《哲學與幼童》一書,是由錢鐘書先生推薦給三聯書店的,我榮幸地接受了三聯書店給我的翻譯工作。”作為智者的錢鐘書為什么會推薦這部書呢?這里是否隱含了推薦人育兒經歷的經驗總結,抑或失敗教訓的自責與懺悔?我們自然是不得而知的。但在楊絳先生的《我們仨》里,卻有這樣一段不著痕跡的育兒過失的檢討:“姐姐妹妹都怪我老把圓圓抱著攙著,護著孩子失去了機靈。這點我完全承認。我和圓圓走在路上,一定攙著手;上了電車,總讓她坐在我身上。圓圓已三四歲了,總說沒坐過電車,我以為她不懂事。一次我抱她上了電車,坐下了,我說:‘這不是電車嗎?她坐我身上,勾著我脖子在我耳邊悄悄地央求:‘屁股坐。她要自己貼身坐在車座上,那樣才是坐電車。我這才明白她為什么從沒坐過電車。”
人類可以登月,可以克隆,可以制造傻瓜相機,但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發明過傻瓜人生,甚至即使以后也不會有所謂的哲人敢斗膽去撰寫《人生指南》一類的教科書。可是這并不影響我們對于人生的探討。澳大利亞的安德魯·馬修斯是位傳染快樂的人,他為孩子們寫了《做個快樂少年人》。這是一本把“形而上者謂之道”的幼童哲學思維培養,轉化為“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可操作的人生話題演練。這樣看來,兩個馬修斯的著作為我們提供一個“道”與“器”互補的例案。天下為人父母者,若無奢望培養孩子成為一個精神貴族,而愿意培養孩子擁有一個平凡、有用的快樂人生的話,那就有必要讀讀《做個快樂的少年人》。安德魯·馬修斯的嘗試是成功的,例如有些事實就擺在你的面前:一個十歲男孩,他的寶貝就是足球,足球就是他全部生活的內容,他抱著它睡覺、吃飯。他對于與足球相關的世界無所不知,但對于嬰兒來自哪里卻從來沒關心過。有一天下午,他丟失了足球,到處尋找卻找不著,他疑
心肯定是被人偷了。最后他看見一位女士,她好像把他的足球藏在外衣里面,他怒氣沖沖上去質問:“你干什么把我的足球藏在你衣服里面?”當然,不是她拿走了他的足球。不過,這天下午這個男孩總算知道了嬰兒是從什么地方來的以及十月懷胎的女人的樣子。誰說人生不能彩排,馬修斯的研究告訴我們,一次性的人生也是可以預演或彩排的,然后再正式粉墨登場。如每個童年所有的游戲,都是對于成人世界的模仿,從游戲程序到游戲規則的設計,無不具有成人社會的儀式,因此孩子的游戲,莫不是對成人社會生活的提前演練。
在這本為孩子們量身定做的書里,這樣討論孩子的教育,我們不僅找到了輕松,而且也找到了行之有效的方式。例如,我們也可以說孩子快樂教育的最基本的訓練應該是生活態度。如果生活常常是給予,那也許是另一回事;問題是我們經常生活在逆境中,或者,我們經常是失敗者。假如“你申請了一份兼職,他們卻聘用了你的朋友;你新買了一輛車,在一星期內卻被偷了;或者,你愛上了隔壁的男孩,他卻愛上了對面街道女孩”,你很容易產生這個世界和你過不去的感覺。我們該如何改變自己懊惱的感覺呢?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人采取所謂“屢敗屢戰”的方式,但這樣處理的方式是不是把生活描繪的太悲壯了?還有一種是“生活就像一面鏡子,你對它笑它就笑,你對它哭它就哭”的說法,這樣的黑色幽默等于把生活比成了哈哈鏡,而讓自己扮演了一個小丑的角色。而馬修斯認為,“關鍵不是發生了什么,而是你怎么樣去處理它”——“案例一:我的朋友約翰·福佩天生沒有手臂。他獲得了傳播學碩士學位,還到世界各地的公司和學校去演講。他從來都不會問:‘為什么我天生就沒有手臂?他只會問自己:‘我可以怎樣去克服它呢?”對于一個失敗者,或對于逆境中的生活實在沒有更好的靈丹妙藥,惟有你如何積極地面對它。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也曾從反面講過一則如何面對失敗的故事:從前有個臭棋簍子,和人下棋每下必敗。為此他向神仙求助下棋必贏之法。神仙告訴他:我沒有必贏之法教你,但可以教你必不輸之法,那就是你以后別再和人下棋了,這樣你肯定就不會輸了。我們都知道《阿甘正傳》里的阿甘吧,他不光腿不方便,而且只有常人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五的智商,但他有百分之百的情商,有稚拙到幾近圓滿的良心道德,在他的母親的呵護下,經歷了殘酷現實生活的錘煉后,他居然長成了大樹。
人生的形式常常是以這種積極自助的方式來完成的,如馬修斯稱之為“積極思想”對孩子的幫助:想象你坐著巨型客機飛往歐洲,機翼的一個引擎掉了下去,你希望機長會有什么反應?你會不會希望機長說:“保持冷靜,扣好安全帶!飛機有點搖晃,但我們會安全著陸的?”反者,你還是希望機長在客艙過道上來回氣急敗壞地尖叫著:“我們全都死定了?”——你想想,哪個家伙有可能讓你安全著陸?“現在,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你就是你的機長”,你就是自己的上帝。如果你生在森林里,你只有一把斧頭,一個指南針,一把堅果和漿果,你就可以出發了,即使生命的羅盤早已指錯了方向,你不僅可以披荊斬棘穿過樹林,你還可以學會與動物相處。
兩位馬修斯的教育思想,與我們經世致用的教育思想相去甚遠。我們的教育不是著重于教人做人,就是實利地活學活用、立竿見影。家庭的教育是望子成龍功利心過重,學校教育是要為國家制造出一批批永不生銹的螺絲釘,在你拉我扯的爭奪中,我們較少想到孩子心靈的正常發展。應試教育是防錯教育,難以容納孩子天真詭異的思維;誰能說我們讀著《半夜雞叫》的課文長大,就能培育出一顆溫柔善良的心靈呢?如果我們多發現孩子們的心靈,不再去“教育孩子”,而是理性地開始考慮關于“孩子的教育”,那樣,事情是不是會好一些,或者說我們會有一個好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