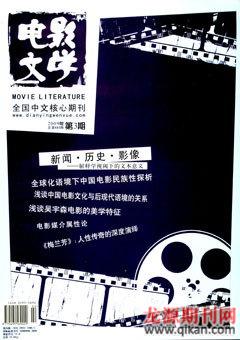淺談中國電影文化與后現代語境的關系
楊 杰
[摘要]后現代文化是與當代社會的高度商品化和高度媒介化聯系在一起的,這種文化是一種對世界的意義深感不信任的文化。電子媒介的迅速發展也是產生后現代文化的社會背景。但在中國的娛樂性商業電影中,后現代性卻是和主流意識形態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人類傳媒手段的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語言階段、文字階段、印刷階段和電子傳媒階段。本文從后現代語境、電影的后現代性和后現代主義幾個方面闡述了兩者的關系。
[關鍵詞]后現代,語境;電影文化
一、后現代語境
電子媒介的迅速發展也是產生后現代文化的社會背景。人類傳媒手段的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語言階段、文字階段、印刷階段和電子傳媒階段。電子傳媒的重要特點就是用圖像符號替代了非具象性的符號,由于它用具像直接作用于人的視覺,消除了人們的知覺與符號之間的距離,因而也消除了文字那種需要通過接受教育才能理解的間接性,消除了從符號的所指到能指之間的思維過程。電子傳媒的這一“優勢”使它不僅替代了印刷媒介的權威地位,而且迅速地影響到人們的行為方式和生活習慣:人們越來越滿足于不假思索地接受外來信息,越來越迷戀于直觀的復制形象而不愿意進行個人的閱讀或思辨,越來越關注流動的現象而不是恒定的主體,于是正如著名社會學家戴維·恩斯曼在他的《孤獨的人群》中所指出的那樣,后現代社會是一個由“他人引”的社會,傳媒滋生了一種“從眾心理”,因而后現代文化也是一種大家公有、共享的高度平面化的文化。
后現代性文化是后現代文化的主體,也是后現代社會的文化市場的主要商品,因而它必須滿足消費者直接的實用目的,必須以批量生產的方式來迎合消費者的需要。這是一種平面性的文化,它既不需要通過對現實境遇的揭示來喚起人們對自己的真實處境的覺悟,也不需要通過對某種烏托邦理想的期望來引發人們的實踐熱情,任何深度的出現不僅沒有必要,而且往往有可能擴展文化品和消費者之間的距離,從而影響到它的商業價值。而后現代語境,正如利奧塔德所說,則是一種精神,一套價值模式。它表現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論、解“元話語”、解“元敘事”。它用價值顛倒、視點位移、規范瓦解、種類混淆等修辭手段來消解一切恒定的常規、秩序,來表明它自身的不確定性,它用反諷和玩笑來揭示所有既成的對世界的解釋的人為性和虛假性,但它卻并不想用新的闡釋系統來取而代之,它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個浪跡天涯的自由的流浪者,沒有家園的快樂的單身漢。
二、后現代性:電影游戲
20世紀80年代后期,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電影廠走向了企業化,迫于巨大的經濟壓力,中國的電影制作者不得不意識到電影并不僅僅是一種藝術,甚至主要不是一種藝術,而是一種需要獲得經濟效益的工業產品,因而他們只能忍痛割愛、委曲求全,暫時放棄自己的藝術追求,藝術個性,勉為其難地拍攝所謂的娛樂片。三十多年來,中國第一次出現了關于電影的“娛樂性”的討論。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人們的電影觀念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第五代”導演的中堅之一的田壯壯在他的《搖滾青年》中率先宣布:“怎么開心怎么來”,當年“為下一個世紀的觀眾拍電影”的豪言壯語變成了一種堂·吉珂德式的笑話,電影不再追求“第五代電影”那樣的個人風格,也不再迷戀于那種烏托邦式的人文理想,而是要讓盡可能多的觀眾感到愉悅、暢快,電影不再是一種美學創造,而是一種能滿足大眾無意識夢想的“實用”消費品。于是,“第五代”電影人紛紛改弦易轍,田壯壯拍攝了充滿一種浪漫情懷的青春影片《搖滾青年》,張藝謀拍攝了反劫機的驚險片《獵豹突擊隊》,何群則從《西行囚車》到《烈火金剛》,直到《消失的女人》,一直在樂此不疲地拍攝著商業性的情節片。娛樂性影片很快成為數量上的主體。而這種電影觀念的轉變還并不僅僅是因為電影受到商品邏輯的支配,而且也因為人們對所謂的美學深度已經深感懷疑,當人們把這種深度嘲笑為故作深沉時,他們為那種后現代的平面已經開辟了道路,于是,電影終于名正言順地成為一種電影游戲:它消除了時間感,排除了歷史意識,它也割斷了與現實的真實性聯系,而成為一種自成體系、自我封閉的游戲文本。
后現代文化是一種對世界的意義深感不信任的文化。但在中國的娛樂性商業電影中,后現代性卻是和主流意識形態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如果說,西方商業電影是以對主流觀念的一種有限的偏離來釋放觀眾的弒父情緒的話,那么中國電影則是通過對主流觀念的有意識的認同來淡化它的精神分析功能。從1989年的《龍年警官》開始,商業電影“主旋律”化就成為了一種有效的敘事策略而被采用。《焦裕祿》成功地將一個共產黨人塑造成為了一個高度倫理化的忍辱負重的傳統人格,使這一策略的潛力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但是,任何主流觀念都意味著對想象界的一種抑制和規范,都企圖為那個展示著快樂原則的電影游戲賦予一種意義和一種深度,而這與商業電影的運作機制并非沒有矛盾。蹣跚在商業化和主流化雙重軌道上,這種“一仆三主”的現象,也許正是中國電影的一種后現代特征。
三、后現代主義:游戲電影
后現代性文化是商品經濟的直接現實,它通過文化游戲來牟取暴利。而后現代主義文化則是對后現代社會的價值體系和生活方式的話語表述,它通過游戲來拆解深度和意義。對于中國來說,后現代主義文化并不只是一種舶來品,它的滋生與中國社會所發生的變遷有著密切聯系。新時期剛開始,不到十年,人文主義旗幟就在商品經濟的滄海橫流中風雨飄搖。價值觀念的頻繁位移,暴露出了所謂“永恒”真理的“永恒”性只不過是對其“暫時”性的一種策略性掩飾,任何關于世界的認識和闡釋,都是人為的,都隱含著某種意識形態動機。我們面對的并不是一個本原的世界,而是一個被符號化的意義化的世界。正是基于這樣的覺知,后現代主義對神圣性、秩序、常規、傳統,甚至一切概念、符號都深感懷疑,它不僅懷疑浪漫主義的烏托邦,懷疑現實主義的真實性,甚至也懷疑現代主義所包含的各種劇烈的感情:焦慮、孤獨、無法言語的絕望和形而上的追問,我們不能走得太遠,這樣會致使我們去猜測。于是,對深度的拆解、消解,就成為后現代主義的典型特征。
這種后現代主義觀念在蘇童、余華。池莉、方方的小說中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表述,而電影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它對后現代主義觀念的表達則不得不更加隱晦,更加具有某種策略性:它必須意識到它對深度的拆解只能在一定的限度中和一定的限制中進行。因此,中國幾乎沒有完全意義上的后現代主義電影,但中國電影中卻已經表現出了后現代主義的消解性特征。
這種特征最突出地表現為它常常通過否定自己賴以生存的社會和文化網的正統性和合法性來與這種狀況對立,它把這張網看做是某種偶然性的產物。它對為現狀提供永恒性解釋持懷疑態度。它否定正義和理性的形而上學概念、否定以對善與惡的機械劃分或以簡單的因果邏輯關系為基礎的對于世界的解釋。1987年,根據王朔小說改編的《頑主》最早對光怪陸離的社會現實作了一種玩世不恭的解釋。周小文在《瘋狂的代價》中用小女孩那無所謂的泡泡吹破了姐姐孜孜不倦的復仇行為的意義。特別是近年來一批城市幽默喜劇,如《大撒把》、《上一當》、《站直羅,別趴下》等影片,對種種人們習以為常的價值觀念、倫理觀念、社會觀念和歷史觀念作了調侃式的嘲諷。而《三毛從軍記》則大量采用了反諷、戲擬、類型混雜、滑稽模仿和“元敘事”等解構手法,不僅對歷史、戰爭、英雄作了重新解釋,而且也對電影作了重新解釋,從而暴露了這些解釋的“非必然性”和其意義的“非真實性”。
后現代文化所受到的最激烈的批評往往來自于它的與工業化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千篇一律的“復制性”。本杰明指出,電影、電視、廣播等電子傳媒的出現,意味著不僅是對物質的復制也是對于精神的復制,“復制技術把所復制的東西從傳統的領域中解脫了出來,由于它制作了許許多多的復制品,因而它就用眾多的復制物取代了獨一無二的存在。”的確,后現代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種復制的文化,它不僅是可以復制在膠片、磁帶、激光唱盤上的批量生產的商品,而且它的類型、風格、模式,甚至語言也是復制出來的。它日復一日地為人們提供著各種大同小異的流行文化,個性、創造力、批判熱情、現實精神都消失殆盡。人們當然會擔心:在一個喪失了首創性和懷疑精神的社會中,我們的生存、發展,靠什么來得到保障?在我們突然面對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困境時,我們是否還有從容處理的能力和意識?當我們放聲譏笑著普羅米修斯之后,還會有誰再愿去盜來圣火?當后現代文化在商品經濟的大潮裹挾之下橫掃著我們的電影和整個社會時,保持幾分清醒和冷靜也許并非沒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