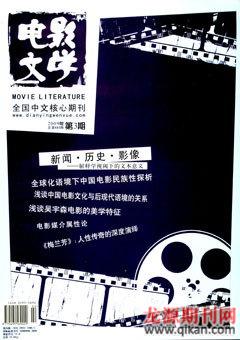當代好萊塢災難片中的生命意識
鐘 蔚
[摘要]好萊塢的災難片表現了“天人對抗”的模式,與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有著本質的區別,也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文化心理。這一模式可分為自然災難型與人為災難型,兩種類型的影片盡管在內容等方面有著種種區別,但都共同反映了制作者對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的思考。影片中分外渺小卻自視甚高的個體對于自然界瘋狂的掠奪終招來走向毀滅的恐懼。由此,影片同時也暗示了對理想的生命倫理的模式乃在于人對自然的敬畏態度。
[關鍵詞]好萊塢災難片;生命,恐懼
一、“天人合一”與“人定勝天”
自從出現了人類,便有了人與自然的密切交往。人類在自然中求生存,與之和睦相處或反目成仇。自然真實的面目究竟如何,這是人類始終無法窮盡的。在中國古代,人們對于不可知的“天”的敬畏,促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的生成。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無論是主張“入世”還是“出世”,其實都具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即十分看重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這種“合一”,是以敬重自然的崇高地位為前提的。儒家雖不如道家那樣將人的活動置于自然運動的法則中去加以約束,卻也對自然敬畏有加,許多感世傷懷的文人墨客,均在對自然的詠嘆中寄托了自己的情懷。在古代文化中,“天”所代表的自然界及超驗的世界永遠是高懸于人們頭頂上的神秘天地;而所謂的“天人合一”,也并非僅僅是道家“法自然”的觀念,而是深入到國民文化心理中的普遍的信念。對于道家來說,“天人合一”意味著人對天道的順應,其前提是將人視為天道系統中的一個微不足道的組成部分,人的成長,猶如其他生命的生長,也都體現著天道運行的規律。
相比之下,在西方人的傳統文化中,“天”卻是一個外在于人的客體。在天一人的關系中,人才是掌握能動性、主動權的主體。在希臘神話的諸神身上,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這種主體與客體分離的狀態:在這些神的身上,世俗人性的分量大大超過了天國的神性。他們對情欲的放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的生命個體無所顧忌的狂歡。而作為這一對立面的神性,強調的是節制與理性,但這樣的精神追求卻常常被諸神的世俗性所掩蓋,陷于被揶揄、遮蔽的被動地位上。這種天人分離的觀念在后來西方科學理性盛行的時代里,曾被發展為。人定勝天”的樂觀思想,達爾文的進化論無疑充滿信心地向世人展示了一個歷史不斷進步、勇往直前的美好圖景。
在被大眾喜聞樂見的西方好萊塢電影中,同樣反映了制作者對這一命題的思考。
從上個世紀70年代相繼出現的好萊塢災難片,因其宏大的場面,驚險的情勢加以愛情、友情等無處不在的細膩情感常演不衰,充分說明了好萊塢災難片的獨特魅力。一直以來,《大白鯊》及其眾多續集以其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緊張的氣氛吸引了眾多的觀眾,而后來的《未來水世界》(WaterWorld,1995)、《烈火狂峰》(Dantes Peak,1996)、《大海嘯》(Tsunami,2004),《后天》(The Dayafter Tomorrow,2004)、《華氏911》(Fahrenheit9·11,2004)等一系列大片借助現代電影數碼影像,實行天馬行空的想象力,讓觀眾身歷其境地體現逼真震撼的災難場面。當這類影片在全球上映的時候,也無不引起轟動,追捧者趨之若鶩。對此,如果僅僅將原因歸結于商業運作的成功,則是一種淺嘗輒止的做法。筆者要深究的是:在這些災難片迎來一片叫好聲的背后,隱藏著制作者及觀賞者怎樣的心理呢?
二、天人對立
好萊塢災難片盡管懸念迭出、情節緊張刺激,但其中矛盾的對立卻顯得較為簡單:它往往表現為某種二元對立的模式,總的來說,是人與自然的對立。自然能給人們提供舒適的生活環境,但是一旦人們對它的索取超過了必要的限度而形成掠奪,那么人類也將因此而受到自然環境的嚴厲懲罰。而且,在災難來臨的時刻,在生與死的危急存亡關頭,恰恰是最能體現出人性美丑善惡的良機,這同樣也包含著對人性各種內涵進行比較取舍的二元對立模式。
這一模式在影片中具體表現為以下幾種類型:
首先,是自然災難型的。這一類影片以人與自然的搏斗為主線,講述了地震、海嘯等來自自然界的重大災害,還包括來自海洋、陸地深處等的不為人所知的自然界怪物。在這些災難巨大的魔影下,人類的身影顯得十分渺小。人與自然搏斗的力量也顯得是那么微不足道。如《大海嘯》中沖上陸地后所向披靡,具有極大破壞力的狂濤駭浪,《烈火狂峰》中火山爆發時的驚天動地,《大白鯊》中超乎人們想象力的高智商鯊魚等等。人在它們面前,只有拼盡了全部的氣力與智慧,團結起來,方可死里逃生。
其次,是人為災害型的。這一類影片以人類“自作孽”為主題,想象了在一個經濟、科技水平高度發展的社會中,人與自然的對立造成的災難。如《后天》所講述的關于世界末日的科幻故事:溫室效應帶來的全球變暖,引發氣候突變——以美國為代表的世界各國,遭受到洪水、海嘯、冰雹、龍卷風和暴風雪的猛烈襲擊,氣溫驟降,冰期來臨,人類陷入了空前的災難之中。如果說《后天》給我們展現了全球變暖兩極冰雪融化給世界帶來的大災難的話,那么《未來水世界》則展現的是大災難之后地球的生態現象,人類將永遠陷入尋求陸地的攻伐戰爭的地獄之中。除此之外,近年來,由于美國“9·11”事件的影響,恐怖主義也被視為人為災難的元兇之一,如《華氏9·11》等。
通過對具體表現類型的剖析,可以使我們認識到:天人對抗是由于人類進度的經濟活動而引起嚴重的自然生態危機,是歸咎于現實中,人類傲慢地認為“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統治者與被統治的對象之間,形成了尖銳的矛盾。影片顯然對這樣的對立關系進行了顛覆,它們試圖要警示人從自然界進化而來,隸屬于自然界的事實。讓人類反省自己的破壞行為。
隨著對生態倫理的認識的改進,人類逐漸意識到自己在自然界中極為渺小的位置,認識到自己與他人,與其他形式的生命之間牽扯不斷而又難以控制的關系。也就是說,人類逐漸地發現了他/她失去了對自己的絕對主導權。人之個體實際不過是生命關系網絡中極微小的一個罷了。這種觀念表現在災難片中,便是人對周遭自然、社會的懷疑、猜測與畏懼感的表現。
在災難片中,當大自然發生改變的時候,人們是無能為力的,只能是忍耐和躲避,等候大自然恢復原有的面貌。如眾多“怪物”的出現,不管是來自自然的,還是來自實驗室的,都象征著人們對于不可知世界的困惑與焦慮。種種未知數匯聚成了編導對于災難即將來臨以及對其殺傷力無法進行預計的焦慮。
可見,無論這些災難片如何推陳出新,必然要有尖銳的對立雙方的存在,讓在現實中深感焦慮的觀眾獲得精神的解脫。這與中國“天人合一”的矛盾對立與融合的模式及其背后所反映的文化心理顯然有著本質的區別。
三、敬畏生命
災難片表現了對地球上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的哲學意義。災難意識是人之為人所特有的意識,是人類的一種永恒
的憂患意識。正是有了這種意識,人類才能在同災難的無數次抗衡中生存下來,推動著人類文明的前進。因此,災難片給予觀眾的,不止是當下,更多是指向永恒,不止是個體的心靈震撼和宣泄的愉悅,而且是人類眾生一體永恒的思考和對生命力的體悟。災難片可以看出人們內心對于環境破壞、自然災難等方面的潛在擔憂,呼喚人類保護環境,促進社會和諧,遠離戰爭和災難。這就是此類影片的悲劇審美價值和現實意義。
西方許多學者總在不停地思考著這一“生命倫理”的問題。提出在人以外,對所有生命形式的“敬畏”:“由于敬畏生命的倫理學,我們不僅與人,而且與一切存在于我們范圍之內的生物發生了聯系。”“由于敬畏生命的倫理學,我們與宇宙建立了一種精神關系。我們由此而體驗到的內心生活,給予我們創造一種精神的、倫理的、文化的意志和能力,這種文化將使我們以一種比過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動于世。”這番話對于我們理解好萊塢災難片所要傳達的生命觀是具有重要啟示作用的。踐踏其他生命的結果將是毀滅自己。我們理應為現代人類貪婪的掠奪、殘忍的暴行而進行深深的懺悔。自然,理應使人類產生敬畏、而非無知的藐視。
這些災難片同時也深刻地表達了編導心中的末世情結,即人們心中對未來世界的悲觀絕望之感。災難傳達的是人們心目中深深的悲傷與恐懼。而對災難片的熱捧則反映了人們的悲劇審美心理。朱光潛先生曾說:“人們好像普遍期望幸福結局。悲劇不僅給人快樂,也喚起惋惜和憐憫的感情。這種惋惜和憐憫心情常常會非常強烈,以致威脅到悲劇的存在本身。人心中都有一種變悲劇為喜劇的自然欲望,而這樣一種欲望無疑不是從任何天生的惡意和殘忍產生出來的”,“恐懼只要不是太近地威脅我們,就是一種產生快樂的激情,而憐憫由于是生自愛和社會情感,所以是一種伴隨著快樂的激情。”這段話所給予我們的啟發是:在災難片的欣賞中,人們無意中傳達出他們的末世恐懼—通過電影載體,這種恐懼被升華為藝術作品,在逼真的畫面與觀眾之間形成了一定的“審美距離”。正是通過審美距離的作用,影片的制作者們成功地拉開了虛構與現實之間的距離,以使觀眾在欣賞的過程中非但沒有深陷于絕望的牢籠,反而獲得了審美的快感,即精神上的超脫。因此,當影片最后無一例外地出現了英雄勝利的喜劇性場面時,恰恰是滿足了觀眾在此類悲劇審美中的情感期待,最終俘獲了眾多觀眾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