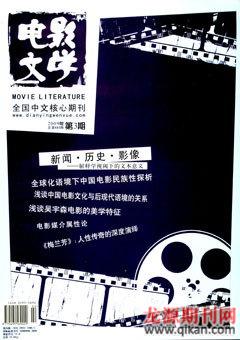微笑中的無奈與感動
陳建華
關注小人物的生存狀態,尋找大眾的認同點,這可以說是賀歲電影吸引觀眾的深層原因所在。尹鴻指出賀歲片用小人物的悲喜劇來喚起大眾認同,“其核心故事是小人物在轉型時代中的夸張而滑稽的掙扎、錯位以及不期而遇的一點溫情,最終將中國百姓在現實境遇中所感受到的種種無奈、困惑、期盼和憤怒都化作了相逢一笑,以笑來表現悲涼。以戲謔宣泄欲望,既提供娛樂消費快感又有一定現實指向”。雖然處于命運不可知的失措狀態,卻都沒有呈現悲劇結構,于是在詼諧幽默的主體氛圍和大團圓結局的預期中,使得觀眾給予主人公以真情關懷的同時達到優越的心理,才更適合成為觀眾俯視與共鳴的對象。通過這些小人物的喜怒愛樂,觀眾仿佛在銀幕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可以說賀歲電影仿佛就是觀眾審視自己的一面鏡子。賀歲電影的鏡頭真正承載了世俗平民的視角和觀念,并且以此來看待,甚至是批判現活及世事人生。于是在這樣的觀照與視角之下,各種人性欲望就在世俗的價值評判中,得到了真實坦率和從容自信的展現。
賀歲電影《桃花運》是好看的“桃花運”。導演把五朵桃花從她腦海里運到銀幕上,然后,開在觀眾心里。影片講述了五對男女的愛情故事,各色愛情饕餮,撲面而來:一個拜金的白領,一個失婚的母親,一個外冷內熱的婦人,一個有戀父情結的富家女,一個思想保守的“剩女”。這樣的五個女人,在某個時期集體走了“桃花運”:拜金女遇到了夢寐以求的大款,失婚女遇著了愛孩子又貼心的男人,婦人心甘情愿為一個騙子付出了一切。富家女在一個廚子身上找到了父親的味道,而“剩女”則碰上了一個剛認識沒多久就要求同居的開放男子……五個故事,五枚“桃花運”,穿插上演,節奏緊湊流暢,看起來也是輕松愉快的。這五個故事,它們彼此都以原生態存在于社會,聯系的紐帶就是“人”,形形色色,結局各異。現代社會的極端化表現就是這樣一個結果,導演把當下愛情生活的各個方面提純后再呈現給你,赤裸裸而又現實。
影片中經常呈現的含而不露的冷面自嘲,實際上是一種以退為進、賦予自身心理回旋空間的生存策略方式和柔性姿態,同時也以一種諧趣對正統話語和傳統道德進行了某種后現代的解構,因為嘲弄他者的同時也在嘲弄自我,實現了雙重解構,達到后現代主義的典型特征“去中心化、去立場化”。影片中拜金女的求偶標準——“三有一無男人”,有錢有房有車沒老婆,老處女對性生活的恐懼——“房間里好大一張床,什么都沒有!”絕望主婦的催促——“要采取措施么?”“安全!…剩女”的絕望吶喊——“世界不公平,怎么會丟棄這么多未婚男女?”……于是拜金、同居、熟女、剩女等時下社會生活里熱門敏感話題,就被辛辣而調侃地觸及,用沖突的故事和精妙韻臺詞讓人臉紅心跳的同時又若有所悟。“怕新鞋硌腳,特意用熱毛巾捂了一個晚上。”——殺死人的體貼,夠狠;“萬一是個機會呢?”——從葛大爺的嘴里說出來,怎么就有于無聲處聽驚雷的感覺,“總要全面了解之后才能更好地相處。”——真是道出了男人的心聲。這種發自內心的小人物的自嘲,消解了導演所設置的調侃和嘲諷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作者并不是為了表達一種與秩序的對抗,或者對現實的尖銳批判,而是在調侃中注入了一種溫情。但是這種調侃絕不是毫無深度的逗樂,而是能夠讓觀眾會心一笑的同時,又不禁贊嘆語言的精準絕妙與切入肯綮。雖然賀歲片中的主角對世俗的欲望表白直言不諱,但他們對于人生卻又都是自嘲的游戲態度。這也賦予了觀眾一種相對優越的地位,這一點恰恰把握了觀眾接受的一個重要心理契機,可以在日常世俗的層面,撓到民眾心理的癢處,撥動社會的敏感神經,從而在一種集體的自嘲、反諷的游戲快感中贏得效應。
從影片開篇開始,以梅婷為代表的大齡未婚“剩女”就翹起了心里愛的欲望,等待一個命中注定的男人出現,來解救自己快要日益萎縮甚至枯萎的愛情夢。“桃花運”在馬儷文的電影里不再是男人的專屬名字,也許女人比男人更渴望。也許經歷越多的女人,愛的容量也越容易膨脹。即便是因丈夫另有年輕貌美新歡而離婚的絕望主婦鄔君梅,也在葛優溫柔體貼的攻勢下復活了,淪陷了,說出了“愛情像得水痘麻疹,人人有份!我寧可當白癡,也不能終生無愛”這樣明顯桃花癥狀的話。當元秋一腳把不再關愛自己的“糟老頭子”踢下了床,也勇敢地把早已干癟無料的婚姻踢飛了。離婚對元秋來說不是一種恥辱和委屈,而是重獲自由和幸福的開始,于是便有了郭濤的登場。面對比自己年輕很多歲的郭濤,元秋也本能地在抗拒,即便是一個風華正茂的年輕女孩,也不太會相信青春不再的老女人還能獲得年輕男人的愛。所以當郭濤說出“愛與年齡無關”,“我就是喜歡年長的女人,有種母性的力量”時,我們用質疑的眼光審視著郭濤的一舉一動,而元秋更愿意以姐姐甚至母親的身份感受郭濤的接近與照顧。當郭濤的手機作響,謊稱別的女人時,元秋說:“去吧,你應該有個好歸宿,只要你把我這里當家就行”,看到這里,我真的為元秋心疼,明明她心里已經愛上郭濤,但她不愿意像一個熱戀中的小女孩一樣,用所謂的關系或者婚姻獨占他,只要能見到他,就已是愛的慰藉。當郭濤的“催債”電話一響再響,當一幫兇巴巴的老女人找上門來,我們都明了郭濤的騙局了,元秋又何嘗不是?但是她愛無法拐彎,歷經人生滄桑,還有什么能比為愛勇敢付出而幸福?……影片里的人物有著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命運,各段感情也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結局,雖然里面有虛榮也有欺騙,有功利主義也有機會主義,但我寧愿相信,其中的每段姻緣都是有真感情流淌其間的,無論起始于什么目的,終結于什么結果。
作為一部女性導演的作品,女性角色成為影片的主導力量,無論她們的個體是柔弱還是堅強,但總體來說,她們是影片的強勢主體。鄔君梅演的年輕媽媽,獨自撫養兒子,雖然艱辛孤獨,但她堅強支撐,后來得知葛優的騙子實質時,能夠把眼淚咽下,獨自面對肚子里的孩子慢慢長大的現實,小宋佳扮演的富家女,善良穩重,相信真感情,在愛情的道路上毅然接受了與自己差距懸殊的廚師男朋友;在《桃花運》里李小璐是個拜金女,為了追求富家公子使出渾身解數,看起來還頗為奏效,梅婷的角色是個古板的傳統乖乖女,由于拒絕婚前性行為而失去了海歸男友,但自己的原則始終是堅持住了;元秋的角色最是強大,很喜歡她一腳把前夫踢下床的舉動,足見此人的性格特征,但是待到“真情”來臨時,她凌厲的腿腳功夫全化作百般柔情,并且心甘情愿地讓自己并不寬敞的臂膀為那個小男人遮風擋雨。看看電影中的這幾個女性角色,可以說在《桃花運》里你可以找到關于愛情的多種理解和多種可能,如果你是位女性觀眾。可能體味到的會更多。
我們可以把《桃花運》中“離婚女人被婚騙所騙”“老女人被弟弟型男人騙”“富家女愛上窮廚子”“女白領愛上男上司”“剩女終于出嫁”五故事集合起來,看成是馬儷文對這個社會女人情感問題的基本判斷。如果撇開人物的年齡、身份、財富這些可以任意設計的東西,在馬儷文的鏡頭下,你會驚奇地發現,《桃花運》的五個故事非但是順著一個脈絡下來的,而且結尾驚人一致,都是女性為了拯救男性而不同程度地犧牲了自己:為了挽救失足中年人,服裝店老板變賣家產,為了幫富二代度過經濟危機,小白領放棄了原來的工作,為了被開除的廚師重新上崗,真正的大老板干脆暴露身份;耿樂最終接受了“先婚后性”的觀念,也算是面對傳統道德的浪子回頭,而葛優與鄔君梅的故事明顯沒完,因為葛優在商場接到電話時,雖然他沒接,但顯得心事重重……
這就是《桃花運》最有意思的地方,從頭到尾都是女性視角,但卻一點都沒有那種張牙舞爪的女權主義。它只是含情脈脈但又斬釘截鐵地說出這樣一個事實:女人很挑剔,但是她一旦認準,就會一條道兒走到底。相比在戀愛初期熱火朝天的男性,女性所有的能量都是為戀愛乃至婚姻儲備的。
導演馬儷文在《桃花運》里細膩、溫情得像一個夜歌者,音調舒爽,節奏適中,把一部其實希望在商業上有所斬獲的電影“搗持”得好看又不失“品”。有人也許會覺得這五個事例并不新鮮,但我理解,其實刻意過濾掉很多過于時髦的展現模式,她挑選、剪裁的這五個斷面,已足夠有代表性,讓觀眾在會心一笑的同時,能明了編導的想法,能感受到導演從內而外濃烈的文藝份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