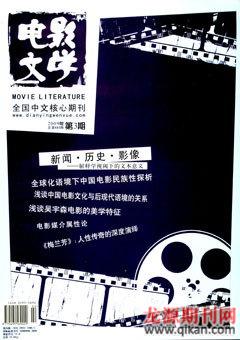賀歲片,請亮出你的喜劇性
粱 華
考慮到新年和春節的喜慶氣氛,賀歲片的風格多為輕松、幽默,具有強烈的觀賞性和娛樂性,一般有“令人發笑”的要求,尤其是冠以“喜劇”的賀歲片。喜劇性成為賀歲片的鮮明特點。只是說電影是藝術,即便是娛樂性質的喜劇片,也是藝術,把喜劇片簡單等同于“搞笑片”,無論如何是不夠嚴肅的。
《桃花運》的確有很多笑場:首先是“時裝混搭”的效果,如保守的“老處女”梅婷與性開放的耿樂,悲情中的“單身媽媽”鄔君梅遇到“情場圣手”葛優,均具有“混搭”產生的笑料;片場也有很多笑點:梅婷的南京話亮相,范冰冰蓬頭戴著800度近視眼鏡在片尾出現,葛優留著飄逸長發、西裝筆挺的向觀眾走來,段奕宏扭起了電臀舞,還有諸如“總要全面了解我之后才能更好地相處”之類的臺詞等等,讓影片在播放過程中,頻頻引發爆笑。但是細細究來,這些笑聲更多是演員表演本身引發的,或者是演員表演之外的其他條件引發的,而不全是角色或者劇情本身引發的。比如,葛優的出場,他隨便一句并不幽默的臺詞甚至一顰一笑都能引起笑聲。其實這種笑聲與劇情無關,與演員在該劇中的表演無關,與所扮演的角色本身也沒有關系,倒是與演員自身有關:是觀眾對葛優自身已經奠定了的笑星地位形成的心理定勢而產生的反應。因此影片在播放過程中引動的笑聲總有點夸張、不真實。因為它不全是喜劇本身引發的笑聲。
一、喜劇性產生條件
什么才是喜劇本身引發的笑聲?作為一門獨立的藝術,喜劇是以諷刺、幽默、嘲弄、機智、詼諧、滑稽等手法建立起來的藝術形式,是憑借角色的自嘲式的“動機敗落”來動人笑感,讓人在笑聲中認識和回復本真的生活體驗和本真的世界,以揭示生活中的普遍的真實。角色的“動機敗落”本身并不可笑,可笑的是角色自嘲式的“動機敗落”。所謂自嘲式的“動機敗落”是通過角色自身的夸張、變形、偽裝、假作正經、自相矛盾等等喜劇手法來實現的。因此,喜劇性才能讓喜劇本身引發笑聲。下面的一些條件都可以產生喜劇性:
1動機喜劇性
所謂的“動機喜劇性”是指角色的動機本身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基本上是屬于違反正常尺度的要求,而且在現實生活中幾乎是不太可能實現的。因為動機的低現實性所以具備了“敗落”的可能性。《桃花運》站在女性的立場講TX段有關桃花運的故事,這五段故事都很有“動機”,但是這些動機中只有曉美的動機可能成為“喜劇性動機”。其他四個人的動機都是合理的、正常尺度的要求,不具備喜劇性。
2情景喜劇性
最基本的喜劇性情景是形式和內容的背離:形式強大,內容空虛。比如一個錯誤、一個虛無的內容被表現得一本正經,喜就會產生。《桃花運》的喜劇性情景主要是在男主角方面:郭濤扮演的張蘇是職業騙子,偏是一往情深的對待高姐,影片中有很多細節、室內戲的安排,像照顧病人上廁所、喂病人喝甜粥等還頗有生活氣息;葛優扮演的求婚男人王奔明明是至少在三個女人之間游走,卻偏偏不動聲色地去跟葉老師的兒子去踢球、談心。這些強大的形式和內容的虛空之間的矛盾和錯亂一旦被喜劇手法揭穿,喜劇性就會產生。可惜導演沒有從男角的角度去挖掘這些喜劇性情景,而是從女主角的角度去表現結局:高姐的結局生成毫無邏輯性的“高尚”,葉老師的結局生成了令人同情的“凄涼”。喜劇性情景因為導演表現角度的轉換而完成了其喜劇性。
3人物喜劇性
作為賀歲片的喜劇,因為娛樂的要求,風格輕松,所以題材多見于日常生活,喜劇的對象往往不具有敵對性。這類喜劇片的人物宜是有缺陷的好人:壞人與主體敵對,很難造成輕松氛圍,完美無缺的人失去喜劇性的基礎——人類自身的弊端所造成的偏離。人物喜劇性從內容上講,是被歷史否定了的東西,它偏離或低于正常的歷史尺度。簡單地說,人物喜劇性是對正常生活的偏離。但是從喜劇的角度來看,“偏離”本身并不具備喜劇性,只有當人物意識到偏離而不由自主地產生了偏離,或者意識不到自己的偏離,而把偏離作為正常的東西顯示出來,或者明知自己的偏離卻要掩蓋自己的偏離,甚至炫耀自己的偏離,這個時候,喜劇性才會產生。喜劇性引起的笑,一方面是出自于審美的人對喜劇性人物的偏差、錯誤、丑陋的發現,另一方面也有對于自己能保持正常的尺度的自豪和自尊。從男主角的立場看,《桃花運》五個男主角中只有職業騙子張蘇和情場圣手王奔具備喜劇性,另外三個不是喜劇性人物。尤其是廚師關翔,以未婚妻的名字買了一小套婚房,在大海的背景下奮力背著一塊裝修婚房的門板,是一個誠實可愛的年輕人,不屬于喜劇性的人物,而屬于“美好”的人物。以情騙錢的張蘇,雖然行為可惡,但是在劇情中有細心照顧病中的高姐的種種真實行為,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惡劣性。至于游走于三個以上女子之間的情場圣手王奔,雖然濫情,但也因為在劇中有對葉老師的孩子的一片愛心的真實表現,其丑陋性同樣也得到削減,終于沒有成為十足的“惡人”,從而具備了喜劇性人物的潛質。但是導演并不是從男角的角度去讓其動機“自嘲式的敗落”,反而是從女角的角度去揭穿其騙局,讓這兩個具有喜劇性潛質的人物完全失去了喜劇效果。
從女主角的立場上看,《桃花運》的五個女主角中,只有一心要嫁給富商的曉美是喜劇性人物。年輕漂亮的曉美從原公司請假半年來富商的兒子任職的公司“臥底”,但是最后是“動機敗落”了:富商的兒子的公司遭遇金融風暴,“金龜”消失了。影片中有一些情景也很富有喜劇性:經理給她發獎金,她不肯“因小失大”,只好大方地說:“分給大家吧”,但是回到家里卻眉飛色舞地在那一沓錢上狠勁兒的親了一下,經理請她吃飯,飯后讓她去商場挑選生日禮物——曉美幻想著買了一大堆高級時裝,最后卻不得不壓抑著欲望,選了一件普通的禮品。影片運用夸張、對比、自相矛盾的手法將曉美的拜金主義進行了善意的嘲諷。觀眾以一種輕松的居高臨下的態度對它們進行評價與批評,明顯地覺得對象低干自己,是自己嘲笑的對象,從而完成喜劇性。
二、喜劇性與審美情感
一般來說。喜劇“幾乎不去‘建設,不試圖去創造所謂新的、大的、有用的‘思想體系,不鼓勵‘創造美好生活的動機,不在形式主義的意義上去追求‘真、善、美。它似乎一直在‘破壞,通過破壞假象來還原生活本來的、真實的面目。”這才是喜劇的功用和立場。依此,有兩種審美情感是不能完成喜劇性的:
1贊嘆和崇尚
贊嘆和崇尚是對人生正價值的肯定,對象與主體同一或者高于主體,審美的人無法產生優越感,不能完成喜劇性。比如《桃花運》中的曉美,最后是在公司裁員、并且只能領取最低生活費的情況下,留了下來,這已經從喜劇走向美好了。它讓我們感動,而不是讓我們輕松愉快的笑。
2同情和恐懼
比如一個人悠然自在的吹著口哨、西裝革履地騎著自行車,在拐彎時突然滑倒,他的狼狽與他的衣著形成強烈的反差,行人就會幸災樂禍的大笑起來。但是,如果這個騎車的人摔傷了,行人肯定就不會笑了,因為產生了同情和恐懼。喜劇也一樣,它引起的審美情感是不能有諸如同情、恐懼這樣的痛感的,否則就笑不起來。比如《桃花運》中的葉老師被情場圣手所騙的遭遇就不能完成喜劇。
當然,賀歲片也不是一定要拍成喜劇片;作為一種審美類型,喜劇里面也可以有美好、有悲劇的成分。不過,想要引動觀眾的笑感,不去挖掘喜劇性,而在別的效應(比如明星效應)上去“搞笑,實在不能叫做藝術。觀眾需要娛樂,也需要藝術;觀眾是在電影院里看電影,不是站在馬路上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