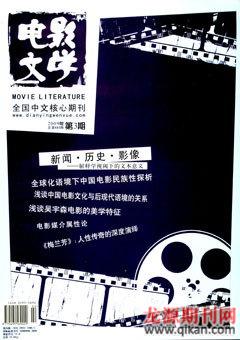“底層”創(chuàng)傷、性別倒置與視覺權(quán)力
劉保慶
陳凱歌導(dǎo)演的《梅蘭芳》自公映以來,褒貶不一。梅蘭芳是個伶人,伶人生活在社會底層。從底層敘事角度分析,這部電影顯示出非同一般的視覺潛力。
一、“底層”創(chuàng)傷
電影《梅蘭芳》講述的是京劇大師梅蘭芳幼年到少年成年的悲歡離合故事。故事大致選擇了梅蘭芳一生中死別、生離和聚散三個片斷來講述,把這三個片斷貫串起來的是梅蘭芳大伯臨死前寫給梅蘭芳的一封信。
在電影中,信件出現(xiàn)了四五次。大伯的信不僅是這部電影的外在線索,把整部故事勾連起來,還是推動故事情節(jié)向前發(fā)展的因素。這封信蘊涵了大伯對自己一生的總結(jié)和感悟,不同階段的梅蘭芳對這封信有不同的解讀和認(rèn)識。
信件對整部電影以及梅蘭芳這個形象形成了一種控制,體現(xiàn)在電影先放映幼年的梅蘭芳讀大伯的信件,然后才打出字幕“梅蘭芳”。信件就好像魯迅小說《狂人日記》前面的“序”一樣。對整部影片發(fā)揮著不斷闡釋、控制的作用。
信對幼年的梅蘭芳產(chǎn)生了一種“震驚感”,表現(xiàn)在電影中幼年的梅蘭芳讀到大伯因為戴上紙枷鎖時那驚訝和恐懼的鏡頭。太后的萬壽節(jié)人人穿紅,大伯因為舅母出殯沒穿,被“賞賜”一紙枷鎖,撕破一點就弄死。紙枷鎖事件對幼年的梅蘭芳造成創(chuàng)傷,形成輝之不去的陰影,對唱戲產(chǎn)生一種內(nèi)心深處的恐懼感。紙枷鎖事件,在電影中被大伯解釋為“記著,唱戲的再紅,仍然讓人看不起”。
“創(chuàng)傷”是精神分析學(xué)家弗洛伊德提出的一個概念。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創(chuàng)傷是引起疾病的重要原因。當(dāng)人經(jīng)歷比如死亡、暴力等災(zāi)難時,心理上會產(chǎn)生焦慮不安、無助感。為消除這種“痛”,當(dāng)事人把它壓抑進“潛意識”,但創(chuàng)傷并沒有消失,時常會冒出來,“侵蝕”人脆弱的自我。弗洛伊德創(chuàng)傷理論揭示了創(chuàng)傷不僅僅是個生物意義的疾病,而且想象和幻想在對付創(chuàng)傷中的作用。”
這種精神創(chuàng)傷是由歧視造成的,擺脫這種創(chuàng)傷的努力是梅蘭芳和十三燕演戲的動力。電影《梅蘭芳》講述的不僅是梅蘭芳面對精神創(chuàng)傷的心靈史,而且是作為“底層”的伶人反抗命運的抗?fàn)幨贰<埣湘i不僅籠罩在梅蘭芳心靈上,而且籠罩在所有伶人身上。如邱如白所說紙枷鎖可怕在于它是薄薄的,易撕開。可是如果可以撕開,那么梅蘭芳的爺爺、大伯早就撕開了。
二、循環(huán)邏輯
提高伶人地位,改變伶人被歧視的現(xiàn)狀,是梅蘭芳和十三燕共同面臨的問題。
十三燕對自身地位有清醒認(rèn)識“因為我們是下九流啊”。對于自己出神入化的戲劇表演,十三燕極其自負(fù),同時又深深感受到了自己從事職業(yè)的卑微。在十三燕觀念中,要提高伶人地位,必須改變社會對伶人的印象。要改變社會對伶人的印象,就必須唱好戲,而且要按規(guī)矩唱戲。十三燕的觀念是傳統(tǒng)專制思想影響下的產(chǎn)物,也就是認(rèn)同現(xiàn)實秩序,如同啟蒙者邱如白所說“只能申訴,不能反抗”。這就注定了十三燕反抗命運、爭取地位的人生是個悲劇。這集中在梅蘭芳和十三燕對待“改戲”態(tài)度上的區(qū)別。
啟蒙者邱如自批判京戲處處都是規(guī)矩,戲中的人是死的人,而真正的好戲應(yīng)該是帶人打破規(guī)矩的。邱如自代表當(dāng)時啟蒙者對大眾的啟蒙,因此要求改戲。梅蘭芳深表贊同,這和他內(nèi)心深處的紙枷鎖創(chuàng)傷分不開。要想消除或彌合紙枷鎖創(chuàng)傷,要么不把它當(dāng)作紙枷鎖,完全和戲中人物合一-要么就是打破紙枷鎖,徹底消除可能戴上紙枷鎖的恐懼。因此,梅蘭芳堅持改戲,也是為了消除歧視帶來的創(chuàng)傷。
十三燕認(rèn)為,改了戲會被別人看做是朝三暮四,會加深別人對伶人身份的歧視:伶人是下九流啊。馬三認(rèn)為改變被歧視的命運就是認(rèn)同現(xiàn)實專制秩序,演好戲,唱紅了才能獲得別人尊重。他遵循的是個循環(huán)邏輯:要提高伶人地位就要唱好戲,把莊重而高貴的京戲人物演活,這樣才顯得莊重和體面。但是現(xiàn)實是,他越唱得好,越無法改變伶人被歧視的現(xiàn)狀,也越符合伶人的身份,越被人歧視。
第二場比賽十三燕失敗,馬三把瓜子皮吐在戲臺上。這在十三燕看來簡直是對自己人格的侮辱,“這臺上這么尊貴的地方,容你這么糟蹋啊?”戲臺是體現(xiàn)其生命價值的地方,糟蹋戲臺就如同糟蹋十三燕。為了希望馬三不要糟蹋戲臺,十三燕甚至向馬三鞠躬。但當(dāng)十三燕要求十三燕低三下四給他再次鞠躬時,他高聲拒絕“那得爺樂意”,這在十三燕看來是人格的侮辱。但是十三燕明知必敗仍然要唱,他并非想要通過第三場來獲得座兒的認(rèn)可,而是要贏得人格和尊嚴(yán)。
馬三的侮辱使得十三燕從夢中驚醒,讓他認(rèn)識到,作為伶人再唱得好也被人歧視。所以他告訴梅蘭芳“等你大成了,一定要大大方方地提拔提拔咱伶人的地位”。
從清末到民國這段傳統(tǒng)和西方思想交融中,伶人的地位并沒有得到改變。十三燕的悲劇暗示出處于底層伶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他為了爭取人的尊嚴(yán)而付出了生命,讓人體會到老一代伶人高貴的人格,同樣對社會歧視產(chǎn)生一種批判。
三、看與被看:性別倒置
大伯的紙枷鎖創(chuàng)傷并沒有隨著清朝的滅亡而銷聲匿跡,梅蘭芳同樣并沒有因為戰(zhàn)勝十三燕而克服紙枷鎖創(chuàng)傷。紙枷鎖的陰影還時刻讓他感到焦慮、不安、無助,體現(xiàn)在他怕輸上。
邱如白留過洋,思想激進,反對京戲中存在的規(guī)矩,反對專制、壓迫和歧視,主張好戲應(yīng)該啟蒙大眾,打破束縛人的規(guī)范,從而解放人。邱如白是啟蒙者。影片的深刻之處不僅在于揭示出底層伶人的精神痛苦和創(chuàng)傷,而且對現(xiàn)代啟蒙思想同樣進行了批判。
視覺文化一個重要發(fā)現(xiàn)是,思想的形成并非僅僅是觀念,而是和人的視覺分不開的。腳弗洛伊德認(rèn)為窺視癖是人的心理本能,窺視癖滿足了人內(nèi)心潛意識的需要,人們通過看來得到性的滿足感。
看與被看構(gòu)成了電影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戲院不僅讓觀眾欣賞藝術(shù),提供藝術(shù)欣賞的對象,而且在布局安排上體現(xiàn)了一種等級制度。看戲已經(jīng)被性別化了。梅蘭芳扮演旦角。在戲中,梅蘭芳不僅是京戲故事的一個人物,更主要的是成為觀眾欲望投射的客體,承載著觀眾的欲望。被看的是女性,看的觀眾是男性。男性的觀眾正是在看戲中女性的梅蘭芳,從而獲得一種性的欲望滿足。這種觀看機制不僅存在封建專制的被啟蒙者看戲上,作為啟蒙者的邱如白第一次看戲時,也獲得了欲望投射的快感。影片中邱如白講自己不知道該把梅蘭芳當(dāng)作男人,還是當(dāng)作女人。實際上,作為啟蒙者的邱如白、胡適等和被啟蒙的大眾對梅蘭芳的觀看都是一樣的:男性看女性。戲臺給觀看的人戴上一層“藝術(shù)”的光環(huán),讓看者可以光明正大地來釋放自己的性欲。
視覺文化認(rèn)為看與被看還存在一種權(quán)力關(guān)系。看的快感分裂為主動的男性和被動的女性,是不平等的一種關(guān)系。這種不平等和歧視不僅表現(xiàn)在觀眾對伶人梅蘭芳的欲望觀看;而且還體現(xiàn)在梅蘭芳自己看待自己的態(tài)度上:觀眾把梅蘭芳當(dāng)女性看,梅蘭芳習(xí)得這種觀看方式,并內(nèi)化于自己觀看自己的方式。
現(xiàn)實中,梅蘭芳把自己看作男性,在戲臺上,他又必須把自己看作女性。出于理性的考慮,在現(xiàn)實中,梅蘭芳必須把戲臺上的自我觀看方式壓抑進潛意識中去,才能成為一個
“正常人”,即男性。但這兩種觀看方式必然發(fā)生沖突,造成人格的分裂。這就是性別倒置,通過刺客劉錫長間接表現(xiàn)r出來。
劉錫長是梅蘭芳的另一面,是梅蘭芳自視為女性形象的被壓抑對象。劉錫長為了迷上梅蘭芳,讓梅蘭芳看自己一眼,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槍殺孟小冬。梅蘭芳一方面想接近孟小冬,一方面又排斥孟小冬。作為梅蘭芳的女性自視形象,劉錫長槍殺孟小冬,其實是梅蘭芳人格中男性眼光和女性眼光的矛盾。
紙枷鎖指的是一種內(nèi)在心理控制即自視。梅蘭芳屬于座兒的,他要受到座兒的制約。座兒把他當(dāng)作了女性來觀看,那他就不能把自己當(dāng)作男性。孟小冬的出現(xiàn)讓梅蘭芳重新感知到自己的男性身份。他要和孟小冬在一起,其實是他掙脫紙枷鎖的努力。但作為紙枷鎖主體的觀眾逼迫他離開孟小冬,因為他這樣做和座兒對他的觀看發(fā)生了沖突,所以邱如白要雇殺手逼迫孟小冬離開梅蘭芳。如果梅蘭芳和孟小冬在一起,他就不能把自己和戲中的女性融合在一起。邱如白認(rèn)為“只有心中最干凈的人才能把情欲演得那么到家,那么美”,孤獨成就了梅蘭芳,誰毀了梅蘭芳的孤獨就是毀了梅蘭芳。
影片展示出,現(xiàn)代啟蒙思想雖然批判了京戲中的封建專制思想,如邱如白批評京戲?qū)ε缘募s束,提倡解放人,打破壓迫和規(guī)矩。但是,現(xiàn)代啟蒙思想重新塑造了新的視覺專制機制,同樣對底層的伶人形成一種壓迫的力量。
四、現(xiàn)代明星機制
梅蘭芳經(jīng)歷了從清末到民國,再到現(xiàn)代三個歷史階段,伶人的地位也在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變化,這就是現(xiàn)代明星機制的形成。與傳統(tǒng)不同,現(xiàn)代明星機制表現(xiàn)在;明星是個公共人物,他不僅在戲中屬于觀眾,需要迎合觀眾欲望的投射,而且現(xiàn)實中也必須符合觀眾對他的想象和期待。
如果說傳統(tǒng)社會把伶人當(dāng)作低一等人看待,現(xiàn)代視覺機制則要求明星的私人生活也必須符合觀眾對明星的期待,一種無形的視覺壓迫更生活化、更細(xì)微化了。當(dāng)現(xiàn)實中的梅蘭芳把自己當(dāng)作男性接近孟小冬時,邱如白不惜一切手段阻止,標(biāo)志著現(xiàn)代演員的私人生活已經(jīng)成為公共空間了。
演戲不僅帶上了政治色彩,而且還包含民族歧視和文化侵略意味。日軍攻陷南京,發(fā)生了震驚中外、毫無人性的南京大屠殺。為掩蓋日本野蠻中國的罪行,實行愚民政策。日軍認(rèn)為梅蘭芳最能代表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最能表達(dá)中國人的情感和人心,讓梅蘭芳給日軍攻陷南京唱戲,是為了從文化上讓中國人俯首稱臣,為了維護日本的非正義統(tǒng)治。演戲同樣也是對中國人的民族歧視。梅蘭芳扮演旦角,最能代表中國人心,觀看者為日本人。日本人觀看演出,其實內(nèi)在的是主動/男性/日本人與被動/女性/中國人的對立結(jié)構(gòu)。演戲中看與被看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再次轉(zhuǎn)化為,中國人是低等的、女性的、柔弱的、被動的、是被觀看的;而日本人是高等的、男性的、剛強的、主動的,是觀看者。
為了抗拒這種歧視,表明民族大義,梅蘭芳的留須明志就不僅帶上了民族反抗、文化反抗的色彩,而且也是他消除紙枷鎖創(chuàng)傷的一次努力。留胡須,在日本軍官田中隆一看來是不可思議的,認(rèn)為是梅蘭芳戲弄自己。田中隆一在這里的質(zhì)問不僅代表了日本對中國的民族歧視,因為留胡須就不能再讓日本人把中國人當(dāng)作女性來欣賞;而且也代表觀眾對梅蘭芳的質(zhì)疑。田中隆一也像中國觀眾一樣喜歡京戲和梅蘭芳,表明觀眾開始把演員的私人生活也當(dāng)作觀看的對象,不允許梅蘭芳打破觀眾對其女性形象的欲望想象。梅蘭芳留胡須在觀眾看來不只是戲弄自己,更是戲弄他們心中的欲望,讓觀眾欲望的投射無法實現(xiàn)。
梅蘭芳留胡須,不僅是明民族大義,也是一次消除紙枷鎖創(chuàng)傷的努力,表明自己的男性身份。梅蘭芳希望觀眾在現(xiàn)實中把自己當(dāng)男性看待,也是爭取伶人地位的努力。影片讓他在留須明志時再次講到大伯、十三燕對自己的期望:體體面面提高伶人的地位。而他能做的只能如此。留胡須,梅蘭芳想表明,伶人也有民族氣節(jié),而且是有尊嚴(yán)的人。
現(xiàn)代明星機制把演員當(dāng)作公共人物看待,使得演員不僅要演好戲,而且現(xiàn)實中也要受到觀眾眼光的觀看和約束。這在當(dāng)今已經(jīng)成為普遍現(xiàn)象,被當(dāng)作“狗仔隊”的記者為了滿足觀眾對明星的窺視欲望,竭盡所能報道明星的隱私,已經(jīng)成為約束演員的一種壓迫性力量,這也是影片創(chuàng)作的現(xiàn)實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