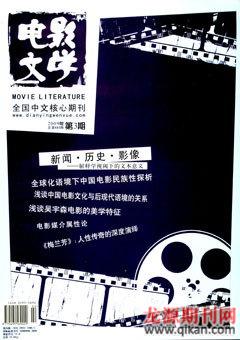兩個“我”的迷藏
潘自意
[摘要]《捉迷藏》是一部由天才童星達科塔·范寧和奧斯卡影帝羅伯特·德尼羅主演、20世紀福克斯公司出品的一部心理驚悚電影。影片以心理懸疑的手法將一個由家庭倫理而引發的悲劇曲折道來,將心理與故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形象地展現出分離性認同障礙這一神秘的疾病。本文從心理學的角度入手分析,結合文本敘事,深入剖析了分離性認同障礙的來龍去脈。
[關鍵詞]《捉迷藏》;精神分裂癥;分離性認同障礙;人格分裂
長久以來,心理題材的電影總能吸引廣大觀眾的眼球,因為直到今天,即使人類已經進步到可以上天入地、改造世界,可對于自己的心理卻始終懵懂無知。我們對一知半解的東西總是最好奇的,特別是與自身有關時。《捉迷藏》正是抓住了人們的這一心理,將一個家庭倫理悲劇以心理懸疑的手法曲折道來,讓人的心隨影片一起跌宕起伏、飄忽難安。
影片開場便奠定下了一種灰暗、壓抑的基調:在一幅陰冷抑郁的畫面中,一輛汽車在高速公路上奔馳,一曲忽緩忽急、變幻莫測的配樂同時環繞耳畔,仿佛在向觀眾預示著前路的陰暗與恐怖。事情緣起于艾米莉(由天才童星達科塔·范寧飾演)的母親——理查德(由羅伯特·德尼羅飾演)的妻子,她自殺了。艾米莉就此變得沉默寡言。身為心理醫生,父親理查德堅決帶她搬往鄉下,希望通過遠離傷心地,讓女兒的心理創傷慢慢愈合。但是沒想到,鄉下并沒有帶給他們想象中的寧靜,意外事件接踵而至,從寵物狗到父親的新女友接連都像艾米莉的母親那樣死在了他們家的浴缸中。在父親愈發憂慮的目光中,似乎殘酷的真相無可避免:這樣一個美麗弱小的女孩原來竟是心理變態的兇手!就在這股氤氳不去的恐怖中,一種揮之不去的不安和來自心底的驚嚇油然而生。但是,最后的二十分鐘,影片峰回路轉,在艾米莉聲聲“查理”的呼喚中,父親躲藏多時的第二個人格終于被他本人捉住了:原來所有的死亡——包括自己妻子的——都是自己的另一面查理一手造成的;原來自己的女兒自始至終都只是個孤立無援的受害者;原來自己這位聲名在外、心心念念要為女兒治病的心理醫生才是病人!
真相大白,可更令人感興趣的一個疑惑仍然未解:父親理查德得了什么病?是精神分裂癥嗎?恐怕不然。因為精神分裂指的是那些思維、知覺和情感嚴重失調的人,他們往往舉止異常,并且伴有社會性退縮。具體來說,精神分裂主要有妄想、幻覺、言語混亂、行為無序或緊張、消極性表現這五種癥狀。有的精神病人會妄想有人在監視、威脅、迫害、控制自己,或者自己是一個權勢無上的人物。有的病人則無法沿著一條思維軌跡說話,而是毫無邏輯地胡言亂語。還有很多人有幻覺,他們會聽到不存在的聲音,或從外界傳來、或在自己的頭腦中。他們的心境和行為往往異于常人,要么狂躁不安,要么遲鈍平淡,甚至出現緊張性木僵。這些癥狀在父親理查德那里基本上見不到。在真相揭露之前,理查德在他人眼中始終是一個令人尊敬的心理醫生,至多覺得他因為喪妻而郁郁寡歡并且整天為女兒操心。
理查德的病應該是分離性認同障礙,俗稱多重人格——一種罕見的人格障礙。從全世界范圍來看,1986年的DID個案也僅有約6000件(Eizinga,van Dyck,&Spinhoven;,1998),而且絕大多數都集中在北美——也就是本部影片的制作地。最早的案例可以追溯到1905年由摩通·普林斯報告的鮑恰姆普小姐,這位病人共有17種人格。自此以后,這種障礙對北美公眾的吸引力就與日俱增,而與之相關的電影以及文學創作更是接踵而至。從蒂格鵬(Thigpen)和克雷克利(Cleckley)的《三面夏娃》(The Three Faces of Eve)(1957)這部電影以及書的流行,以及描寫一個有16種人格女孩的《西比爾》(sybil)(Schreiber,1974)成為最暢銷書籍這兩點就可見一斑了。
具體來說,這種患者的人格會分裂為“兩種或更多不同的身份或人格狀態,每一種都整合、發展得很好,它們輪流控制患者的行為”。不同人格之間可能互相了解、可能互相遺忘、也可能只是一方了解另一方。在后兩種情況下,當寄主——即在障礙出現之前就存在的人格——引導患者行為時,交替人格——即隨障礙出現的人格——完全意識到寄主的想法和行動并且會悄悄地行動,而對于寄主來說,只有當看到交替人格的行為時才會漸漸意識到交替人格的存在。在影片中,父親理查德就有兩個人格,一個是他自己,一個就是查理。這兩個人格輪流出現在父親的身上。而且,作為交替人格的查理知道理查德的存在,并且對他的想法和行為似乎也了如指掌,但是理查德直到最后一刻之前,始終對查理的存在一無所知。而正是這種無知導致了悲劇的無可挽回。
理查德和查理這兩種人格代表了父親身上的善與惡、好與壞。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角度來說,理查德反映著父親的超我,也就是善的部分,他是受人尊敬的心理醫生,深愛妻子的丈夫,關心女兒的父親,珍惜家庭的男人,友好善良的朋友。而查理則是父親的本我,即是惡的化身,他沒有道德觀念,只遵循快樂原則,隨心所欲、為所欲為,雖然影片中對查理的正面描寫只有最后的二十分鐘,但就是這二十分鐘,他所表現出的那種赤裸裸的邪惡讓人不寒而栗,他殺人如麻,誰妨礙他誰就要死,即使連艾米莉也不放過,他似乎不僅想毀滅身邊的一切,更想毀滅他自己——或者應該說另一個自己:理查德。而這位心理醫生之所以會患上人格分裂,就是因為第三個人格結構——自我——的弱小。他的自我無法像正常人的那樣去整合本我和超我,只能徒然看著兩者分道揚鑣,互相對抗,最終兩敗俱傷。
那么,到底父親的病因在哪里?原來一切的根源,就是父親親眼目睹了他妻子的紅杏出墻。父親無法接受自己深愛的妻子竟然背叛了自己,這一突如其來的強烈刺激令他猝不及防:他憤怒,他絕望,可是他一貫的道德觀——他的超我——阻止他做出任何發泄甚至報復的行為,所以他選擇了隱忍;但是在他的內心深處——他的本我,對這種奇恥大辱實在難以忍受;自我的強制壓抑,耗竭了自己的資源,最終使這種憤怒以扭曲的形式——一個不同的、不被認可的自我——爆發出來;而此后,自我又選擇了遺忘這些經歷,從而保護心理不受超我的譴責。正如影片中另一位女心理醫生反復強調的“trauma causes pain(創傷導致痛苦)”,父親情感上的巨大創傷導致了他超乎常人的痛苦。但是女醫生沒有料到的是“pain causes DID(痛苦導致雙重人格)”,這種無可抗拒的痛苦最終導致了父親人格的扭曲。片名《捉迷藏》表面上似乎是說艾米莉和父親之間的迷藏,實際上卻更暗示著理查德和查理——父親的兩重人格一之間的迷藏。
影片的最后一格定在艾米莉的畫上——異峰突起:當父親最終被女醫生自衛槍殺,艾米莉最終被女醫生領養、回歸正常生活,一切看似歸于平靜時,艾米莉的自畫像上竟赫然出現了兩個頭!她也患上人格分裂了嗎?……其實,這一“最后小高潮”的手法在好萊塢很多驚悚懸疑類電影中都曾使用過,比如《本能》、《致命ID》等等,都是在最后一刻再掀波瀾,營造一種言有盡而意無限的氛圍,使觀眾在震驚之余,回味不已。本片中的這一手法除了有上述作用外,更暗合了影片對分離性認同障礙的解釋——trauma causes pain(創傷導致痛苦)。實際上,調查研究顯示,幾乎有一半的分離性認同障礙患者報告在小時候親眼目睹過暴力致死,而對象通常是父母中的一個或者兄弟姐妹(Putnam,Guroff,Silberman,etal.,1986)。恐怕艾米莉也正是因為在短短幾個月內接連目睹了母親的死亡和父親的瘋狂,才使她也不得不分離出另一個人格來承受她的痛苦。在女醫生的照顧下,從外表上看,艾米莉似乎已經和正常的女孩沒有兩樣了,她一改往日的憂郁,重展笑顏;但是很可能,在內心深處,她始終滯留在了父親死亡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