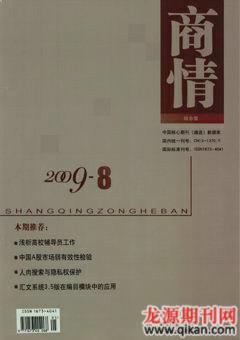儒學和基督教道德核心理念的差異
傅 明
【摘 要】儒學對天人關系的基本認識是 “天人合一”,基督教將天人關系定義為 “父子關系”。天人合一是相通相類、和諧平等的關系,父子關系則是創造與服從、緊張與對立的關系。儒學與基督教對天人關系的不同回答,既導致了中西宗教自由主義與專制主義的差別,也反映了中西思維方式的不同和文化的本質區別,以及中西方道德內涵的不同。
【關鍵詞】儒學 基督教 道德哲學 仁 愛
作為中西文化的代表,基督教和儒教均以重視道德見稱,然而二者的核心理念及其哲學基礎卻是大為不同的。“愛”是基督教的核心理念。一般認為,《舊約圣經》的主題是“律法”,《新約圣經》的主題則是“愛”。在《新約圣經》中,“愛”既通過基督的生平尤其是受難體現出來,也通過保羅書信得以明確。保羅在《羅馬書》中指出,所有的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愛完全了律法”。
“仁”在儒教道德體系中的地位就仿佛“愛”在基督教中的地位。《論語》中兩個最重要的道德范疇是“仁”與“禮”,其中“仁”字出現105次,“禮”出現75次。孔子視“仁”為諸德之首。“仁”具有統攝諸德的內涵。
一、儒學與基督教道德哲學核心理念的相同性
基督教的“愛”與儒家的“仁”有許多相通之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愛”和“仁”都強調一種對他人私的關愛
儒學和基督教都是非功利主義的,重視仁愛的義務性。孔子說,“仁者愛人”(《論語?顏淵》)。董仲舒進一步強調仁只能存在于愛人而不是愛自己之中:“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仁者,愛人之名也。”
在基督教里,盡管“愛”有多種形式,但是都必須是一種發自內心、出自靈魂和主動給予的愛。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中對“愛”有一段經典描述:“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張狂,不作失禮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動怒,不計較人的過犯;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愛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的。”
(二)“愛”和“仁”都是人突破自身局限、形成完善人格的必由之路
在儒家看來,既然“仁”是人類一切美德中最高的美德,是人與生俱來的本質特性,那么要想做一個完善的人,就要擁有“仁”。基督教的觀點與此相同,正如保羅所說的那樣:“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能說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那么我也只是個鳴的鑼、響的鈸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具有各樣的知識,而且具有全備的信,所以能夠移山填海,但若沒有愛,我就什么都不是。我若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給予窮人,又舍己而置身于火焰之中,若沒有愛,仍然與我毫無益處”。
然而所有宗教所體現的道德關系都包含兩方面的內容:神與人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其中神與人的關系是核心,是決定性的。人與人的關系是神與人的關系的社會表現,是從屬性的。在人與人的關系層面,基督教和儒教存在著相當的相似性、相通性,然而一旦深入到神與人的關系層面,巨大的差異就體現出來。
二、儒學與基督教道德哲學核心理念的差異性
(一)“愛”與“仁”的本體論依據不同
基督教的“愛”來自上帝,儒學的“仁”則來自人的本性。根據基督教教義,“愛”出自上帝的賜予。人自身之所以無法產生愛的能力,是因為每個人生而有罪,這罪不是一時一地的邪惡行為,而是貫穿人的全部生存狀態,所以人必須靠上帝的恩典才能愛。
儒學的“仁”是人生而具有的。《孟子?告子上》認為:“仁、義、禮、智,非由外爍我也,我固有之也。”既然仁義都是人生而具有的,那么行仁義的依據也不在外,而在自身。孟子認為仁義是人之為人的標志,不行仁義則不能算是人,只能算是禽獸,因此為了證明自己是人,就必須要行仁義。
(二)基督教的“愛”有著比儒學的“仁”更為廣泛的內涵
“仁”是人的社會屬性,說得更具體一點,是人的道德屬性。“仁”就是良知、良能。其在儒學倫理觀中有著嚴格的界限。對父母是親愛,對人民是仁愛,對萬物是愛惜,三種愛指向不同的對象。
基督教的“愛”則不僅僅限于道德領域。奧古斯丁認為,愛之不同只在于目的,其本質“都是將我們和我們所愛的目的物連在一起的企圖”,“一切的愛都是占有欲的愛”,所以愛與愛欲的區分僅僅是義理層面的。在基督教看來,情欲的愛、理性的愛和宗教意義的愛只是愛的對象、目的不同罷了,實際上所有的愛是連成一體的,因為都是上帝對人的賜予,具有神圣的意義。
(三)博愛與“愛有差等”的對立
基督教強調愛的超越性——超越國家、民族和血緣的界限,因此是一種博愛。耶穌所弘揚的天國是向所有人開放的,不僅向猶太人,也向異教徒和罪人開放,體現出一種世界性宗教的博大胸襟。
儒學也有提出過博愛思想的人,如韓愈、張載。韓愈說“博愛之謂仁”(《原道》),張載說“愛必兼愛,成不獨成”(《正蒙?誠明》),“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正蒙?中正》)。但是,這種愛骨子里還是儒學“愛有差等”的愛。說到底,儒學的“仁”盡管提倡“愛人”,但是這種“愛”是受到禮的節制的,正所謂“克己復禮為仁”,“禮”作為宗法社會中的行為規范,自然具有濃厚的宗法血緣特征,所以孔子認為“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論語?學而》)
儒學以尊親為衡量道德行為的首要標準。對于儒學而言,“仁”不僅是個人修養的重要內容,也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
基督教和儒學在倫理觀上的差異,是宗教、社會基礎和思維方式的差異的結果。雖然二者有著諸多的的差異,但這并不能說明基督教文化和儒學文化之間是不可通約的。基督教教義和儒學學說都是不斷汲取人類文化的優秀成果而成為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的代表,而且這一過程仍在繼續中,它們所體現出的強大包容力、吸納力使我們有理由相信它們之間的相互理解、融合是可能的。
參考文獻:
[1]蘇興.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63.
[2]翟本瑞,尤惠貞.基督教“愛觀”與佛教“慈悲觀”的比較.普門學報,2002,(2).
[3]董小川.儒家文化與美國基督教新教文化.商務印書館,1999.
[4]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5]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古籍山版社,1997.
[6][美]胡斯都?L?岡察雷斯著.基督教思想史.金陵協和神學院,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