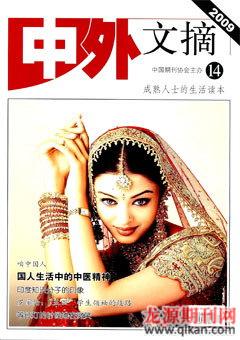西南聯大的另一筆財富
2009-07-23 01:48:24游宇明
中外文摘
2009年14期
游宇明
1941年4月,國立清華大學在昆明拓東路聯大工學院舉行三十周年校慶。人在重慶的張伯苓特地叮囑南開大學秘書長黃玨生,清華和南開是通家之好,應該隆重慶祝,校慶大會上,黃玨生大作“通家”的解釋,指出清華的梅貽琦是南開第一班的學生。接著,馮友蘭登臺說,要敘起“通家之好”,北大和清華的通家關系也不落后,北大文學院院長(指胡適)是清華人,我是清華文學院院長,出身北大,此外還有其他好多人。會議開得非常熱烈,大家紛紛舉出三校人物互相支持的情形,在場的人無不深深地感受到西南聯大人的真誠團結。
其實,三校合校之初,彼此也是有些矛盾的。歷史學家、西南聯大校友何炳棣說:“最初較嚴重的是北大和清華之間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資格最老,而在聯大實力不敵清華。”劉宜慶《絕代風流》一書更是直接描寫了北大與清華之間的一次沖突:當時,梅貽琦任命聯大各學院院長、系主任時偏向清華,引起北大師生強烈不滿。一日,身為西南聯大三常委之一的蔣夢麟有事到暫留蒙自的文法學院去,北大諸教授竟言聯大種種不公平,一時師生群議分校,爭取獨立。正在群情激憤的時候,錢穆發了一個言,認為國難方殷,大家應以和合為貴,他日勝利還歸,各校自當獨立,不該在蒙自爭獨立。蔣夢麟立即插話:“今夕錢先生一番話已成定論,可弗在此問題上起爭議,當另商他事。”蔣夢麟采納了錢穆的意見,教授們便不說話了。……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