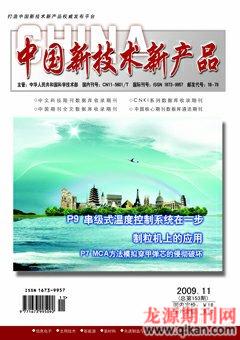從美術角度談藝術美
龔碧花
摘要:本文從美術方面談談對藝術的一些認識和看法,供同行參考。
關鍵詞: 美術;藝術美;程式
說到藝術,人們會很快想到美術,音樂、文學、舞蹈、戲劇等等。限于專業,我只從美術方面談談個人對藝術的一些認識和看法,想必能一斑窺見全豹。
藝術的外在形式可以是事物,可以是聲音,也可以是行為。美術的表現方式則是通過實物呈現的視覺藝術。“美”是美術作品生存的根本,一件作品失去了“美”,則毫無價值。美學家說過:“美術作品一定要美。”這個“美”正是藝術美。藝術美是一種獨特的美,它通過藝術作品表達一種思想、理念并引人思考,使作品從形式上,內容上達到完美的結合,給人以藝術的享受。優秀的藝術作品雖然令熱愛藝術的人愛不釋手,但它不一定是“美”的東西,它或許看上去很難看。很美的東西不一定具備藝術美。拉非爾的畫可謂“二美”結合(藝術上的美和世俗中的美相結合),他的作品總是給人甜美的感覺,波提切利的作品亦多以“美”而著稱,他們的作品因“美”而打動人,而梵高筆下吃土豆的農夫,割耳朵的自畫像,畢加索“解剖”的妓女,抽煙斗的男人等,看起來給人以恐怖或悲憫,不會使人想到美。而他們的作品則更能打動人,給人以震撼力,打動觀者的心靈,這便是藝術“美”之所在。現代藝術往往不能以美術稱之,但它們能引導人們的思考,它們依然很“美”。
藝術上形式與內容的問題始終被人們鬧得喋喋不休,偌大得一個中國,大部分藝術作品都是千片一律。形式和內容居然都有不成文的“規定”,山水畫必然是“斧劈”、“披麻”,要有山有水有云有樹有房屋,否則不是山水;油畫則要講筆觸,講肌理……,中國人習慣于守程式,講法則,筆筆皆有出處,說《芥子園》害了幾代學國畫的是有些道理。設計行業亦然,凡是“祖國”、“中華”題材的,長城、故宮、天安門等。藝術上最忌程式化,公式化。本來前人的法則自有前人的道理,但一定成為定理,便會失去生命力。一般都說內容決定形式,但也不一定,有時有了好的形式,未必是先有內容的。藝術本無定法,沒有固定的程式,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也沒有定法。藝術需要感情,美需要感覺,一切藝術類都是作者和觀者心靈之間感覺的交接和 碰撞而來的。
我們看到一副繪畫作品,被其深深地吸引,沉浸在藝術的美妙之中。而旁邊有人在解釋:什么顏色大膽,筆法樸拙,構圖奇特,黑白處理得當,這畫似乎是哪兒哪兒的山水……說得愈是具體,愈是顯得不美。真正的美是模糊的。美往往是只能意會不可言傳的--因為美來自情感,人的情感是微妙的,抽象的,模糊的。我們看達利的畫,會被深深地震動,但我們說不出到底“美”在那里,一旦說得仔細,達利的畫也就失去吸引力。達利自己也拒絕解釋他的作品。他說:“我和你們一樣看到我的畫感到驚訝。”藝術往往毋需太多的解釋,藝術是感性的,它的美是屬于感覺的,是“從心造境”(郭若虛語)的。千萬不要把本來模糊的東西說得十分具體。
既然美是情感產物,那么產生藝術美的唯一源泉是真情實感而非技術。技術可以幫助表現情感,但技術絕非藝術。偉大的藝術品并非技術性都很高,相反,真正的藝術品,其手段往往是笨拙的。而技術上相當高妙的,藝術性往往不高--因為他缺乏感情。原始社會留下來的樸拙的巖畫、石刻,雖然手段極其落后,然而并未絲毫影響其藝術美,相反增加了藝術性。漢、唐雕塑,洋洋大氣,氣魄宏偉,充滿時代的激情。其手法質樸、古拙。而明清的雕飾品,大部分雖技法精熟,雕飾精到,技法上遠勝于前代,但大都流于程式,過分的雕飾必然導致庸俗,讓人看了并不覺得很美。羅丹說,真正的藝術是忽視藝術的。同樣,真正的技巧是忽視技巧的。為藝術而藝術,為技巧而技巧,必然難以產生藝術的美。梵高在繪畫時,自己被深深地感動,他富有激情的筆觸完全是他情感的自然流露。他不會想到要用如何如何的技法等等。一切服從于藝術家的情感。真正達到“天人合一”境界的藝術家,中國只有徐渭,西方只有梵高。藝術家是因情感而激動而創作,而非為創作而情感。
藝術作品因有藝術美而生存,但現在藝術品是可以復制的或用人來復制,或用機器復制,藝術品被復制了。藝術美被復制嗎?這當然要看被復制的程度。復制的與原作越接近,其藝術美則會被復制一部分,但作品可以復制,作者的感情是不會被復制的,即使作者本人復制本人的作品(真正的藝術家是不會這樣做的),也不可能復制的一樣,因為很難再達到當時那種情境了。這也是一些藝術家的創作會有高峰和低谷的原因之一。北大美學家彭鋒先生認為當藝術家作品被復制得一模一樣時,藝術品本身顯得不重要了,判斷一件作品是否為意識品的標準是看其是否是藝術家創作的。我有不同的看法,其一是藝術家如果沒有藝術作品,何以為藝術家?一個被認為是“藝術家”的人,其生活方式又何以判斷是不是藝術家?其二,難道是“藝術家”創造出來的任何“作品”都是藝術品嗎?例如有一件作品的作者是一位普通人,時間久了,那位普通人成為知名的藝術家,那么那件作品是不是藝術品呢?即便是偉大藝術家,也有失敗作。看來判斷一件作品是否為藝術品的唯一標準是看其是否有“美”,羅丹說:“在藝術中,有‘性格的作品,才算是美的”。所謂“性格”,就是不管是美的或是丑的,某種自然景象的高度真實,甚至也可以叫做“雙重性的真實”;因為性格就是外部真實所表現于內在的真實,就是人的面目,姿勢和動作,天空的色調和地平線,所表現的靈魂、感情和思想。要使自己的作品有“性格”,藝術家本人必然是有“性格”的,藝術品永遠是藝術家個人的表現。在藝術家的眼力,自然中的一切都具有性格,因為藝術家所看到的,是他心靈的濾鏡所透過的,事物蘊藏得意義。藝術發展到今天,呈現出近于混亂的局面,什么樣的形式都有,打亂了我們原有的藝術欣賞習慣,人們感到藝術欣賞今天很難有一個標準,但什么樣的才叫有“性格”呢?似乎又很難確定,尤其是西方的一些“現代藝術”,有的像是再做游戲。因為古典藝術是以和諧為美的,而現代藝術的特點是不和諧。不“美”,但往往令人思考。在當今雜亂的“藝術游戲”中,我們應該冷靜地去看,如果在其“游戲”的內部傳達了某種內容和趣味,那就值得我們欣賞,如果“游戲”里還透露出一種人生的體驗,一種生命的體驗,而且很巧妙,引人深思,這個游戲便是一件作品了。--藝術如何變,是不會脫離感情的。“沒有情感這個品質,任何筆調都不可能打動人的心。”(狄德羅[法]語)改變的只是表現方法和形式藝術表現的是站在自然前面的人的情感。吳冠中提出的“風箏不斷線”也是這個道理。
參考文獻
[1]鮑詩,西方現代派美術,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
[2]《羅丹藝術論》1978年,人民美術出版社
[3] 王明居,模糊美學,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4] 劉冶貴,中國繪畫源流,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3.
[5] 溫肇桐,中國繪畫批評史略,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
[6] 王伯敏,中國繪畫通史(上下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7] 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8] 俞劍華,中國古代畫論類編,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
[9] 蔣勛,美的沉思:中國藝術思想芻論,上海:文匯出版社2005.
[10] 于安瀾,畫史從書,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
[11] 張育英,中西宗教藝術,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