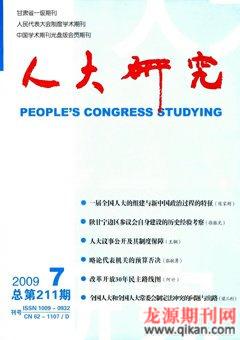改革開放30年民主路線圖(上)
阿 計
30年來,在中國社會先后出現的“法治”、“人權”、“依法治國”、“政治文明”、“以人為本”、“保護私產”、“和諧社會”、“公民社會”等流行話語,莫不源自“民主”這一普世價值的精神滋養,它們支撐著政治變革的漸行漸深,也見證了執政理念和國家價值觀的不斷成熟。
路線1:“草根民主”,讓自治成為公民的生活方式
1980年1月8日,在劉三姐的故鄉——廣西宜山(現宜州市)屏南鄉合寨村,經過村民自發的投票選舉,產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村民委員會,村民自治的序幕就此拉開。
改革開放前,由上級欽定領導班子的“生產大隊”,是中國農村最基層維系了幾十年的組織體制。改革開放后,隨著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全面推行,集權管理模式已難以為繼,而以村委會為載體的民主自治機制,恰恰十分契合新興的經濟變革。正因此,村委會的“創意”被各地紛紛效仿,并很快得到高層認同,最終被1982年通過的新憲法所確認。其后,被喻為“草根民主”的村民自治全面啟動。
在中國農村改革史上,安徽小崗村和廣西合寨村無疑是最關鍵的兩個地理標記,前者的一紙契約引爆了經濟改革,后者的驚天創舉則激發了政治改革,它們共同構成了農村改革的兩條基本路徑。
1987年,經過激烈爭議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以“試行法”名義出臺,10年后的1998年,該法經大幅修訂后“轉正”,村民自治成為不可動搖的法定機制。與此同時,各種民主新機制也在村民自治實踐中不斷創造,其中最富傳奇色彩的當數“海選”。1991年,吉林省梨樹縣雙河鄉平安村換屆選舉村委會時,“不劃框框,不定調子”,將候選人提名權完全交給村民,由村民投票決定,這種類似大海撈針的選舉模式被形象地稱為“海選”。此后,“海選”在各地農村被迅速復制,并在上世紀90年代吸引了無數國際觀摩團。而“海選”與“草根民主”亦成為指稱鄉村民主的兩大公共詞匯,流行至今。
改革開放30年后,我國農村已普遍完成了六至七屆村委會選舉,平均參選率約為80%,約85%的農村建立了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會議的民主決策機制,90%以上的農村建立了村務公開、村民理財小組等民主監督機制。
與改革開放幾乎同時起步的村民自治,徹底顛覆了農村傳統的治理模式,讓9億中國農民進入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訓練班”,其樣板效應,亦開始向城市輻射。
盡管居民委員會在建國后不久就已出現,1982年新憲法和1989年《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亦將其定位為城市基層自治組織,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居委會成員一直由政府指派委任。直到1999年6月,沈陽市沈河區首次進行了由居民代表選舉居委會的試點,才打破僵局。此后,選舉居委會的民主實驗在各地此起彼伏,2001年在廣西武鳴等地出現的20余次居委會直選試驗,2002年在北京九道灣社區舉行的居委會大差額直選,2005年在深圳鹽田區的居委會直選中爆發的種種風波等等,都曾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到2007年底,浙江省寧波市已在全國率先實現了居委會全部直選。
隨著城市住房商品化的演進,一種新型自治組織——“業主委員會”浮出水面。1991年3月22日,深圳萬科天景花園成立了第一個業主委員會。與日俱增的業主委員會,很快成為城市業主維權運動的組織平臺和沖突焦點,呈現出“小區維權”通向“小區民主”的清晰軌跡。其中典型當數2006年發生在北京的“美麗園事件”,圍繞著罷免業主委員會、物業公司去留等議題,美麗園小區先后三次投票,民主理念和程序的演練可謂酣暢淋漓。更加耐人尋味的是,2003年深圳、北京等地的基層人大代表換屆選舉中,一批經歷了小區維權洗禮的業主,以自薦參選的方式成功當選,成為從“小區民主”走向政治參與的領軍者。
借助基層民主這一平臺,新的民主機制也在不斷衍生,浙江溫嶺的“民主懇談會”,武漢、重慶等地的社區聽證、“圓桌會議”等等,都成為推進民主的成功典范。
不可否認,無論在鄉村還是城市,基層民主自治都遠未達到理想狀態。持續多年的宗族勢力、行政干預、賄買選票等陰影,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使村民自治走入了瓶頸期,而“農民素質過低,不適合民主”之類的論調也從未平息。在城市,居委會過于濃重的“行政化”色彩、小區內外部日趨復雜的利益沖突等等,也對基層自治構成了巨大挑戰。也正是為了破解這些現實困境,《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均已列入修法議程。
但更應該看到,城鄉基層自治作為改革開放的一個關鍵指標,已經促使中國社會的基層治理結構由高度集權逐漸轉向民間自治,進而對國家政治生態產生了革命性影響。另一方面,隨著自治日益演變成公民的生活方式,基層民眾的民主意識和技藝不斷提高,漸漸成長為合格的現代民主政治主體。這就打開了一條“自下而上”的民主路徑,為更廣闊、更高級的民主實驗和政治改革提供了無限可能性。
只有洞察了這些深刻的變遷和未來的愿景,才能真正理解“草根民主”在30年改革開放歷程中的分量。可以斷定,城鄉基層自治仍是未來遞進民主的基本路徑。
路線2:為民行權,人大權威全面崛起
相較于近些年“兩會”所產生的“眼球效應”,似乎已很難想象30多年前人大制度的凋敝,彼時,人大盡管在理論上貴為國家政體,但歷經“文革”浩劫后已幾近癱瘓。
基于歷史的教訓,重建人大這一最重要的民主體制,是改革開放后的必然選擇。隨著1979年選舉法、1982年新憲法等相關立法的出臺,擴大全國人大常委會職權、縣級以下人大代表實行直選、縣級以上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等重大變革得以確立,這是推動人大崛起的基礎動力,至今仍是政治體制改革的豐厚遺產。2000年立法法、2006年監督法的先后問世,則為人大的兩大基本職權進一步提供了制度支持。
1979年7月,全國人大通過了刑法等7部法律,這是改革開放后“人心思法”的第一批成果,并啟動了一個延續至今的“立法時代”。到2008年,我國現行有效法律已有229件,地方性法規7000多件,現代法律體系基本成型。從“無法可依”到“有法可依”,人大居功至偉。
更實質的變化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后,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升溫,人大不再是一個僅具程序意義的“表決機器”,而是真正開始主導立法。198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修改草案時,爆發了人大歷史上第一次激烈的立法爭議,導致該法歷經三審才出臺,成為人大改變“橡皮圖章”形象的重要起點。時至今天,凡是部門利益冒頭、保護公民權利不力的立法案,無不在各級人大引發爭論,遭遇阻擊。1999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公路法》修訂草案時,由于委員們普遍擔憂征收燃油稅將增加農民負擔,最終否決了這件本擬通過的法律案,成為人大立法史上的破冰之舉。
與人大立法相比,人大的監督、人事任免等行權實踐,更令人見識了民主的力量。
1980年8、9月間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170多名人大代表就寶鋼工程向冶金部提出質詢。全國人大歷史上的第一起質詢案發生在改革開放后不久,本身就喻示著政治正在走向民主和開明。此后,日益增多的爭議打破了人代會的“溫吞水”狀態,頻頻出現的反對票也改寫了“一致通過”的“慣例”。1992年召開的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興建三峽工程的議案引發激烈爭議,近三分之一的代表投了反對票或棄權票,以民主的方式對重大建設工程行使決定權,一時傳為佳話。而1997年3月召開的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表決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時,更是出現了1009張反對票、棄權票,占總票數的40.4%。地方人大的行權實踐同樣精彩紛呈。1985年,湖南省部分人大代表因不滿湖南省副省長楊匯泉清理整頓公司不力且對代表質詢敷衍了事,提出罷免案并獲通過;2000年,廣東省人大代表就“四會電鍍城”事件質詢省環保局,場面極為火爆,并建議撤換省環保局副局長;2001年,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腐敗窩案引發人大代表強烈憤慨,盡管某些領導反復“打招呼”、“做工作”,但市中院工作報告依然在人代會上被無情否決,開創人大監督史上的先河;2005年3月,廣州市人大代表在人代會上數次質疑政府預算,掀起轟動全國的“預算風暴”……這些傳誦一時的標志性事件,無不見證著人大行權的民主足印。
人大整體權威崛起的同時,人大代表的履職能力、政治勇氣亦在成長。1983年的全國人代會僅僅收到61件議案,到 2004年則創下了1374件的歷史記錄,坊間昵稱的“議案大王”、“建議大王”不斷涌現;人大制度重建之初,“只說好話”還是人大代表的常態,時至今天,“無畏代表”、“直言代表”、“放炮代表”與日俱增,許多人大代表已完成了從“頌歌”向“諍言”的轉型;30年前,人大代表在百姓眼里只是一個榮譽符號,如今,“有事找人大代表”已漸漸成為社會共識。
遼寧省、沈陽市兩級人大代表馮有為,數次在人代會表決時孤獨地舉手,勇敢地投出唯一的反對票;浙江的全國人大代表周曉光自費8000元發布向選民征集議案的電視公告;廣東的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陳雪英在人代會閉會期間,以一紙緊急建議擋住了五大銀行的“霸王式收費”……這些富于個性的人大代表不斷進入公眾視野,激發了全社會對于民主的深層思考。
從歷史的觀點看,30年前人大制度的鳳凰重生,既是改革開放的時勢產物,也是中國走向現代憲政和現代國家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倘若沒有人大的崛起和持續變革,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法治進程必然大大延遲。自然,人大的民主實踐并未盡善盡美。如何在人大選舉中融入更多的競爭性?如何改善“官員代表”過多的代表結構失衡現象?如何改變人大監督相對乏力的現狀?如何妥善“磨合”人大和執政黨、人大和政府之間的關系等等,都是人大制度改革不可回避的大問題,也是人大制度既要堅持、也要完善的基本理由。
經歷了30年改革風雨后,中國當下已進入深化改革、矛盾凸現的轉型期,亟須建立更加完善的政治規則和民主平臺,以避免社會動蕩甚至是“街頭政治”的危險。可以預料,人大的制度變革和行權實踐將是今后政治改革的突破口,也是推進憲政民主和現代公共政治的必由路徑。
路線3:“控權”、“擴權”,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的歷史變遷
1988年3月,一位叫包鄭照的浙江農民因不服強行拆除其樓房的行政處罰決定,將蒼南縣政府告上法庭。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起“農民告縣長”案,長期信奉“民不可告官”的中國社會為之震驚,更為之沸騰。富于歷史巧合的是,此時,為“民告官”提供強大制度支持的《行政訴訟法》正在悄然制定中。
1989年4月,全面確立“民告官”制度的《行政訴訟法》正式問世,這是中國推進政治民主、走向現代法制的里程碑事件。同時也標志著,固守多年的威權主義行政傳統開始走向式微,以程序公正、行政民主為核心價值的制度革命拉開了序幕。
1994年,《國家賠償法》出臺,行政侵權的受害者從此有權得到實質性補償;1996年,《行政處罰法》出臺,“十頂大蓋帽管一頂小草帽”的荒誕退出歷史;1997年,《行政監察法》出臺,行政權內部筑起了一道監督堤壩;1999年,《行政復議法》出臺,又一條“民告官”道路得到法律確認;2003年,《行政許可法》出臺,奏響了“審批經濟”的挽歌。此后,《行政強制法》《行政收費法》等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步伐亦在快馬加鞭。時至2008年,《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施行,制度保障向知情權、監督權等更高層次的民主權利邁進……
近20年來,由《行政訴訟法》引領的這些制度變革,清晰呈現了“控權”與“擴權”的雙重軌跡,所謂“控權”——政府權力日益受到控制,所謂“擴權”——公民權利不斷得到擴張。
這些拆筋動骨的制度變革,喚醒了無數公民的民主意識和權利訴求。以行政訴訟為例,《行政訴訟法》施行18年來,“民告官”案件數已超過百萬,“民”的勝訴率約為三至四成。時至今天,幾乎所有中央部委都曾被推上了被告席,有的甚至被告十多次。而近年來成為公共話題的一些“民告官”案件,諸如2002年的陜西“夫妻居家看黃碟”案,2005年的深圳公安機關懸掛“堅決打擊河南籍敲詐勒索團伙”橫幅而引發的“地域歧視”案,以及《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后接踵而至的“信息公開”案等等,無不彰顯著公民權利的尊貴,以及平民百姓以法維權、以法“治官”的勇氣,對于“懼官”、“畏訟”傳統根深蒂固的中國社會而言,這樣的變遷在30年前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方面,政府部門的行為模式和思維定式亦為之改變,向來權威赫赫的行政機關開始學會謙卑和謹慎,一貫“不拘小節”的行政執法者開始小心翼翼地尊重時限、程序等細枝末節。《行政處罰法》實施不久后的1998年1月,因四川省聚酯股份公司不服國家環保總局的處罰決定,在成都市召開了首例針對中央國家機關的行政處罰聽證會。為了總結執法得失,時任國家環保總局局長的解振華親自出馬部署,四川23個地市州的環保局長全部趕赴現場旁聽,行政機關提高執法水平的意識由此可見一斑;時至2008年,隨著《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從汶川地震、三鹿“問題奶粉”到貴州甕安等地的群體性事件,再到頻頻發生的礦難、食品安全、工程事故、出租車罷運等“敏感”信息,無不及時公開,對于一個有著數千年“密室政治”傳統的國度而言,這樣的變遷堪稱翻天覆地……最近20年來,諸如此類的政府自我革命數不勝數、日積月累,促使一個全能型、封閉型、管理型、威權型的政府逐漸轉向有限政府、透明政府、服務政府和法治政府,而政府轉型的原始動力和關鍵推手,正是以民主化為軸心的公權變革。
從“政府老大”到“民權至上”,從“官貴民賤”到“以民為本”,從威權行政到民主行政,從“暗箱行政”到政治開放……以“控權”、“擴權”為導向的制度變革,對社會觀念的改造,對政府與公民之間關系的重新定位,對公共權力和公民權利的平衡和調整,乃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偉大的社會變革之一,并從根本上牽引了依法行政、政治民主的歷史進程。時至今天,盡管一些行政機關的民主觀念依然淡薄,不少公民的權利意識依然匱乏,政府與公民的強弱對比依然有待改善,行政訴訟、國家賠償實踐也不盡如人意,但約束公權、解放民權的改革大勢已不可阻擋。
隨著社會轉型期階層分化、利益沖突的加劇,政府作為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必然集中承受各種壓力,公權行使稍有不慎,社會矛盾便會演變成官民沖突。近期在貴州甕安、云南孟連等地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公權失范、民權受抑的“積累效應”所致。正因此,在制度層面進一步規制公權、保障民權,并在實踐層面真正落實這些政治規則,借民主之力實現行政公正、官民和諧之目標,依然是改革開放30年后的核心議題。
路線4:司法民主,力推司法公正
1998年7月11日,一檔電視節目吸引了無數正在度周末的百姓。這天上午,“八一”等十大電影制片廠訴兩家音像企業侵犯版權一案,在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中央電視臺覆蓋率最高的第一套全程直播了此次庭審。5個多小時內,法官的審案風采,原被告及其律師之間的唇槍舌劍,原汁原味地搬上熒屏。據事后統計,此次直播收視率高達4.5%,超過了不少熱門電視劇。
法制重建伊始的上世紀80年代初,曾經電視直播了對林彪、江青兩大集團的審理。上世紀90年代中期起,一些地方電視臺也開設了錄播、直播庭審的專欄節目。但中國著力構建現代司法機制的時代背景,卻使1998年的這次全國性庭審直播引起了格外關注,海內外輿論普遍稱其為“滿足公民知情權,以司法公開促司法公正”的標志性事件。以此為拐點,電視媒體與司法機關步入了空前的蜜月期,各地庭審直播節目如雨后春筍。1999年初春,中央電視臺再度直播了重慶綦江虹橋垮塌案的庭審,“豆腐渣”工程一時成千夫所指。時至2004年11月,北京朝陽區法院在全國首次網上直播了一起噪音污染案的庭審,庭審直播開始邁向網絡化。
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風行一時的“庭審直播”,是司法領域極為獨特的社會現象。它標志著,長期列為司法禁區的審判公開原則,開始由憲法原則真正落到實處。伴隨著“庭審直播”的“眼球效應”,審判公開的理念開始深入人心,向來神秘的司法面紗漸漸揭開。
事實上,司法民主化始終是改革開放后司法改革的一條主線,在“庭審直播”之前,許多推進司法民主的制度變革早已啟動。
1980年,廢棄多年的律師制度重新恢復。此后,《刑事訴訟法》《律師法》的制定或修訂不斷擴張著律師的執業權,律師隊伍也由最初的212人猛增到目前的13萬多。正是因為律師群體全面介入訴訟、尤其是刑事訴訟,在司法體系中設置了民主制衡的理性力量,才降低了冤假錯案的幾率,維護了司法公正。
上世紀80年代末期試點、1996年全面推開的由“糾問式”轉向“控辯式”的審判方式改革,在司法改革史上至為關鍵。“控辯對峙,法官居中”的新庭審模式不僅根治了“先定后審”等司法弊端,更重要的是使當事人擁有了更多的發言權,建立起了更加平衡的訴訟民主機制。這一改革也使庭審成為檢視司法公正的焦點,為“庭審直播”做了先期準備。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就已確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是體現司法民主的最直接形式,但“陪而不審”等現象,卻使這一機制名存實亡,甚至引發了持續多年的存廢之爭。2004年8月,《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頒布,這既是復興人民陪審員制度的重要拐點,也清晰表達了堅持司法民主的基本立場。
改革開放以來,被海外譽為“東方一枝花”的人民調解制度,針對困難群體的法律援助制度,監督檢察工作的人民監督員制度,以及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旁聽庭審等機制,無不增添了司法的民主色彩。
不過,隨著司法改革的日益深入,司法民主與司法獨立、司法“平民化”與司法“職業化”之間的內在沖突,也日益成為學界、坊間的爭議話題。而民意、輿論對一些重大案件的影響,尤其令人喜憂參半。
2003年,湖南女教師黃靜裸死案發生后,先后出現了6份結論不一的司法鑒定書,輿論為之大嘩,司法鑒定的公信力成為眾矢之的,最終促成了2005年司法鑒定體制的全面變革;從2002年起不斷曝光的多起“槍下留人”案,以及聶樹斌案、佘祥林案等冤案,將死刑復核問題不斷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在民意的強力推動下,最高法院于2007年收回了死刑復核權,成為朝野雙方在重大人權問題上良性互動的典范;從2007年11月起,許霆惡意取款案引發全國熱議,短短4個月內,許霆案由“無期徒刑”銳減為“5年有期徒刑”,沸騰的民意糾正了司法機器的明顯偏差。
在推動司法公正和制度變革的同時,民意也產生了令人不安的效應。早在1997年8月,在河南鄭州某公安機關擔任要職的張金柱酒后逆行駕車,將一對父子當街撞成一死一傷。經媒體曝光后,激起社會公憤。盡管不少法學專家和律師認為張金柱罪不該死,但民間、媒體的喊殺聲卻此起彼伏,張金柱最終被判死刑。耐人尋味的是,此案判決書出現了“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之類的非法律用語,而張金柱臨刑前亦留下遺言:“我是被記者殺死的。”
民意和輿論是否會不當干預、影響司法,在張金柱案判決后首次引發了廣泛討論,但困惑并未就此消除。2002年4月至2003年12月,遼寧“黑老大”劉涌從死刑改成死緩,又變回死刑,洶涌的民意幾乎主宰了劉涌命運的起伏,以至有學者感嘆:“程序正義之艱難,既有來自行政權力的干涉,也還有來自民間的道德抗議”;而2006年邱興華特大殺人案發生后,一些法學學者要求對其進行精神病鑒定、維護程序正義的呼吁,同樣被強大的民意所擊潰。
與其他領域相比,司法領域的民主化顯得更為艱難和復雜。一方面,保障律師執業權利、深化審判方式改革、落實陪審機制等基礎性制度仍有待加強。另一方面,面對輿情民意與法律規則、道德激情與司法理性、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之間的種種沖突,如何尋找到合理的平衡點,對司法民主構成了嚴峻考驗。但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未來的司法民主化改革如何演進,司法公正都是其最終目標。
路線5:傾聽民意,公共決策民主化漸成潮流
2008年11月14日,經過長達一個月的公開征求意見后,新醫改方案共收到35260條公眾意見,這將成為進一步完善新醫改方案的重要依據。
與公眾利益息息相關的公共決策步入“草根”社會、傾聽民間訴求,已成為公共治理的常態。這與以往閉門造車甚至長官拍板的決策模式形成了鮮明對比。同樣以醫改為例,上世紀90年代起推行的“產業化”醫改方案,并沒有經過充分的公共討論,對日后的“看病難、看病貴”等社會問題難辭其咎。
追溯起來,價格聽證制度的引進,是改革開放后政府行政決策民主化的一個重要起點。1993年,深圳率先實行價格審價制度,成為價格聽證的雛形。1997年出臺的《價格法》以法律形式正式確立了價格聽證制度,此后,價格聽證會在各地漸次推開。
2001年8月,南京舉行液化氣價格改革聽證會,經聽證代表據理力爭,為居民減負300多萬元;這年年底,廣東舉行公路春運調價聽證會,上浮95%的原定方案調整為65%;20多天后的2002年1月,浙江的公路春運調價聽證會重演了這一幕,因多數聽證代表堅決反對,上浮30%的預案縮水近半……借助價格聽證這一平臺,平民百姓對向來由壟斷企業把持的公用價格有了發言權,而展現各方利益公平博弈的聽證過程,亦培育了公民的民主意識和素養。
2002年1月,第一個全國性價格聽證會——鐵路價格聽證會在北京舉行。此后,民航、電信等“價格堡壘”紛紛被攻破。時至今天,全國所有省會城市均已舉行過價格聽證會,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水電氣、交通、教育、醫療、景點門票等等無不納入聽證議題。十多年前國人聞所未聞的價格聽證,已成為中國社會的流行詞匯,成為公眾最熟悉的一種民主參與方式。
以價格聽證為先導,聽證、咨詢、協商等民主機制開始逐步運用于行政決策。近年來更重大的變化是,無論是制定行政法規、政府規章,還是醫改、節假日安排、燃油稅改革等涉及民生的重大公共政策的調整,“征求民意”已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普遍姿態。
在立法領域,決策民主化同樣高歌猛進。1987年黨的十三大召開后,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升溫,一度封閉的立法活動開始走出“密箱”,以往嚴格保密的立法草案開始在媒體上公開討論。經過立法公開的“預熱”,開門立法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起蔚然成風。隨著2000年《立法法》的出臺,立法聽證等種種民主機制得到確認。
1999年9月,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就《廣東建設工程招標投標管理條例》修訂草案舉行了國內首次立法聽證,進而引發了各地的“立法聽證潮”。2005年9月,全國人大就個稅起征點問題舉行了全國人大歷史上首次立法聽證會,成為“民主稅政”的標志性事件。
公民旁聽立法會議、公開征集立法項目……頻現各地的種種實驗,不斷豐富著立法民主的內涵。各級人大普遍推行的公布法律、法規草案征求公眾意見,更是掀起了一場場“全民立法運動”。2001年新《婚姻法》草案公布后所引爆的新舊觀念大戰,2005年《物權法》草案公布后所激發的民間議法熱潮,2006年《勞動合同法》草案公布后創紀錄的19萬多件立法建議等等,無不成為難忘的公共記憶。時至2008年4月,履新不久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始推行法律草案“全公開”,從此“人人都是立法者”。
歷經多年積淀,近年來公共決策民主化已呈現出兩大趨勢,一方面,決策機關的開放姿態引導公民越來越廣泛地介入公共決策,另一方面,自發性的民意表達也在不斷激活制度性的公眾參與,影響乃至改變了公共決策。
2003年《道路交通安全法》出臺后,有關事故責任認定的條款引發坊間經年不息的爭議,促使北京等地通過征求市民意見、召開立法聽證會等民主渠道,出臺了更具民意基礎的地方交通法規,并推動國家立法機關于2007年修改完善了相關條款;2005年“圓明園湖底防滲膜事件”中,學者、民眾、民間環保組織與公共媒體的共同吶喊,促成了環保總局的首次環評公眾聽證會,不僅阻止了一場生態災難,亦推動環評從此成為公眾參與最為活躍的領域;2007年“廈門PX風波”中,民間訴求的強大壓力,敦促當地政府啟動了公眾座談會、網絡投票等民主程序,消除了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緊張,民意表達亦由對抗性的“散步行動”漸漸轉向理性建言。最終遷建PX項目的決策轉變,更是成為尊重民意、決策民主的里程碑事件。
改革開放30年來,封閉型、壟斷化的傳統決策模式逐漸讓位于開放型、民主化的現代決策機制,乃是公共治理最重大的變遷之一。與此同時,借助公眾參與等機制,公共權力與民間社會開始孕育出良性互動的“共同治理”結構,推動代議民主、間接民主向參與民主、直接民主演進,這將深刻地影響中國民主進程的未來走向。
必須正視的是,諸多民主決策機制的象征意義還遠遠大于其實際效用。以起步頗早的價格聽證為例,由于許多價格聽證會缺乏公正性甚至被暗中操縱,多年來輿論批評極為激烈,社會公眾也由最初的興奮轉為失望,甚至將聽證會與“漲價會”劃上等號。此外,一些公共決策盡管經過了征集民意之類的民主程序,但并未對民意予以足夠尊重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也難免存在“民主秀”之嫌。盡管有著這些現實弊端,但公共決策民主化已不可逆轉,未來改革的核心議題是:通過改良民主技術和轉變治政理念,促使形式民主真正走向實質民主。
路線6:吏治“新政”,從“公推公選”到問責政治
“治國先治吏”是中國古訓,現代公共治理亦依托于具備合格從政能力和道德的官員階層。改革開放后,干部制度的民主化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議題,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后,改革步伐驟然加快。
最初的突破來自基層。1998年,四川省遂寧市步云鄉由全體鄉民投票“直選鄉長”,破冰之舉轟動一時,但由于與“鄉鎮長由鄉鎮人大間接選舉”的法律規則相抵觸,“步云試驗”廣招爭議,最終被叫停。
不過,探索的腳步并未停止,改革姿態亦由激進轉向理性,致力于在制度框架內尋求突破。從上世紀90年代末期起,深圳市龍崗區大鵬鎮民主推選鎮長候選人、山西省臨猗縣卓里鎮兩票選任鎮政府主要領導、湖北省京山縣楊集鎮以“海選”方式推舉鎮長候選人等實驗紛紛亮相,盡管做法不同,但共同特點是“從多數人中選人、由多數人選人”,日后統稱的“公推公選”改革即由此發端,其普遍流程是,采取個人自薦、群眾舉薦和組織推薦相結合,通過考核、演講、答辯等程序,公開選拔領導干部候選人,再依法舉行選舉或組織任命。這是在堅持“黨管干部”原則和人大依法選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擴展官員選拔的民主性。
2002年后,“公推公選”由鄉鎮一級向上突破,競爭上崗等諸多改革亦風起云涌,走在前列的省份甚至被海外媒體稱作中組部的改革“試驗田”,江蘇尤其成為改革重鎮。2003年12月,江蘇沛縣產生了全國首位“公推公選”的縣長;半個多月后的2004年1月,南京市白下區、雨花臺區“公推公選”出兩區區長,再開全國先河。從鄉鎮長到縣長再到副廳級區長,江蘇“公推公選”三級跳僅耗時半年,改革力度令全國矚目。
以“公推公選”為表征的官員選拔機制改革,使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改革理念深入人心,撬動了“小圈子選人、選小圈子人”的官場生態,這對任人唯親甚至買官鬻爵等官場腐敗,無疑是釜底抽薪之舉。
與此同時,對在任官員的政績考核亦注入了越來越多的民意因素。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通過民意調查、網上評議等手段,各地“民評官”實驗此起彼伏,其中不乏“萬人評議政府機關”之類的壯舉。
真正的要害在于,公眾評議意見往往跟進著官員職務升降等獎懲措施,一些庸碌無為的“太平官”盡管無過,但因為評議排名靠后,照樣官位不保。2003年,江蘇省泗陽縣在國內首次評選最差政府部門和政府官員,2個政府部門和9名政府官員上了“黑名單”,震動效應輻射全國;2005年,江蘇省濱海縣推出“民主彈劾干部制度”,人大代表、黨代表乃至普通公民均有權對工作不稱職的干部進行彈劾,因彈劾去職者3年內不得擔任同一職務;江蘇省徐州市自2003年起組織市民評議機關作風,5年間已“真刀真槍”評“掉”12名局、處級官員的官職……“民評官”不僅改寫了官場的生存規則,而且也推動了問責政治的勃興。
“官員問責制”是建設“責任政府”、“民主政府”的核心標志,這一機制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起已開始孕育,但2003年“非典”危機時才全面激活,情勢岌岌可危之際,中央政府啟動了建國后首次大范圍、大規模的“問責風暴”。
“非典”危機后,行政問責開始廣泛踐行于公共行政領域。2003年至2007年,對重慶開縣井噴事故、北京密云縣公園踩踏事故、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商廈火災、廣東興寧市大興煤礦透水事故、山西洪洞縣新窯煤礦瓦斯爆炸事故等等負有責任的一大批官員,相繼引咎辭職或被撤職、免職。2005年《公務員法》出臺后,官員問責制在法律層面首次得以確立。
進入2008年,甕安事件、三鹿“問題奶粉”、山西襄汾潰壩事故、深圳龍崗區舞廳火災以及一些地區水污染、礦難、出租車罷運等危機事件接踵而至,繼“非典”之后的新一輪“問責風暴”迅速刮起,數10名責任官員以令人眼花繚亂的速度紛紛落馬。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此次“問責風暴”不再局限于“事故型問責”,一些日常執政不佳或應對危機不力的“庸官”亦被擼去烏紗帽。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主動請辭、“非典”時就曾被問責的山西省省長孟學農二度去職,更標志著高官不擁有任何問責豁免權。被坊間稱為“行政問責年”的2008年,整肅吏治的力度史無前例,成為問責政治的一個歷史性拐點。
改革開放30年來,沿著選拔、考核、問責等各個緯度,官員制度改革引發了雙重效應:一方面,民眾對官員的選擇權、知情權、監督權不斷擴大;另一方面,做官的“門檻越來越高,權力越來越小,責任越來越重,風險越來越大”,官員階層對權責對等、權力來源等問題,都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借由這些深刻的變遷,公共治理和執政行為向民主、民本、民權的方向日趨演進。
不過比較而言,干部制度依然是政治改革的最大難點之一。無論是“公推公選”還是民主評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政治實驗,并未形成長效性的制度安排,有些甚至有走走過場的作秀嫌疑。尤其是,民眾強烈的民主訴求與現行法律規則之間的沖突,以及一些地方日趨嚴重的買官賣官現象,都在呼喚著進一步擴大“選官”民主的制度調適。就官員問責而言,除了一些黨政條例和《公務員法》的簡單條款外,同樣缺乏完善有力的制度支持。除了行政機關內部“同體問責”外,也亟須推進由人大、政協乃至社會公眾操作的“異體問責”。所有這些,都是留待未來的改革懸念,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民主化”依然是官員制度改革最重的砝碼。
(作者系《民主與法制》雜志主任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