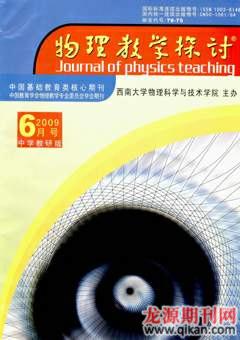可再生與可持續能源篇(上)
作者簡介:歐陽鐘燦,理論物理學家,1968年畢業于清華大學自動化系,1984年獲得博士學位,1997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2003年當選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擔任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會理事會副理事長,北京市科協常務理事,中國物理學會常務理事、液晶物理分會會長,國際刊物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B,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Theoretical Nan science, SoftMaterial以及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of Liquid Crystals的編委。他在軟凝聚態物理、統計物理等領域作出了多項貢獻, 在國際著名刊物發表論文100多篇,出版英文專著l部 Geometric Method in the Elastic Theory in Liquid crystal Phases (合著),并將其擴增為中文版《生物膜泡曲面彈性理論》。
一 、21世紀物理學必須面對能源和氣候問題
21世紀: 物理學從“大科學”向“小科學遍地開花”轉變;
半導體的發明促成人類進入信息技術(IT)時代;
人類期待的能源無虞原子能時代沒有到來,反而面臨能源短缺與氣候變暖;
研究經費向可再生能源、可持續能源的研究傾斜。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20世紀都是物理學帶動世界科學技術大發展的時代。內燃機、電氣化、無線電、飛機是20世紀前十年世界技術進步的象征,它們都是基于19世紀物理學基礎研究的成就,如統計物理與熱力學、麥克斯韋爾的電磁場理論、流體力學等發展起來的。它們大大地解放了人類的生產力,提高了人類的生活水平,因此,列寧給人類的理想社會--共產主義下了一個著名的定義:“蘇維埃加電氣化”。
20世紀初期,物理學的兩大發現,普朗克的量子論與愛因斯坦提出的相對論更是為人類向自然索取提供了無限可能性,愛因斯坦的質能關系E=mc2,使我們懂得一火柴盒的鈾釋放的能量可以抵過好幾列火車的煤。但是,20世紀并沒有帶給我們憧憬的不用為能源發愁的原子能時代,二次世界大戰及其結束后持續多年的冷戰,把最優秀的物理學家幾乎全部集中到國防及武器裝備有關的研究,超音速飛機、人造衛星、宇宙飛船、雷達、激光、計算機、核裂變和聚變等20世紀物理科學的尖端技術無不帶有這種背景。在這種集中支持架構下,如美國NASA(宇航局)與DOE(能源部,原先是專為發展原子武器的AEC),帶給基礎物理研究“大科學”的特點。但冷戰結束后,大科學的統治地位受到挑戰,美國SSC(超導大型加速器)的廢止便是一個例子。而這種趨勢到21世紀愈演愈烈,費米實驗室在2007年遭到一次巨大打擊,甚至準備裁員200人。在美國國會2008年度財政撥款中,國際直線對撞機(ILC)的研發經費比預期減少了75%,這些經費轉而投入可再生能源、清潔煤燃燒等方面的研究。而從2007年10月到2007年底,負責ILC設計的費米實驗室已經花完了剩下的25%經費。同時受到影響的還有美國SLAC的B介子工廠,將比預計提前7個月結束取數。在2008年度的預算中,美國國會不顧總統提出的不增不減的預算需求,堅持將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核能的研發經費增加30%,達到約13億美元;清潔煤和其他化石燃料的研發經費增加了13%,達到5.57億美元。然而,盡管核能項目的總體經費有所增加,布什總統提出的“全球核能合作計劃”的預算需求卻被削減一半以上,只獲得了1.81億美元,該計劃旨在促進核廢料的回收處理研究。能源部科學辦公室也深受打擊。雖然其總體科學經費增加了4.6%,達到40億美元,但絕大部分增加額均用于超級計算機和生物學研究。國會不僅扣留了能源部承諾為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ITER)提供的1.6億美元經費,而且還大刀闊斧,將國際直線對撞機的經費從6000萬美元調到1500萬美元。另外,英國也從ILC的R&D;研究中撤出。美國國會2008年度財政撥款還同時撤出了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ITER)項目中美國應承擔的部分。可以預見,LHC開始運行后,世界高能物理實驗研究的中心將轉移到歐洲。物理“大科學”開始向“小科學遍地開花”的局面轉移,戰爭時代為通信、精密測量服務的半導體研究流向民用企業,并得到了極大發展,巴丁發明的三極管促成了集成電路的誕生,為21世紀的信息化時代順利到來打下了物質基礎,使IT(Information Technology)出現了摩爾定律:每18個月電腦的成本下降一半。2007年是半導體發明60周年,也是超導理論發現50周年,而巴丁在這兩個領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并因此獲得兩次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至今唯一一位在同一學科兩獲諾獎的科學家。
但是,依靠大科學的核裂變、聚變的研究, 進入新千年仍然沒有給人類帶來能源無虞的原子能時代。相反,2005年2月簽署的二氧化碳減排的京都議定書,2007年底的聯合國巴厘島氣候變化會議,以及由美國前副總統戈爾與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小組(IPCC)分享的2007年度諾貝爾和平獎——“人類只有一個地球”,進入21世紀的前十年的一系列牽涉所有國家的環境氣候變化問題都能讓人感到,人類生存環境的問題愈來愈成為世界的焦點。在確保能源供應無虞、促進經濟持續增長以及環境保護議題上,現今科技還無法提供必要解決方案的想法。能源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世界每個國家都極其重要。在人類未來50年所面臨的十大問題中,能源首當其沖。如果世界人口以目前的增長率繼續增長的話,到2050年世界人口將從現在的63億增長至100億。按照我們現在的了解,還沒有足夠的能源來滿足100億人口的需要。世界每天都在使用越來越多的能源,我們正在耗盡地球的能源。因此,必須采取果斷的行動來改變這種現狀。我們不能僅僅從經濟利益出發使用現階段相對廉價的化石燃料,而應該從保護資源和環境的考慮出發,盡量少使用化石能源,盡可能使用無污染的可再生能源。
二、物理學在應對環境和能源的挑戰下應該如何發展
物理學已經為IT服務了50年,現在要從IT轉到ET;
老一輩物理學家的重托:中國的核聚變不要緊跟國外;
P. 安德森:20世紀最后10年的青年研究者正在受SCI拖累。
21世紀物理學的發展目標就是國際純粹應用物理聯合會(IUPAP)的觀點--物理學研究要聯系能源和氣候問題。2007年,IUPAP副主席陳佳洱院士從巴西帶回了一封IUPAP主席關于能源問題的公開信,其中提出物理學要注意兩件世界大事:能源短缺和氣候變暖,認為物理學如果不參加進來,將很可能被邊緣化。IUPAP在其關于能源和氣候問題的報告中專門提到中國、印度、巴西的經濟發展對世界能源的壓力。2007年10月舉行的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新一屆學術委員會第一次大會,北京大學甘子釗院士提出一個建議:物理學已經為IT服務了50年,但是現在要從IT轉到ET,即服務能源(Energy)和環境(Environment)科技。兩彈一星功勛獎獲得者彭桓武先生在去世前最關心的問題就是能源,認為物理不能只關注純粹的理論,還要關心國家需求。1990年,他在《物理》雜志發表文章就預測21世紀物理兩大發展方向之一就是發展核聚變。在他晚年的研究中,他認為慣性約束與磁約束已經走過了沒有結果的半個多世紀,因此,他號召中國的核聚變不要緊跟國外,而要有自己的獨創。近年,世界著名的開展交叉學科研究(包括生命科學、復雜性與新能源)的美國圣塔菲研究所在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連續舉辦了四次國際暑期學校,為此他很有感觸地對筆者說,他現在非常后悔的是當他們從國防研究退出來時,沒有像美國同行那樣辦一個圣塔菲這樣的研究所。理論物理所何祚庥院士也為發展我國可再生能源呼吁了多年。在2008年院士大會的報告中,他對ET中“E”的意義有了擴充,加了Ecology Technology(生態技術),并提出歸根到底是第四個“E”,即Economy,物理學要服務于經濟建設。
事實上,國際上的老一輩科學家都注意這個問題。199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美國圣巴巴拉加州大學(UCSB)理論物理研究所(后來的Kavli理論物理研究所)首任所長,凝聚態物理學家沃爾特?科恩,最近幾十年來一直關注能源問題,其自費制作的紀錄片《太陽的能量》已在世界范圍內無償發行。2006年訪問我所時,應他要求,何祚庥院士曾聯系一位CCTV的有關人員與他洽談播放他的制作,但這種不賺錢的義舉最后是否被接納?筆者就不得而知了。令筆者感動的是,當時他還要筆者給他找無錫尚德公司的老總施振榮博士的電話,他要親自打電話向這位當時上市規模第一的太陽能公司表示敬意。事實上,2008年英國《新科學家》雜志第一期在評述2007年中國科技進展中,特別報道了無錫尚德公司施振榮博士對發展太陽能產業的貢獻及潘建偉等人在量子計算領域的重大突破。這表明中國物理學家在ET及未來的IT方面都作出了世界領先的貢獻。作為北京市邀請參加2007諾獎論壇的嘉賓,沃爾特?科恩于2007年9月13 日再次訪問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并作了題為“全球能源-氣候挑戰:各方反應概覽”的學術報告,分析了全球變暖正廣泛地改變著地球的事實以及科學、政治、經濟等各方對這一挑戰的反應。
為什么這些年過八十的老一輩物理學家對能源問題這么關注,而多數年輕的物理學家對此少有關心?這里可用諾貝爾物理獎得主P. 安德森在L. M. Brown, A. Pais, Sir B. Pippard主編的《20世紀的物理學》一書第28章的文章《20世紀物理學概觀》中的一段話來解釋:“與二戰后早期研究學者出于好奇心執著于發現自然奧秘的人生觀已截然不同,尤其是20世紀最后10年,年輕研究者的競爭已失去科學發現本質的客觀公平判斷,代之而起的評價標準是獲取科研經費的多少,在Phys. Rev. Lett. 發表論文,在Nature、Science及Physics Today新聞欄目被報道就是贏家”。在這種利益驅動的“量化”評價壓力下,很難讓年輕人去思考、從事真正重要的研究項目。由此可見,SCI并不是專門的“中國人的愚蠢指標”。P. 安德森的話使筆者想起彭桓武先生在去世前請我幫他找研究特殊核聚變的年輕合作者提出的條件:“這個人已升教授,不需要再發表許多文章。”可見,要使青年研究者從IT到ET轉變,就一定要打破SCI的緊箍咒。
(欄目編輯廖伯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