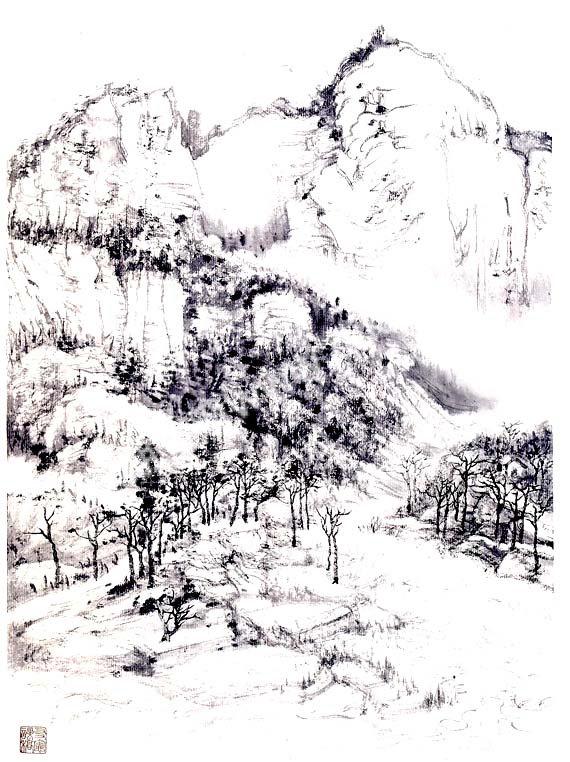重溫老舍先生論中國畫
編者按:老舍先生60年前一篇評述傅抱石大師畫藝的文章,引起了著名畫家張友憲先生的共鳴,于是有了這篇和學生的對話:老舍先生的崇論閎議,錚言快語;友憲先生的鞭辟八里,深刻、明敏,在美術批評與研究已經異化的當下,顯得彌足珍稀。如果說老舍先生的書學畫論歷久不衰、精義日新,那么友憲先生對此的體悟、闡釋和鉤遠致深,具有別樣的意義。
學生(以下間作問):張老師,我們進來常看到您畫案上擺放這篇文字,上邊用紅筆劃了許多道道,旁邊又加了注,能就此給我們談談嗎?
張友憲(以下簡作答):好。這是一篇60年前(1947年10月26日)老舍先生發表在上海《大公報》上的短文。我不久前才發現,一讀之下倍感親切,與我的心意完全相通,是老舍先生關于中國畫的一篇精論!對照當今中國畫壇,極具現實意義。比如:在熱鬧的繪畫市場,如何判斷作品的質量與價值?老舍先生的文中有這樣一句話:
從藝術的一般的道理上說,為文為畫的雕刻也永遠是精勝于繁;簡勁勝于浮冗。
我們知道,中國大部分藝術品藏家是弄不清什么樣才是真正的好畫的,一般都是把“精”等同于“繁”,于是多數畫家只往“繁”里畫,不向“精”中求,就成了一個最大的現實。
問:那么我們應該怎樣看待老舍先生的“精勝于繁”;簡勁勝于浮沉”呢?


答:老舍先生這里的“精”是對應于“簡勁”,“繁”是對應于“浮冗”的,因為,繁密的畫也可以畫得很精嘛,這首先要搞清楚。對于畫家的職業道德而言,“精”的解釋應該是對待每幅作品的專心程度,所謂用功極深,精研而后精通,你的一筆一墨才能畫得純粹(只考慮錢的藝術創作不可能純粹)。詞典中“精”的解釋有一條叫“完美”,我們雖不能要求件件作品都很完美,但是你們看:“完美”的定義是要做到最好,所謂精益求精(既對藏家負責,更對自己的藝術生命負責)。
“簡勁”一詞就非常專業了。“簡”在藝術中首先意味著選擇。簡是繁的反面,不要求復雜和煩瑣,但一定要到位,所謂“言簡意賅”。“勁”是力的使用方法,所謂“談筆力要懂勁”,這可能是由武術中引用過來的。讀畫者說“這畫帶勁”時,往住就是被其作品中的積極興奮的精神所感染了。至于“浮冗”,“浮”者表面也,空虛不實在。一根線條拉出來,不沉著若浮萍無根而飄者也。故老舍先生這樣寫道:
真正的好中國畫是每一筆都夠我們看好大半天的。
冗者多余。一幅畫上到處是不起作用的東西,毫無價值。可是非要讓外行看懂這些是不日月智的,只能是畫家們來認同老舍先生的“精勝于繁,簡勁勝于浮冗”。
問:老舍先生是文學家,他也精通中國畫嗎?
答:拜讀過老舍先生這篇文章的人,就會認為他精通,還會認為他高屋建瓴,更會感受到當下的美術理論家在對待中國畫的繼承發展問題上很難有與之比肩者。老舍先生此文可謂字字珠璣。比如他上來就用了一個“硬”字,來表述他對中國畫線條的感受:
昔在倫敦,我看見過顧愷之的《烈女圖》。這一套舉世鐵崇的杰作的好處,據我這外行人看就是畫得硬。
問:您首先表示出對“硬”字的關注,為什么呢?用“硬”這個字是否準備?“硬”字該如何理解?
答:我剛讀到這個“硬”字時也是一怔。老舍先生把“高古游絲描”說成“畫得硬”,起先是很難理解,但再看他對“硬”的解釋是“每一筆都像刀刻的”,就豁然了。面對作品每個人都可能產生不同觀感,這讓我聯想到一句話叫“切膚之痛”,描述人受到某種刺激后的心理反應。注意,中國人是用生理反應來作描述的,就好比現在有句話“痛并快樂著”,由生理轉化為心理一樣。欣賞藝術,受其感染,由心理到生理產生某種反應是很普遍的現象。如果覺得過癮,大吼一聲,猛擊一掌,都不難理解,甚至有用刀去刻物體的欲念,想像一刀切過去的快感。這樣理解老舍先生的“硬”字,其實就是描述自己的一種藝術觀感。但然。老舍先生或許還有不為我輩所感知的內心體驗。此其一。其二,“硬”字明顯區別于“高古游絲”給人的視覺表象,深入或者升華到文化層面,體現出一種藝術的強度。如何做到這一點呢?老舍先生特別拈出中國畫的“筆力”二字來。中國畫講究“筆力”,以筆力成就的線具有一種穿透力。它深入到人心里頭去,能撩撥你的心弦。你一看到這根線就感覺到心里面那根弦被彈奏了起來,這就是藝術的魅力,或許就是老舍先生所謂的“硬”。很顯然老舍先生“硬”的感覺與“僵”和“板”是無關的,潘天壽所謂“強其骨”,所謂“力能扛鼎,言其氣之沉著也,而非笨重與粗悍是也”。孔子曰:“詩言志。”堅持“畫家不搞形式就是不務正業”者,可以畫出“美的裝飾”,卻無緣想見“美的原動力”。老舍先生從中國畫的主要表現形式看進去,一下子就把握到了繼承發展的關鍵,他說:
我喜歡一切藝術上的改造與創作,因為保守便是停滯。而停滯便引來疾病。可是在藝術上,似乎有一樣永遠不能改動的東西,那便是藝術的基本力量。假若我們因為改造而失掉這永遠不當棄舍的東西,我們的改造就只虛有其表,勞而無功。
問:如此說來,老舍先生是透過現象看本質,那么,中國畫的線條怎樣才能具有“藝術的基本力量”呢?
答:第一要有意識地去追求,所謂“出發點即是歸宿”。清人布顏圖講:“制大物,必用大器,故學之者當心期于大,必有一段海闊天空之見,存于有跡之內,而求于無跡之先。”就是這個道理。這里講的“大”字,在中國哲學中不是一個形容詞,而是個本體規定:大道、人象、大音、大器等等。這是中國文化(也是中國畫)傳統的龍脈。
第二要落到實處。在老舍先生看來,這個實處就是對于筆墨的錘煉。美術界有很多牽扯到中國畫筆墨的官司,我們都不要陷進去。我們應該抓緊時間做錘煉的功夫。我個人體會:錘煉筆墨,先正身形。欲正身形,先正心意。特別是作寫意畫,起始階段意守中正,才能筆正而畫正。一根線條,起行轉折,所依據的是什么呢?一、與物宛轉;二、書法用筆;三、自然隨性。一是根基,二是法度,三是境界,三者是個整體,可以單練,尤如佛家手中念珠,顆顆皆能轉動,睢線頭斷不得。
問:您要求我們做錘煉筆墨的功夫,可似乎又不局限于此。
答:“每一筆都夠看好大半天”的藝術,哪個問題不會同時牽扯到其余呢?就說上述的與物宛轉,作為造型它是根基,可作為莊子的美學觀點,那它的要求就高了,高到你經歷過二和三以后,最終全回到它上面來都可以。元人《移諸生論書法書》中有句話:“萬象生筆端,一畫立太極。”到了清初的石濤和尚那兒就叫做“歸于一畫”。
問:原來如此,現在很多畫中國畫的人都不練書法,您說的“二是法度”能是什么作用?
答:法度是規矩。雖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但天下事規矩定的太過了又會走向愿望的反面。作為處理事物手段的法,可以各式各樣,不同的法結不同的果。如若眾人皆取標準法,那必然結出相同的果。當然其中還有個程度問題。我本人對書法用筆的理解其實就一個字——寫。說它是“法度”僅說的是它的第一受義罷了。你們說很多畫中國畫的人不練書法,書法的法度就
對他不起作用?我不信。因為所有畫中國畫的人都受“寫”的約束,即便不練,他也得(合自己的法,才會有日后的變化之資。學畫者練書法最好懸臂中鋒,由篆切入,然后體會唐人孫過庭所論:“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以至“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悟到“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知“不入其門,詎窺其奧”的道理,只有游進書法之海,并與中國畫實踐相表里,方有望接近“寫”之真諦。
問:如果說“寫”的第一要義在掌握法度,那么,“寫”還有進一步的要求嗎?
答:有。無法時建立法度,有法后破其法度,大概可以視為藝術進取的不變定律。老舍先生這篇文章是專為傅抱石先生的畫寫的。據悉傅抱石作畫往往是涕淚交流,如醉如癡一般,非時下矯揉造作擺名師派者所能夢見。這樣一種投入的狀態,正符合著“寫”的第二耍義。《詩·小雅·蓼蕭》:“既見君子,我心寫兮。”寫者瀉也,二字古來相通。我們說中國畫不是靠畫,而是靠寫,猶如明言其畫者就是通過作畫在宣泄某種情感。所以“寫”的要求至高無上。必須做到動情投入,寵辱不驚,超越功利,物我兩忘,就像莊子所描繪的“解衣般礴”,方當得上一個“寫”字之名,絕非落款中有個某某寫既可稱之為“寫”的。
問:您認為老舍先生在“錘煉筆墨”上有何高見?
答:老舍先生分別從三個不同的角度和層面來談這個問題,他懷揣一顆對中國文化、對中國畫藝術高度負責的赤子之心,其見解當為“錘煉筆墨”的航燈:
讓我拿幾位好友的作品作例子來說明吧!我希望他們不因我的信口亂說而惱了我!趙望云先生以數十年的努力做到了把現代人物放到中國山水里面,而并不顯得不調諧,這是很大的功績!但是假若我們細看他的作品,我們便感覺到他短少著一點什么,他會著色,很會用墨,也相當會構圖。可是他缺乏著一點什么,什么呢?中國畫所應特具的筆力……他的筆太老實,沒有像刀刻一般的力量。他會引我們到“場”上去,看到形形色色的道地中國人,但是他并沒能使那些人像老松似的在地上扎進根去。我們總覺得過了晌午,那些人便都散去而場上落得一無所有!
問:老舍先生到底是大文豪,這番話描述得太好了!對今天的批評界有表率作用。
答:筆力太弱不行,是老舍先生的第一層意思。是不是只要“強”就行呢,也不是。他批評豐子愷的畫時這樣說:
一律用重墨,沒有深淺。他畫一個人或一座山都像寫一個篆字,圓圓滿滿的上下一邊兒粗,這是寫字,不是作畫,他的筆相當的有力量,但是因為不分粗細,不分濃淡,而失去了繪畫的線條之美。他能夠力透紙背,而不能瀟灑流動。也只注意了筆,而忽略了墨。
問:筆能強到力透紙背真厲害,但動不起來,缺乏墨色變化也不行,這是老舍先生的第二層意思嗎?
答:對。但是老舍先生還有一層意思:
再看關山月先生的作品,在畫山水的時候,關先生的筆是非常地潑辣,可是有時候失之粗獷。他能放而不能斂。“斂”才足以表現力量,在他畫人物的時候,他能非常的工細,一筆不茍。可是他似乎是在畫水彩畫。他的線條仿佛是專為繪形的,而缺乏著獨立的美妙。真正的好中國畫是每一筆都夠我們看好大半天的。
老舍先生這三層意思環環相扣,在他的“筆力”概念中,首棄“弱”字,復重其“變”,更提出了“斂”的要求。弱者無能之謂也。自然界弱肉強食,弱而必致于喪亡。故老舍先生用“落得一無所有”之語警世。
筆有正、側、聚、散之變,墨有新、宿、積、破之變,變則通,通則靈,然后既能“力透紙背”又能“瀟灑流動”是之謂變通。
斂者收也縮也。王勃詩:“川霽浮煙斂,山明落照移。”世事人生活一境界而已。力的表現形式應以此為高。
問:您好像講過“現在的中國畫壇不怕少石濤,惟恨缺四王”,對照老舍先生的高論,張老師想必擔心的是繼承問題,而非發展問題
答:天下事萬變不離其宗。
找到自然之美與藝術之美的聯結處,這個聯結處才是使人沉醉的地方。
老舍先生這句話無疑點到了中國畫的要穴(這恐怕也正是所有架上繪畫發展的不二大道),而這個聯結處的“度”的把握自然就是對實踐者的考驗了。記得宗白華先生講過,歷史每向前一步的發展,必伴隨著退后一步的探本求源。老舍先生對發展中國畫的意見也是首先想到第一要去把握我們承傳有緒的“筆力”,然后才言及其它。因此,我們看老舍先生對林風眠“不折不扣的真正西洋畫”的分析,就竟然與一直以來的“潮流”相悖。老實說,我心里也一直疑惑“林是中西合璧”的觀點。辛亥革命80周年,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舉辦過一個紀念展,其中有孫中山的書法,黃興的字等歷史資料,我特別留意到展廳里懸掛著一幅林風眠的早期立軸畫,其中國畫水準確如老舍先生所言“一定要先再下幾年功夫”。僅由材料層面接觸中國畫,任你再有才,也難融入中國畫歷史的發展洪流。
問:最后,我們還想請老師談一談何謂“美的裝飾”?何謂“美的原動力”?對老舍先生的這句話,我們該如何理解?
答:老舍先生6。年前評述畫作的這些語言,我們今天咀嚼起來別有滋味。現時有一些畫家為了迎合市場,說自己的畫富有“裝飾美”,同時,“裝飾美”這一詞匯也幾成美術評論時尚之語。殊不知這從另一側面暴露了畫家和評論家自己的疏淺和缺乏創造力。“裝飾美”咋一看是美的,但卻是圖式化的,若過于偏重的話,在純藝術作品中就是淺薄的,沒有內涵和活力的,而美的原動力則蘊藉著厚重博大的自然美和原始美。注意,這里說的自然美和原始美,不是不事雕鑿,不是原生態,不是所謂的生野樸拙,而是歷經風雨之后的綻放和返樸歸真的極致,是生命被賦予線條、色彩的光華映射,是思想的勁舞,靈魂的高歌,血脈的律動,它反映了一種詩情,一種文化品格,一種精神氣度,可謂之升華了的絢爛,大境界、大美。它是有堅韌的質地的。
附錄:
老舍先生1947年寫的《傅抱石先生的畫》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對中國畫有極為深刻的見解,獨到而精辟,有普遍的美學指導意義。張友憲教授和學生的談話對這篇文字做了很好的介紹,同時也深入淺出地加以分析,說得很好,是一篇認真思考的作品。今李群先生帶來給我,讀后甚喜,特記之。
舒乙
2008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