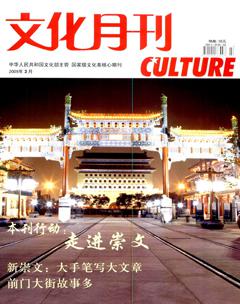漢學家史景遷的秘方
葛曉愛
美國漢學大師史景遷,十分景仰我國漢朝史學家司馬遷,并以弘揚太史公文筆優美的書寫傳統為樂事,于是取了這么一個中國化的名字。40多年來,他寫了10多本有關中國的書,如《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1974年)、《利瑪竇》(1984年)、《追尋現代中國——1600-1912的中國歷史》(1990年)、《中國縱橫》(1992年)、《大汗之國: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1998年)、《毛澤東》(1999年)等。
史景遷的中國歷史作品不僅在史學界反響甚大,也常常成為出版界的熱門貨。美國評論界稱,“它們不僅要接受來自同行的由衷贊揚,還奮不顧身地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據說,許多美國青年正是通過他才知道魯迅、丁玲并了解中國現代史的。
史景遷講述中國故事的秘方何在?史景遷講述中國故事的人文視野,為中國出版走出去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提供了一種視角和技巧。
一種視角
進入20世紀80年代,史景遷出于對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興趣,創作了《利瑪竇的記憶之宮》(1984)和《胡若望的困惑之旅》(1988)這兩部作品。利瑪竇在中國生活長達27年,竭力調和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間的矛盾,并積極傳教,收獲頗豐。而胡若望則是一個皈依了天主教的中國人,曾被帶到法國生活數年。但他對西方文化并不適應,結果鬧出許多亂子,自己還一度被關進瘋人院,歷經坎坷,最終被遣送回國。通過這種比較研究,史景遷揭示了晚明時期中西文化交流效果的強烈反差。
這種比較研究為中國出版走出去提供了一個不同尋常的著眼點,那就是在世界版圖中觀察發生在中國的事。這種視角的確立,可以使海外讀者在一種左右對比的審視中,來觀察那個年代中國所發生的一舉一動,尋找其中的距離與落差,從而改變傳統所見講述中國故事的自說自話的陳舊模式。
我們知道兩種文化相處時很容易有“誤解”,“誤解”不一定符合被看的一方的本來面目,所以不同文化之間需要互看。北京大學樂黛云教授在評價史景遷對學術的貢獻時說:“史景遷的主要貢獻是啟發不同文化要互看,從而造成一種張力。自己看自己,比較封閉。我看你,與你看你自己是不一樣的。”
一種技巧
我們生活的年代,構成我們生活的背景。沿著年代的背景,去考察每個人生活的狀態,他們的情緒或表情,都構成了社會生活、國家生活的表情,從而成為一種時代性的記憶。
一沙一世界。反之,宏大的社會生活、國家生活都表現于微觀的個體生活,農民、城市群體的際遇,無不折射著一個時代的表情。由此,具體的個人、事件濃縮社會的變遷,而個體的體驗和感情為社會的變遷作了鮮明的注解。
傳統的歷史研究往往局限于帝王將相、偉人、成功者,或者是參與重大事件的精英人物。所以梁啟超在批判傳統的史學時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而中國出版業走出去也往往囿于王侯將相、朝代更迭的歷史坐標。
但是在史景遷的中國故事中,有雄才偉略的封建帝王康熙、雍正,有熱血沸騰的革命者毛澤東,有農民起義領袖洪秀全,有才華橫溢的作家曹雪芹、魯迅、丁玲,有封建君主忠實的大臣曹寅,有謀逆秀才曾靜……甚至還有最普通的平民百姓如胡若望、王氏,等等。
史景遷講述的中國故事正是通過追究人物的自身存在價值以及社會投射在個別生命中的痕跡,揭示各色人物背后的大歷史,才讓海外讀者相信:在他的故事中,歷史人物是真實的、可靠的、生動的、活潑的。這為中國出版業走出去提供了“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技巧。
按照這樣的邏輯,我們不妨這樣講述中國故事:將個人或事件置身于一個宏大的時空背景下來考察,深入到個體的生活中,具體觀察事件的脈絡,借助小說式文學化的語言表現具體的人和事,能有效表達出這個中國故事的主題。
這正是漢學家史景遷講述中國故事的人文視野,也是中國出版業走出去需要建構的視角和技巧。當然,這只是我,以自己職業的眼光“斷章取義”地看到的史景遷講述的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