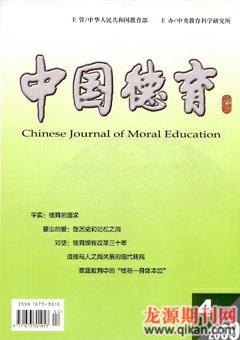面向身體關照的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應該是有魅力的,因為“它面對的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人和冷冰冰的理性”(魯潔教授語),對人之身體的關照是道德教育的應有之義。自尼采以來,身體從被壓制、被遮蔽的歷史命運中覺醒,道德教育也在壓制、否定身體的道德教育和物化、規(guī)訓的道德教育后,重新審視自我,開始訴求生命的發(fā)展與身體的關照。
一、歷史語境下的身體命運
(一)卑賤和被壓制、遮蔽的身體
很長時期以來,人們總是將自身分為靈魂與身體兩個部分,對靈魂與身體關系的探討成為哲學史上不休的話題。自柏拉圖以來,身體被降格為肉體,處于卑賤的地位:身體是短暫的、貪欲的、低級的和惡的,靈魂和身體是對立的。柏拉圖認為,身體對于知識、智慧、真理來說,都是一個不可信賴的因素,身體是靈魂通向它們之間的障礙。“帶著肉體去探索任何事物,靈魂顯然是要上當的。”[1]在《高爾吉亞篇》和《理想國》中,柏拉圖也拼命貶低身體,對身體的滿足感嗤之以鼻,認為正是身體的欲望、需求導致了塵世間的苦難與罪惡。相對于身體,靈魂才是優(yōu)越的,通達善的。“在柏拉圖的這個二元論傳統中,身體基本上處在被靈魂所宰制的卑賤——真理的卑賤和道德的卑賤——位置。可以說,自此以后,身體陷入了哲學的漫漫黑夜。”[2]6同樣,身心二元論在奧古斯丁那里得到了強調。他說,身體“是人接近上帝必須克制的放肆本能”。正是由于欲望的身體無法接近真理,是卑賤低下的,需要受到克制,所以在黑暗的中世紀,身體被神學禁錮,處于被壓制的狀態(tài)。
17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使知識與理性慢慢占據了哲學的興趣中心,身體不怎么受到譴責和管制了,但卻因為其不再是個問題而受到忽視,被遮蔽了。科學不再理睬身體,因為科學知識是那些經由理性思考的確定的知識,而基于身體產生的感性經驗則是不可靠的,受到理性的科學知識的歧視。哲學觀由身心二元對立轉為感性與理性的二元分立。身體被遮蔽、被遺忘,始于笛卡爾的意識哲學。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確立了自我的中心位置。在笛卡爾那里,靈魂是思想的實體,而這一實體的存在,是不以身體的實存為前提的,當“我”在懷疑我身體是否存在時,“我的意識(精神)”已經先在地被確證了,而這一意識(精神)的實存是不容懷疑的。“我”就是“我思”,是無外部經驗內容的、純粹的自我,只有純粹的自我,才有所謂的確定性。因此,笛卡爾的“我思”意義上之“我”,是抽掉了具體內容的、作為“純粹思維”之“我”。正是在這里,人的身體被抽空了,虛化為一種以沉思作為生存方式的“意識”。[3]
無論是笛卡爾之前的對身體的壓制,還是笛卡爾之后對身體的遺忘和遮蔽,身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遭受著悲劇式的命運。
(二)“一切從身體出發(fā)”:尼采與身體轉向
直到尼采那里,身體才跳出了靈魂對它的壓制與遮蔽,跳出了二元分立傳統,可以自我做主了,“一切從身體出發(fā)”是尼采的口號。尼采要將身體放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也就是說,要“以身體為準繩”:“一切有機生命發(fā)展的最遙遠和最切近的過去靠了它又恢復了生機,變得有血有肉。一條沒有邊際、悄無聲息的水流,似乎流經它、越過它,奔突而去。因為,身體乃是比陳舊的‘靈魂更令人驚異的思想。”[4]由此,尼采開辟了哲學的新方向,開始將身體作為哲學的中心。
德勒茲與福柯繼承和發(fā)展了尼采的身體一元論和決定論,都對身體的價值給予充分肯定,但在身體的主動性與被動性上,二者的觀點有所不同。身體在尼采和德勒茲那里是主動的,表現為積極的生產性,它生產了社會現實,生產了歷史,身體的生產就是社會生產。身體在福柯那里則是被動的,表現為被動的權力改造,它被作為一個生產工具,“權力關系總是直接控制它,干預它,給它打上標記,訓練它,折磨它,強迫它完成某些任務、表現某些儀式或發(fā)出某些信號” [5]。
從以上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身體不只是肉身化的存在,而是刻寫著歷史印記的存在,身體是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統一體。在傳統二元分立的哲學觀下,身體只是包括醫(yī)學在內的自然科學的主題,而身體的覺醒使身體的話語開始呈現在包括教育學在內的人文科學之中。
二、身體在道德教育中的遭遇
當身體問題被歷史地凸現出來時,道德教育作為面向人的一門學問,也應對其與身體的關系作一個歷史的省思。道德教育如何面對身體,將意味著道德教育的指向和實踐態(tài)度。
(一)古代道德教育:對身體的壓制、否定
在古代漫長歷史時期中的道德教育,總體上的特征是壓制、否定身體的道德教育。
由于充滿欲望的惡的身體是無法達至不朽的善的靈魂的,所以在西方中世紀,在道德教育實施場所的教會和修道院中,禁欲是控制身體的基本手段,身體要“克己、苦行、冥想、祈禱、獨身、齋戒、甘于貧困”,“正是將身體陷入沉寂狀態(tài),信仰、啟示以及上帝的拯救才能紛至沓來。靈魂活躍狀態(tài)的前提,是身體的必要塵封”[2]7。道德教育正是通過對肉體、感官欲望的壓制,來達到靈魂的純潔。道德教育的過程,是對身體自然欲望馴服的過程。
自文藝復興以來,人的身體、身體欲望被重新召喚出來,但是并沒有獲得充分的自我解放,哲學此刻的目標是摧毀神學,并非解放身體。因為神學的對立面是科學和知識,所以所有的任務都是激發(fā)對知識的興趣和理性的張揚,教育和道德教育也不例外。在笛卡爾那里,心靈同身體分屬于兩個不同領域,身體的感知能力無足輕重,只有心靈的能力才能揭開知識和真理的秘密。主體的實質性標記是思考,而不是盲目的身體。這樣,身體與知識的關聯被切斷了,身體在教育過程中便成了可有可無的角色,也就在教育歷史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進而被邊緣化了。道德教育強調的是道德知識的傳授,道德體驗也被抽離掉了生動的身體感覺,成了沒有身體的空虛的心靈說教,身體在道德教育中是受到否定的。
同樣,在中國古代,身體在道德教育中也經歷著相同的命運,突出反映在各種“禮”的道德教育中。明朝《社學要略》中要求學生:“行步要安詳穩(wěn)重,不許跳躍奔趨;說話要從容高朗,不要含糊促迫;作揖要舒徐深圓,不可淺遽;待立要莊嚴靜定,不可跛倚;起拜要身手相隨,不可失節(jié)……”從禮儀教育入手,卑賤的身體首先成為需要壓制的對象,道德感的獲得及相應的評價標準就是來自于對身體動作的規(guī)定性要求。
(二)現代道德教育:對身體的物化、規(guī)訓
隨著人類科學技術的空前發(fā)展和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人繼而以技術化的存在為其現實的存在,人的技術化生存使人的存在等同于“物件”,身體在道德教育中又成為了被物化、規(guī)訓的對象。
現代社會中身體也是具有欲望的,但是與以往社會相比,“現代社會中身體的欲望不是簡單的自然欲求,而是被現代社會組織和消費文化規(guī)制下的欲求”[6]。人與人之間的透明關系,變成了以現代技術如電子網絡為中介的間接關系,身體被符號化的關系遮蔽了,靈動的生命代之以同質化的單子,以身體為基礎的生命感覺日益枯竭。人的技術化存在導致的后果是,身體的自我和自我的身體成為兩個分立的概念,表現著身體的現代性分裂。在此背景中,身體被等同于物件,道德教育成為規(guī)訓的工具也就是必然的。
與此同時,現代社會高度的社會分工和市場經濟的功利主義邏輯,使人不再關注自身,而關注社會的需要,因此,教育不是成“人”的教育,而是成“材”、成“器”的教育。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道德教育也必然受到功利主義的影響,成為使人成“材”、成“器”,規(guī)訓身體的權力話語之一。在功利主義的影響下,道德教育有著強烈的社會本位色彩。自道德教育產生開始,就在社會發(fā)展和人的發(fā)展之間徘徊并確認著自身的屬性和價值,道德教育的應然追求是使社會目的與人本目的達成統一。然而,由于片面強調社會目的,維護社會穩(wěn)定和發(fā)展的秩序,道德一度被演化為一些道德規(guī)范教條,以此來約束人,道德教育成了社會教化的工具,而缺少了對人、人之身體的關懷。
倘若道德教育僅僅將身體作為打壓和規(guī)訓的對象,力圖以此來成全空洞的精神,或達到某種社會目的,那就是一種值得警惕的邏輯。道德教育有必要重新彰顯對生命的提升,訴求生命發(fā)展,讓身體重新找回它在道德教育中應有的位置。
三、身體關照:道德教育不可忽視之維
身體是自我的一個標志性特征,與人的生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長期以來,“生的意義,或者更準確地說,人的意義總是置放在生命這個范疇內,而不是置放在身體這個范疇內”。“事實上,身體是生命的限度,正是在身體這一根基上,生命及其各種各樣的意義才爆發(fā)出來。”[2]23道德教育的目的是生成人的德性,使人過一種有道德的生活,道德教育還有一種超越性,促使人不斷追求生命的意義。因此,身體在道德教育中不可缺席,道德教育需要面向身體關照主要基于以下幾方面的理由。
(一)身體:道德認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為的承載
道德的構成性要素包括道德認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為三方面,在歷史上和當前的道德教育理論和實踐中,對這三者的強調有不同的側重。在皮亞杰和科爾伯格那里,道德認知被擺在突出的位置,他們認為個體道德認知水平的發(fā)展狀況決定著他的道德行為;在霍爾曼和艾森伯格那里,情感方面受到了重視。無論強調道德構成要素的哪一個方面,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它們都是人所產生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由人的身體所產生的。忽視身體的道德教育,再高階段的道德認知,再美好的道德情感都是虛無縹緲的,也無法變成期待中的道德行為。
同時,更為重要的是,身體還是道德行為的擔保。“沒有了身體的擔保,人們很快變得行為放縱,為所欲為”,“沒有了身體的約束,人性和道德也就失去了擔保,人性中的惡就會堂而皇之的到處游逛”[7]。在非物質性的網絡世界中,身體是“退隱”的,因為沒有身體,我們看不到他人的面孔,所以就可以逃避責任,這將產生始料不及的道德后果:“倫常的松懈、人際的粗魯、義務的淡漠、責任的飄零”[7]。身體就像道德生成的“土壤”,身體不在場,情感交流、道德熏染等都無法達成,道德教育能否使道德的種子在個體成長中生根、發(fā)芽就值得懷疑。
(二)身心和諧:道德教育應有的身體觀
傳統理論中,身心是二元對立的,靈魂是善的、高尚的,而身體是惡的、低賤的,道德教育便成為管制身體的工具,成為了并不道德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所應持有的身體觀是在身心統一的立場上來理解身體,理解受教育者。
海德格爾在解讀尼采的審美思想時,對身體問題做了如下論述:被看作純粹心靈上的情感狀態(tài),應當歸結于與之相應的身體狀態(tài),“從整體看來,這恰恰就是那個未被撕碎的,也撕不碎的身—心統一體”,“我們并非‘擁有一個身體,而毋寧說,我們身體性地‘存在”[8]。18世紀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教育家盧梭已經看到了軀體養(yǎng)護背后的道德意義,他說“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體”,正是基于這些道德意義上的洞見,他制定了對愛彌兒的完整的教育計劃。身心和諧的身體觀不僅是道德教育對于完整人類生命的肯定,也是其鮮明的學科立場。道德教育不能肢解身體,即便我們在對教育做出德育、智育、體育等劃分時,也應把身心和諧作為根本出發(fā)點。
(三)身體力行:道德教育的培養(yǎng)目標
道德教育旨在生成個體的德性,使個體過有道德的生活,這就不僅要使個體具有良好的道德判斷,產生道德情感,還要求個體能夠成為在道德上“躬行實踐”的人。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強調“做中學”,主張教育要特別注重人的身心培養(yǎng),注重那“發(fā)動的、有精力的、有生氣的性行。身體上的動作,應當分外注意”。杜威由此論述了三種主要的“造就發(fā)動的性質和方法”,包括游戲運動、注重手的活動、注重人對天然物象的觀察和實驗。道德教育也可以被看作是這樣一種“做中學”的學問。
以往我們的道德教育是一種“徳目”化的道德教育,集中體現在學校德育課程以學科邏輯來組織,授之以道德的知識,正如杜威所批判的,“直接的道德教學只能幫助學生形成‘關于道德的觀念,不能形成‘道德觀念”。如今,“回歸生活”的理念將價值引導蘊涵在鮮活的生活之中,鼓勵學生積極探究和體驗,通過道德踐行,促進品德的形成與發(fā)展。能夠身體力行的有道德的人才是道德教育的培養(yǎng)目標,而“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是我們所不希望看到的。
參考文獻:
[1]柏拉圖.斐多[M].楊絳,譯.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13.
[2]汪民安.身體、空間與后現代性[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3]孫元濤.身體問題的教育學思考[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6,(10):5—8.
[4]尼采.權力意志[M].張念東,凌素心,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37—38.
[5]福柯.規(guī)訓與懲罰[M].劉北成,楊遠嬰,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27.
[6]王強.道德教育與身體關系省思[J].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73—78.
[7]高德勝.身體退隱的道德后果——論網絡世界中的身體、道德和道德教育[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7,(2):5—11.
[8]周與沉.身體:思想與修行[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399.
【陳麗娜,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2007級碩士研究生。江蘇南京,210097】
責任編輯/趙 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