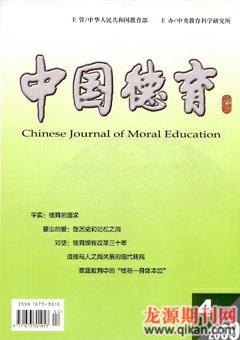后思想時代:用“表演實踐”證明自己是人
畢世響
個人沒有權力作踐人
之為人的尊嚴
藝術冒險或者藝術探險,是人類的最高探險行為,因為藝術探險是對人類精神禁區的侵入,也是對人類尊嚴的挑戰或者冒犯。藝術探險比體育探險、地理探險等要艱難得多,因為頭腦到不了的地方,雙腳肯定到不了。藝術探險是用精神、思想和靈魂和某個神秘打交道,藝術家探險是企圖和某個神靈相遇,達到在某個精神世界的契合。然而,是不是藝術家都能夠懂得倫理學,藝術家的藝術行為是不是符合人類的倫理精神,那就是另外的事情了。藝術證明人的境界,倫理證明人的高尚。
今天,我們的生活之中出現了許多叫人感到不舒服甚至惡心的行為:有人吃人肉,有人和驢子結婚……這些人說他們的舉動是“行為藝術”。人類有幾條基本的倫理規范不能違背:同類不能相食(瘋牛病與牛吃牛肉有相當的因果關系。自然在進化的過程之中,就天然地把倫理理念根植在物種的進化過程和結果之中,違背這個“同類不相食”的倫理精神,必遭天譴),異類不能結婚。這種人吃人的行為、人和獸結婚的行為,無論“藝術家”背后有什么樣的思想,都是反倫理、反道德、反人類的行為。個人的任何行為,都證明著人類的尊嚴,任何一個人都沒有權力作踐人之為人的尊嚴,因為任何一個人都是人類的一環,個人和人類的關系是倫理關系。不存在脫離了人類的個人,任何一個人都在整個人類的支持下存在,任何一個人的尊嚴都關系到整個人類的尊嚴。個人生活在社會之中,不存在純個人行為,社會正義就是依靠個人的善。
我們國家當下處于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我們的倫理道德也處于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我們既不能完全守住農業文明下的倫理道德觀念,又沒有全面進入工業文明下的倫理道德體系,這樣一來,我們每個人的行為都在這兩種文明體系下跳搖擺舞。至少,社會已經不再簡單地用過去那種“正確”“錯誤”倫理道德標準來衡量人們的言論和行為。在這個時代,怎么辨別某些言論和行為到底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的確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而有些行為在道德上到底是不是錯誤的,也很難判斷。因為有些言論或者行為也許在道德上不合適,但是,在法律上卻沒有錯。一個人有權力那樣說話或者行為,這是民主時代,不能用某種強權道德強迫人家。
然而,社會總有它基本的思維精神和道德精神,譬如,在這個時代,“公共理性”應該是中國現代化發展中的根本思維精神,也是道德精神。如過去農民種莊稼,是給自己吃的,現在農民種莊稼,是賣給全國乃至世界上的人吃的,那么,必須考慮對國家乃至世界負責。所以,現在每個人的言論或者行為,都是公共性的,不是個人性的。因為你說的話,做的事,不是說給自己聽的,做給自己看的,而是說給別人聽的,做給別人看的,所以,你說話的道德性就應該受到社會的評價,無論你是誰。如,人民代表大會上的人大代表,該怎么說話才是為人民利益請命;大學教授該以什么樣的利益群體代言為改革理性呼吁吶喊;課程改革專家該以什么樣的目的奔走于學校和學校之間;怎么看待政府官員的“形象工程”和“親民”;怎么看待娛樂明星出沒于受災場合;怎么看待專家、學者在學術場合的登場。難怪社會上有人把這些人的某些言論和行為與“行為藝術”發生某種聯想。這也說明社會的思維在進步,社會并不是以你的社會身份來判斷你,而是以你的言論和行為來判斷你。這,就是民主,就是文明,就是進步,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最大的精神文明。
沒有人否認藝術的高雅、高貴和高尚——只要是真正的藝術,即使不能一時被公眾接受,其明顯的道德性還是能夠辨別出來;而當一種新的藝術形式違背了社會倫理道德的時候,某些“行為藝術”不但在根本上不是藝術,而且還是下流與墮落,無論其初衷是什么樣的。
人人都是
生存倫理學家
二十多年前,中國人做夢也不會想象到當下社會上人的行為:男女同居、穿露股裝、公開親昵、試婚、性交易。現在往往把妓女或者男妓叫做“性工作者”。這種叫法很人性化:她(他)們的行為是工作,和你我一樣的養家活口的工作,所以,不能失去對她(他)們的尊重,她(他)們的行為和你我的行為一樣都是生活方式,是為了生活。這既是社會的寬容,更是社會的現實,也是社會的倫理道德容納,還是現代社會文化的一個特征:多元性。而且,社會的經濟、政治、道德、文化等等走到今天這個發達的時代,居然一切問題都走向了出發點——生存,似乎人們的一切都是為了生存。生存——活著——存在——生活——生活方式,人的生存首先是以一定的生活方式為人,生活方式本身沒有什么可指責的,因為人人都用一定的生活方式生活,只要是生活,就在生活方式之中,道德成為社會對生活方式的評價意義。在一定意義上說,你怎么生活可能并不是你自己愿意那樣生活,而是生活所致。當然,也可能是你愿意那樣生活,那就是你的生活方式。這樣理解當代人的生活方式,可能比較容易理解社會上各種各樣的生存狀況。
生存的意義又是什么呢?現在社會的一般情形是,一個人和另外一個人之間的區別僅僅在于其社會地位的差別、經濟地位的差別,人們在道德上、在智慧上沒有根本性的差別。社會地位高的人、經濟地位高的人,他們的道德和智慧并不必然比社會地位低的人、經濟地位低的人道德和智慧高。當然,也有例外,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本來就應該有例外。這里的道德和智慧并不是指你在公開場合衣冠得體、彬彬有禮、氣度高雅、消費合理,也不是指你能夠說出燦爛的話語、寫出妙曼的文章,而是你的思想、情懷、心地是否良善,有沒有社會正義感。
討論人生存的意義,并不只是專門的思想家或者學者的權力或者興趣,每個人都時時刻刻在討論自己生存的意義——討論的方式不一樣罷了,學者用專門的文章說話,不是學者的人用行為說話。那些生存得優越的人覺得自己的生存有自己的某種意義,那些生存得可憐的人覺得自己的生存也有自己的某種意義。這樣一來,每個人都成為實踐倫理學家,因為任何一個時代的倫理學,實際上都是那個時代人的生存意義和人生價值的理論表現。倫理學,簡單來說就是關于人的生存意義的學問。從學問上說,人類和個人都希望生存得光榮一些、高尚一些、精神完善一些,這就無怪乎有人說,倫理學是一門使人光榮與高尚的學問。哲學的終極目的是在世界上行事的人,而在世界上怎么行事,卻是倫理學的意思。那么,倫理學的終極目的應該是在世界上高尚地、光榮地行事的人。倫理學不是一個中性學科,而是有立場和傾向的學科,用傳統的話來說,倫理學是有“黨”性的,代表一定群體或者階層在說話。這在根本上規定著人的行為應該是高尚的、光榮的。
也許,用傳統的眼光看,中國人現在要出盡天下一切“洋相”,抑或是占盡一切風流或者風光:藝術院校的幾十個男女大學生,以藝術的名義,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絲不掛組成某種符號;女性大學生則以拍攝自己的下體寫真為藝術展覽。和這些“出洋相”或者風流與風光相表里的,則是我們生活的巨大變化:二十多年前,中國人做夢也不會想象到,個人現在打電話比喝涼水都容易——并不是可以隨時喝到涼水,卻可以隨時打電話,因為電話是裝在口袋里、拎在手上、掛在脖子上的。我們搭飛機旅行;出國看風景;買汽車;住花園洋房;吃肉可能吃膩歪了,要吃野菜。這樣的生活方式,那可是過去我們批判了多少年的資產階級的腐朽生活方式呀。原來,我們也可以享受,但并不腐朽。
社會本身就是二元的:有善,有惡,善是道德的歸宿,惡是道德的一個起源,善惡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是可以轉化的,由惡可以激發起善。社會之所以有某種惡,往往就是因為社會有某種對應的善。如果行為藝術之中有某些違背了倫理道德的行為(如異類不能結婚等),那么,應該看到這些行為背后的某種善:“異類結婚”所包含的對異類(動物)的愛護——過去,我們一直把人和動物對立起來,以動物罵人,因為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在于人是有道德的,動物沒有道德,所以,無論怎樣愛護動物,人和動物還是有不能逾越的界限的。現在,我們把動物看作人類的朋友,“愛護動物”正是這個時代的時代精神之一。然而,“愛護動物”只是這類行為藝術的表層意義,所謂的“與驢子結婚”的行為藝術,并不真的是與驢子之間有肉體關系而生兒育女,其深層意義則可能是這個時代人類婚姻的某種隱喻、人類精神的某種訴求罷了。行為藝術家只是用一種夸張的行為表演,把自己的意思演繹了一番而已。這促使我們對時代進行反思,對生活進行反思。在這個意義上說,行為藝術家可謂用心良苦。
實際上,一切行為藝術都應該作如是觀:隱喻,精神訴說,表演,夸張,反思。進一步可以認為,當今時代,人人都是行為藝術家,因為人人都在進行精神訴說,只是訴說的方式不一樣罷了。這也是民主時代的一個特征:人人都可以說話。
“借尸還魂”
與思想的劫后余灰
行為藝術和傳統藝術之間的最大區別是:行為藝術不要為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情負責,“行為藝術家”——他或者她——的行為,可能都不要考慮為自己負責。因為他或者她的行為在相當意義上只是表演給人看的,你看或你不看,你欣賞或你不欣賞,都是你的意志。他或者她知道,他或者她在于表演——在公眾場合表演,表演自己,表現自己。他或者她不在私下表演,因為私下沒有人看,在公眾場合總有人看,所以,他或者她不擔心沒有觀眾。然而,表演自己并不是把自己當作自己來表演,而是把自己當作某一個符號來表演,多少有些孤芳自賞、顧影自憐的情愫與旖旎。行為藝術家在根本上是一種虛無欣賞的魅影,而不是人。在網絡時代,人已經被科技和生活高度異化,有可能人人都已不是人,只是一個魅影罷了。
在網絡民主時代,每個人都可以通過網絡手段向世界證明自己的存在,證明自己是人,只要是合法的,不像發表或者出版著作那樣,除了合法以外還得符合學術編輯部的學術要求。這個時代是后思想時代——把前人的思想據為己有,用自己的地位、身份、話語系統表演前人的某種思想。這樣的表演帶有一定的蠻荒性,如裸體表演、自虐表演、污穢表演、故作高深表演等等。實際上,越是“嚴肅”的表演越蠻荒,越蒼白,越證明自己沒有思想。荒誕的表演,倒可能隱含某種思想。這兩類表演形式,或者能夠為一般公眾所接受與理解,或者不能為一般公眾接受與理解,卻以“文化”“藝術”或者“思想”的名義表演。他或者她宣稱自己在表達某種思想——有時候真的在表演某種思想性的東西,有時候表演的并不是某種思想——自以為是思想性的表演,那種表演就是他或者她要表達的思想。然而,那個所謂的“思想”并不是自己的,而是他人的思想或者社會的思想,他或者她根本就沒有思想。那么,也可以把所謂的“行為藝術”理解為“借尸還魂”——借自己之尸體(軀體),還原他人之思想(靈魂),或者,把自己的軀體中裝上他人的思想而已。那么,這個時代也可以叫做后野蠻時代、后思想時代。他或者她能夠達到的境界只是企圖證明他或者她是人而已——認為自己是藝術家,是教育家,是思想家,是具有某種理念的官員——他或者她根本就不知道柏拉圖的理念是什么意思。實際上,他們充其量只是藝術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劫后余灰。
社會是你的,社會是我的,社會是他的,社會是她的。你、我、他、她,完全可以只過自己的日子——多少有些渾渾噩噩,不跳出來管社會如何,社會責任感是他人的,不是我的。而行為藝術家以某種自己理解的社會責任感,跳出來向社會發問,就像屈原一樣進行“天問”:我是人嗎?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教育科學與技術學院,福建福州,350007】
責任編輯/劉?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