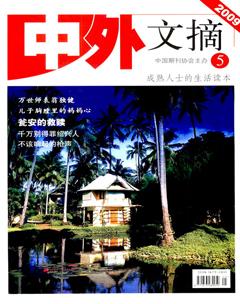我最愿意生活的10個時代
2009-08-11 02:58:32李方
中外文摘
2009年5期
關鍵詞:時代
李 方
一、十一世紀的北宋
這個時代之所以高居榜首,我的想法很簡單,是因為這一百年里,五個姓趙的皇帝竟不曾砍過一個文人的腦袋。我是文人,這個標準?低,對我卻極具誘惑力。
這得托宋太祖的福。他曾對兒孫立下兩條死規矩:一,言者無罪;二,不殺大臣。難得他在十一世紀的五個繼任者都特別聽話。
于是文人都被慣成了傻大膽,地位也空前地高。想想吧,如果我有點才學,就不用擔心懷才不遇,因為歐陽修那老頭特有當伯樂的癮,如果我喜歡辯論,可以找蘇東坡去打機鋒,我不愁贏不了他,他文章好,但禪道不行,卻又偏偏樂此不疲;如果我是保守派,可以投奔司馬光,甚至幫他抄抄《資治通鑒》;如果我思想新,那么王安石一定高興得不得了,他可是古往今來最有魄力的改革家;如果我覺得學問還沒到家,那就去聽程顥講課好了,體會一下什么叫“如坐春風”。
當然,首先得過日子。沒有電視看,沒有電腦用,不過都沒什么關系。我只想做《清明上河圖》里的一個畫中人,又悠閑,又熱鬧,而且不用擔心社會治安……高衙內和牛二要到下個世紀才出來。至于這一百年,還有包青天呢。
二、本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
首先我得聲明,我沒有移民傾向。我只想站在人群里,聽鮑勃·迪蘭唱“How many road must a man walk down,before we called him a man”(一個人要走過多少路,他才能叫男人),這首名叫《答案在風中飄》的歌,是一首反越戰反種族歧視的歌曲,也是那個時代的圣經。
那是一個最紅火又最灰暗的年代。青年人在那時,幾千年來第一次打贏了反抗父母的一仗。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小哥白尼(軍事科學)(2022年7期)2022-09-20 03:51:30
嶺南音樂(2022年4期)2022-09-15 14:03:12
陽光(2020年6期)2020-06-01 07:48:36
陽光(2020年5期)2020-05-06 13:29:18
人大建設(2019年11期)2019-05-21 02:54:48
電影(2018年9期)2018-10-10 07:18:38
金橋(2018年4期)2018-09-26 02:24:44
足球周刊(2016年14期)2016-11-02 10:56:23
足球周刊(2016年15期)2016-11-02 10:55:36
足球周刊(2016年10期)2016-10-08 10:54:55